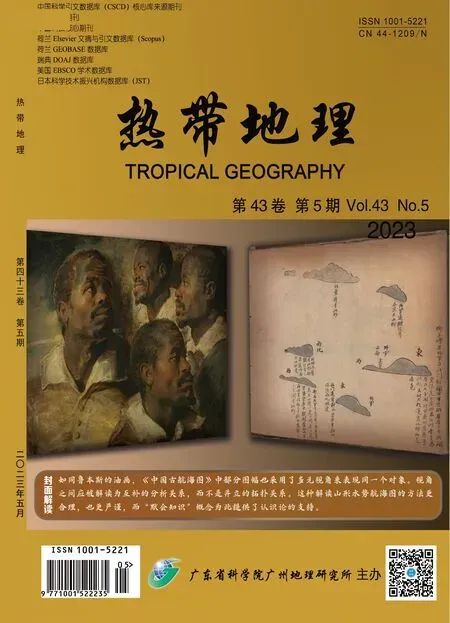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級市設置的空間特征及存在問題
趙 彪,莊 良,王開泳
(1.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邊疆研究所,北京 100101;2.華東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上海 200241;3.中國科學院 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設區市空間布局的結構問題是行政區劃研究的核心內容,如何通過優化城市規模分布來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構建科學合理的城鎮體系,是當前中國城鎮化進程面臨的重要任務。地級市(含副省級城市,下同)是省、縣兩級間重要的中間層級,同時兼具“城市”和“行政區劃”的雙重職能。無論是省直管縣、擴權強縣等縱向的行政體制改革,還是撤縣(市)設區、撤縣設市等橫向城市空間布局重構,地級市都處于改革的焦點。近年來,隨著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快速集聚,中國長期實行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已越來越難以滿足資源要素頻繁跨界流動的現實需求。深入推進以地級市為主體的城市改革,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之義,對于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與高效集聚,以及增強服務能力和提高治理效能都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市制起源于清末民初,清朝末年的上海租界是中國市制的誕生地(朱光磊 等,2017)。1921年頒布的《廣州市暫行條例》,標志著中國市制實踐的正式開始,廣州市也成為中國近代行政區劃建制意義上的第一個市。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市組織法》,將市分為行政院轄市與省轄市2 種,其地位分別相當于省和縣(朱光磊 等,201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主要采取市縣分治、城鄉分治的行政區劃體制,“市”主要指直轄市、省轄市和專轄市,其中省轄市與地區、地級市同級。1983年起開始推行“地市合并”“市領導縣”體制改革后,“省轄市”統一改稱“地級市”,地級政區逐漸由虛級的地區(專區)轉化為實級的地級市,地級市也逐漸由城鄉分治的城市型政區演變成為城鄉合治的地域型政區(杜英歌,2015)。雖然地級市作為一級政區地位的時間較短,但相關研究已在不同學科相繼展開,現有研究普遍認為當前地級市設置仍明顯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如譚其驤(2019)在1991年指出“我國現行的行政區劃基本上還在沿用元明清時代的區劃,歷代雖稍有變動,但基本格局不變”。而近30年來,行政區劃調整也多為撤縣設市、地區改地級市、撤縣(市)設區等整建制調整,行政區劃設置的基本格局仍保持不變。當前地級市的管轄范圍,仍受歷史上各“府”幅員的影響(高茂兵,2020)。地級市可稱為“地級政區”或“統縣政區”,周振鶴(2019)認為統縣政區幅員自秦至宋呈現逐漸縮小的趨勢,元代以后又經過一個先大后小的起伏,在實行“三級制”的時期,對統縣政區幅員大小的考慮著重于行政管理效率。當前,學界普遍認為地級市管縣缺乏憲法依據,對市管縣、省管縣的利弊進行了較多分析(才國偉 等,2011;龐明禮 等,2012;張震,2015;鄭磊 等,2016)。如張震(2015)從“市”的憲法內涵切入,指出地級市在中國憲法上具有規范依據,但地級市轄縣不具有憲法依據,出現了相當多規模較小、功能較欠缺的管縣的市。從歷史和實踐經驗看,省縣之間的管理體制具有很強的不穩定性,變動最為頻繁,學界也存在“強化地級市”和“取消地級政區”等觀點,如肖金成(2004)提出了地級市是中國最重要的區域經濟單元的觀點,認為應通過弱化省和縣級政府,強化市、鎮政府來逐步減少行政層級;而華林甫等(2016)則認為應減少政區層級,取消地級政區,實行省直管縣市。在全球化過程中,一些國家也在不斷尋求較大尺度上最優的行政區劃,以便為城市或區域賦予最優的公共任務和責任(Bakaric, 2012)。盡管每個國家在行政區劃設置方面具有不同的歷史和政治背景,但空間公平和空間效率始終是應當遵循的兩大基本原則(Halas et al., 2017)。
綜上可知,地級市產生時間較晚卻發展迅速,對城鎮化水平的提升起重要作用,逐漸成為行政區劃研究的熱點,并形成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在研究內容方面,對市管縣、省直管縣等“體制”問題(繆匡華,2010;才國偉等,2011;吳金群,2016;葉冠杰 等,2018;紀小樂 等,2021)關注較多,而對地級市設置的“空間”問題關注較少,尚未理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級市設置的空間演化過程;在研究區域方面,多集中在廣東、浙江等少數地區(童宗煌 等,2004;游細斌 等,2005;李含琳 等,2017;趙彪,2022),缺乏對全國范圍的長時段大尺度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定性分析為主,較少結合地理信息系統進行可視化分析,缺乏基于模型的定量研究;在改革思路方面,多集中在行政層級方面,忽視了地級市空間分布產生的問題及其邏輯。近些年,以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轉變為主的縣級行政區劃調整,不僅具有合作關系不斷增強的空間互動效應,而且還存在由競爭引起的相互制約影響(Wang et al., 2021)。跨政區的地級市空間優化設置,對于區域一體化發展、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實施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采用政區相似系數等方法,探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級市設置的空間特征及存在問題,并從地級市的政區演化邏輯思考其未來區劃調整的改革方向,以期為相關的空間理論和治理實踐提供參考借鑒。
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方法
政區相似系數(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imilari‐ty coefficient)。本研究采用1985 和2020 年中國地級政區行政區劃矢量圖,基于ArcGIS 平臺對各地級政區的面積進行測度,并按照“政區名稱”字段進行空間連接,將1985 年的政區面積比2020 年的政區面積,得出地級政區相似系數,即1985—2020 年中國地級政區面積的變動情況。并基于核密度估計法進行制圖,政區相似系數為1時,表示1985年的A政區與2020年的A政區面積大小相等,沒有發生變化;政區相似系數>1 或<1 時,均表示A 政區的政區面積發生了變動,>1 表示面積有所減小,<1 表示面積有所增加,系數越大或越小均表示變動幅度越大。其中,核密度估計法主要是借助一個移動的單元格(相當于窗口)對點或線格局的密度進行估計。一般而言,對于數據集(X1,X2,X3,……,Xn),固定帶寬的核密度估計函數公式為(劉靖 等,2009):
式中:K(*)表示核函數,滿足K≥0、K(x)=K(-x)和∫K(x)dx=1;正數h稱為帶寬或平滑參數,h值越大則平滑度越大,h對于所有的x∈R都為恒定的值;n表示估計點個數;x表示估計點;xi表示樣本i;x?xi表示估計點x到樣本xi處的距離。
由于受切塊設市①指將歷史上的州府駐地即后來的省政府或地區行署駐地的一小塊地域劃出設市,駐地所在縣仍然保留,加之歷史上的州府或行署駐地同時也是縣城駐地,故在設市后很容易出現市縣同城、縣包圍市的問題。的影響,對于既有地級市又有地區建制的狀況,選擇將地級市與地區的面積相加進行比較。如1985年時既有省轄承德市又有承德地區,而2020 年時只有地級承德市,故將1985 年的承德市與承德地區予以面積加總,繼而進行政區相似系數測算。
標準差橢圓模型(Standard deviation elliptic model)。標準差橢圓分析可以獲取地理要素的空間特征,包括中心趨勢、離散和方向趨勢,其構成要素包括轉角(θ)、沿長軸(主軸)的標準差和沿短軸(輔軸)的標準差。轉角(θ)是指在笛卡爾坐標系下x 軸和y 軸按照點集分布的地理方位沿一定角度旋轉后,正北方向與順時針旋轉的主軸之間的夾角。其計算公式為(朱彬 等,2014;王耕 等,2018):
式中:x'i和y'i為各特征時點縣級行政區幾何中心距離區域重心的相對坐標;σx和σy分別為沿x軸和沿y軸的標準差。橢圓的長半軸表示數據分布的方向,短半軸表示數據分布的范圍,長短半軸的值差距越大(扁率越大)表示數據的方向性越明顯;反之,如果長短半軸越接近表示方向性越不明顯。如果為長短半軸完全相等的正圓,則表示沒有任何的方向特征。短半軸表示數據分布的范圍,短半軸越短表示數據呈現的向心力越明顯;反之,短半軸越長表示數據的離散程度越大。同樣,如果短半軸與長半軸完全相等,則表示數據沒有任何的分布特征。
近鄰分析(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該方法常用于尋找離某一個數據點距離最近點的距離。當輸入要素的最近要素是其本身時,該要素將在計算中被忽略,并將搜索除該要素之外的最近要素。采用近鄰分析計算地級市行政中心之間的最短距離(指A市政府到B市政府之間的直線距離),用以評價地級市設置的疏密程度。
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對象為中國的地級市(含副省級市),行政區劃矢量數據來源于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系統②http://bzdt.ch.mnr.gov.cn/和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③https://www.resdc.cn/Default.aspx,包括1985 和2015 年中國縣級和地市行政邊界數據,以及2020 年中國省級行政邊界數據。2020 年中國地市級行政邊界數據是在2015年地市行政邊界數據的基礎上,依據近年來調整情況進行人工修訂獲得。行政區劃調整數據主要來源于民政部全國行政區劃信息查詢平臺④http://xzqh.mca.gov.cn/map、中國行政區劃網⑤http://www.xzqh.org/html/以及歷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1979—2020)。政區數量、人口等其他數據主要來源于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1979—2021)、《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國家統計局,2010)以及行政區劃網等。由于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地級市設置多以切塊設市的方式進行且稱為“省轄市”,1983年“地市合并”“市領導縣”體制推行后,地級市設置模式由切塊設市轉為以整建制調整為主。因此,考慮到矢量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研究對象的可比性,選取1985 和2020年2期矢量數據進行分析。研究區域為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不包括香港和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以及臺灣省。
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級市設置的演化特征
2.1 時間特征
1978年以來,中國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城鎮常住人口從1978 年的1.72 億增至2020 年的9.02 億,與之相適應的城市型政區也得以廣泛設置,統縣政區逐漸由以地區建制為主的地域型政區轉向以地級市為主的城市型政區轉換。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行政區劃管理體系多為“省―地區―縣”的體制架構,城市的數量相對較少,以上下級之間的垂直聯系為主,這與計劃經濟的指令性運作保持高度一致。1978年,中國共有340個地級行政區,其中地級市有99 個,占比為29.12%;到2019 年,中國共有333 個地級行政區,地級市數量為293 個,占比為87.99%。與1978 年相比,2019 年的地級市占比提升了58.87%,共新增地級市194個。如圖1所示,新增地級市主要集中在2003 年之前,2003—2019年僅增加11個地級市,平均每年新增地級市不到1個,而1978—2003 年平均每年新增地級市7.08 個。與地級市快速增加形成明顯對比的是,地級政區數量增長十分緩慢,增速約為2年/個,加之地級市增加的數量與地區減少的數量基本相當,且數量變動曲線高度對稱,這表明大量地級市可能仍沿襲原先地區的行政區域范圍。

圖1 1978年以來中國地級政區數量變動狀況Fig.1 Changes of the number of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since 1978
地級市設置受政策因素的影響非常明顯。由圖1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級市經歷了1983和1999年2次快速增長,這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地市州黨政機關機構改革若干問題的通知》(中發〔1983〕6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意見》(中發〔1999〕2號)、《民政部關于調整地區建制有關問題的通知(民發〔1999〕105號)》等重要政策出臺的時間節點高度一致。1983年的地級市和地區數量基本相當,但地級市數量隨著相關政策的實施而開始快速增加,2003年國家指出“行政區劃調整工作涉及面廣,影響大,非常敏感,是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積極穩妥,慎之又慎,特別是要切實搞好科學論證,認真制定總體規劃,不斷提高科學化、法制化水平,避免盲目性和隨意性”⑥《民政部關于加強行政區劃調整的科學論證和規劃工作的通知》(民函〔2003〕73號)。,自此以后,地級行政區劃調整的數量開始快速減少。
綜上所述,1978年以來中國地級政區經歷了由“地區”向“地級市”轉型的重大變革,調整時間集中在1983—2003年,地級政區調整受政策因素的影響較大,且地級市建制增加與地區建制減少的2條趨勢線高度對稱(見圖1),表明大量地級市的空間格局仍沿襲原先地區建制的范圍。
2.2 設置模式
地級市的設置模式可以進一步證明上述變化趨勢。1983年,國家提出要“實行地、市合并,由市領導縣”“把新興工礦區或城鎮改為市,管轄一部分農村”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地市州黨政機關機構改革若干問題的通知》(中發〔1983〕6號)。,此后地級市的數量便開始大量增加,地級市增加與地區減少基本保持同步態勢(見圖1)。實行“地、市合并”主要是為了充分發揮城市和鄉村兩方面的優勢,緩解切塊設市等因素導致的市縣分設和城鄉分割問題,推動城鄉統籌發展。新增地級市的模式主要包括⑧數據來源:本研究依據行政區劃調整案例進行逐年統計獲取。:撤地設市、地市合并、縣或縣級市升格設市、撤盟設市等。
由表1可知,改革開放后,新增地級市的主要模式多是在原地區(盟)建制的基礎上進行調整,約占總量的80%以上,包括地區與縣、縣級市、地級市等建制進行合并,并以整建制轉換為主,即將地區改為地級市,而將縣、縣級市、地級市(多為切塊設市且面積較小的地級市)轉化為一個或多個市轄區。對于面積較大的政區,則將原縣、縣級市和地級市部分轉化為市轄區,另一部分轉化為縣。對于縣或縣級市升格設市模式,雖然是在非地區駐地設立地級市,但一般都在原地區的范圍內進行調整,即原地區由于面積偏大而不宜整建制改為一個地級市,就在原地區范圍內選擇發展條件較好的縣或者縣級市設立新的地級市,如潮州、揭陽和汕頭3 個地級市都是在原潮汕地區的基礎上設立的。這些特征均表明地級市設置仍延續原地區建制的基本格局,且行政區劃調整多是集中在地級行政邊界內部的整建制調整。

表1 “地市合并”改革后新增地級市的主要模式Table 1 Main models of newly adde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2.3 沿革關系
為準確認識地區與地級市建制轉換之間的內在關聯,采用政區相似系數法進行論證。在對同一政區進行配對的基礎上,共統計到有效樣本293 個,占2020年地級政區總量的88%,其中包含252個地級市,占地級市總量的86%。由圖2 可以看出,政區相似系數高度集中在1左右,其中,有71%地級政區的政區相似系數集中在0.9~1.1。這表明地級市的行政區劃設置與原地區高度相似,除部分地級市外,大多數地級市沿襲了原地區建制的行政管轄范圍。

圖2 1985—2020年中國地級政區面積變動的核密度估計Fig.2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changes in administrative are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during 1985-2020
中國地級政區存在著高度的延續性和相似性,地級市是在原地區建制的基礎上逐漸演化的結果,而地區建制又高度沿襲了歷史上的統縣政區范圍。“1913 年,國民黨政府廢除明清王朝‘府’的建制后,在省、縣之間設立了‘道’”,“北伐戰爭結束后又改道為‘專員公署’”,“1949 年新中國成立后,承襲了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專署設置”,1967 年“把專區改稱地區”(錢其智,2000),1983 年“地市合并、市領導縣”改革后,地區開始逐步轉化為地級市。由此可知,當前的地級市與原地區建制高度相似,地區是由專區“改稱”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專區又是“承襲”著“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專署設置,而中華民國時期的“行政督察專員區公署制與明清時期的‘道’有著十分密切的淵源關系”(張小穩,2010)。以晉東南地區為例(圖3),自秦代以來晉東南地區在秦、西漢、東漢、西晉等朝代的統縣政區(即當代的地級政區)都是上黨郡,到隋代原上黨郡分為上黨郡和長平郡,這種行政區劃格局一直保存至今(圖3-f~k),尤其是澤州與現在的晉城市在行政區劃上高度相似。綜上可知,當前地級市行政區劃格局具有高度的傳承性。

圖3 晉東南地區行政區劃演化過程Fig.3 Ev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Southeast Shanxi Province
2.4 空間特征
中國地級市設置經歷了由沿海向內陸逐漸推進的過程(圖4-a),設市時間在36 a以上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以及內陸的省會城市周邊,而除呂梁等個別地級市外,設市時間在20 a以下的城市均位于西部省份。改革開放以來,大部分地級市的設市時間都在21~35 a,并且多位于胡煥庸線以東地區。目前,除新疆(5 個)、西藏(1 個)、黑龍江(1個)三省區外,中東部已不存在地區建制。

圖4 1978年以來中國新設地級市的城市年齡及其分布特征Fig.4 The urban age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ewly establishe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since 1978
由圖4-b 可以看出,1978 年以來,新設地級市的重心明顯呈現逐步向西遷移的特征,設市時間在36~42 a 的橢圓明顯更偏北偏東分布,隨后不斷向西部遷移,設市時間在0~10 a的橢圓都分布在西部地區。由此可知,改革開放后,中國地級市設置經歷了從“沿海和內陸省會城市”到“中西部地區”再到“西部地區”的自東向西逐步推進的過程。
就具體區域而言,地級市設置由沿海向內陸推進的態勢也十分明顯。以廣東省及其周邊地區為例(圖5),明顯存在“36~42 a”“31~35 a”“11~30 a”3條等時線,其中“36~42 a”等時線以東城市的設市時間多在36 a以上,主要包括均位于沿海地區的汕頭、深圳、珠海、湛江、漳州等城市,這段時間在相繼撤銷了佛山地區、汕頭地區、湛江地區和龍溪地區的基礎上,設立了地級市并實行市管縣體制。“31~35 a 等時線”以東城市的設市時間多在31a 以上,如梅州、清遠、肇慶等城市,這段時間廣東省相繼撤銷了肇慶地區、惠陽地區和梅縣地區,并在原惠陽地區縣級河源市的基礎上成立地級河源市,在原汕頭地區海豐、陸豐兩縣的基礎上成立地級汕尾市。“11~30 a等時線”兩側多為設市時間在11~30 a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廣東省周邊地區,如龍巖、贛州和郴州等市,江西、廣西等省區的地改市多集中在近30 a以內。總體上,中國的地區改地級市初期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然后逐步向中西部推進,當前這波浪潮已到西部沿邊地區。

圖5 1978年以來廣東省及其周邊地區新設地級以上城市的設市時間Fig.5 The establishment time of prefecture-level or above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since 1978
3 地級市空間分布存在的主要問題與基本邏輯
綜上可知,地級市基本延續了原地區建制的空間范圍。由于在設置地級市的過程中,有些城市的經濟中心地位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少數城市是在各地希望升格的大環境中形成的,故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地級市設置的“空間”問題開始日益凸顯。
3.1 地級市空間分布存在的主要問題
3.1.1 地級以上行政中心設置過近的問題 由于在地級市設置的過程中,主要采取撤地設市、地市合并、縣或縣級市升格設市等方式,并且多選擇經濟較發達的縣市進行改革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地市州黨政機關機構改革若干問題的通知》(中發〔1983〕6 號)指出“把新興工礦區或城鎮改為市,管轄一部分農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地市州機構改革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中發〔1983〕44號)指出“現有的地轄市中,有的在經濟上和其他方面都已有相當規模(如工業產值在四億元左右,非農業人口在十五萬左右),并且很有發展前途。為了更好地發揮這些城市的作用,可以將其升格為省、自治區轄市”。,而這些城市往往是工礦城市或距離中心城市較近的城市,這造成部分地級市之間距離過近,即在短距離范圍內存在多個地級市的問題,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成本增加。本研究采用近鄰分析法測度了中國地級及地級以上城市與鄰近城市中最近城市之間的距離,發現共19個城市與周邊城市的最近距離不足30 km,其中鄂州市與黃岡市距離不足10 km,距離在50 km 以下的城市共有65 個,占設區市總量的1/5 以上。如圖6所示,最近鄰距離<50 km 的城市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及遼寧省等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多分布在省級政區邊界處。地級市空間距離過近,使中心城市的腹地相互重疊,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爭奪人口、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問題,隨著城市間人口和產業聯系日益密切,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成本也將快速提升。

圖6 地級及地級以上城市與周邊城市的最近距離Fig.6 The nearest distance betwee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surrounding cities
以西安-咸陽為例,兩市行政中心之間的直線距離不足25 km,由此產生了諸多問題,主要體現在:1)西安市中心城區人口壓力過大。由于與咸陽距離過近,西安難以跨過渭河向北發展,而西安向南約30 km 則是秦嶺保護區,因而人口和產業在中心城區過度集聚,難以向外有序疏解。新城區、碑林區和蓮湖區一共才92 km2,卻集中了超過200萬的常住人口,人口密度>2 萬人/km2,存在明顯的人口壓力過大的問題。由于中心城區管理壓力過大,不得不采取設置功能區等方式進行疏解,既包括中心城區內部集中的3個市轄區以及多個功能區(如城墻管委會、火車站管委會等),以及市里各委辦局“條條部門”的垂直管理,也包括跨渭河向北設置的西咸新區。2)西咸新區管理體制不順。雖然西咸新區已歸西安市管理,但部分區域在行政區劃意義上仍屬于咸陽市管轄,國家按行政區劃制定的各種指標、規劃、任務、補貼等難以直接下達到西咸新區,加之西咸新區地跨西安市和咸陽市,兩市的地鐵、公交以及道路等基礎設施在銜接上也存在一些問題,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兩市之間的要素流通成本。3)咸陽城市衰落問題。西咸新區歸西安市管理后,咸陽市轄區東、北、南三面被西安市包圍,僅直管秦都區和渭城區的4個街道,自身發展的空間和潛力都相對有限(趙彪,2019)。2010—2020年,咸陽市常住人口由489.5萬人降至396.0萬人,常住人口減少93.5 萬人,城鎮化率僅為55.44%,且比全國平均水平低8.45%,全市人戶分離人口占常住人口總量的23.04%⑩數據來源包括:咸陽市統計局.2011.http://tjj.xianyang.gov.cn/tjgz/tjxx/201107/t20110728_544229.html;http://tjj.xianyang.gov.cn/tjgz/tjxx/202105/t20210528_544242.html。中國政府網.2021.http://www.gov.cn/xinwen/2021-05/11/content_5605791.htm。,這都表明咸陽城市發展正面臨多重挑戰。
3.1.2 “小馬拉大車”與“大馬拉小車”的問題
由于在地區改地級市的過程中,多考慮將地區所在地或經濟發展較好的縣或縣級市升格,而這些城市往往分布在中心城市周邊,距離中心城市較遠的地區(尤其是省界地區)往往難以受到中心城市的輻射,進而會產生“小馬拉大車”與“大馬拉小車”的問題。“小馬拉大車”是指地級市輻射帶動能力有限,無法帶動所轄縣市的經濟社會發展,主要包括2種情況:1)在地級市設置的過程中,將部分經濟實力較弱的縣或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而設立后的地級市又無法有效帶動地區經濟發展,這類城市在市管縣體制下一般具有更突出的“市刮縣”“市卡縣”等問題;2)由于部分區域地級市建制較少,一個地級市管轄范圍過大,而在地改市、地市合并時由于多種原因僅設置了一個地級市,造成部分縣(市)難以輻射帶動。如陜西的農業大市渭南市,對渭北地區的合陽等縣的輻射作用十分有限,難以有效推動關中平原東北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大馬拉小車”是指在地改市之后,由于部分市轄區發展相對緩慢,而在地級市內部存在一個發展速度較快的縣或者縣級市,更是加劇了市縣之間的矛盾問題,如浙江的金華市和義烏市之間的體制矛盾。
綜上,在地級市設置的過程中,改革開放前后呈現2種不同的設置模式,改革開放前多是切塊設市的模式,而改革開放后則以整建制調整為主,這是導致當前地級市設置問題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地級市設置過近的問題。由于兩個地級市距離過近,容易產生兩城市腹地重疊、發展空間受限、協調成本偏高等問題,抬高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成本,如兩市距離過近常會出現人口流動頻繁的現象,但由于分屬兩市,使兩地之間的公共服務設施往往難以有效滿足現實需求。另一方面,是“小馬拉大車”與“大馬拉小車”的問題。由于在新設地級市的過程中,多采用地市合并等方式進行,故難以有效識別潛在的經濟增長極,這使部分地級市出現了市弱縣強、弱市帶多縣等“小馬拉大車”問題,以及強市帶少縣等“大馬拉小車”問題,提高了行政區與經濟區協調的難度和成本。此外,切塊設市模式還導致了郊區(縣)包圍城區、市縣同城等問題,如許昌市魏都區被建安區包圍,晉城市城區被澤州縣包圍并且澤州縣長期寄治在晉城市城區。改革開放前設立的省轄市大多存在此類問題,包括廣州市(番禺縣)、杭州市(余杭縣)和南京市(江寧縣)。這種郊區(縣)包圍城區的“蛋黃結構”,造成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人為分割,容易產生中心城市發展空間不足、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難以提升等問題。
3.2 地級市空間分布存在的主要邏輯
空間和尺度是解釋行政區劃的2個重要關鍵詞。作為空間政治經濟學的前沿理論,空間生產、尺度重組、地域重構等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理論不斷得到國內學者的引介和應用(殷潔 等,2013;莊良 等,2019)。空間的生產主要是指資本、權力和階層與空間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的過程,尺度重組則是指權力和控制力在不同尺度之間的變動,而資本不斷重復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2個過程通常被稱為地域重構(Harvey, 1973; Brenner, 1999; Shen,2007)。行政區劃中的尺度重組實質上是指特定行政區空間對資本控制力的尺度轉移,如國家借助尺度重組促進地級市權力與制度的重新安排乃至城市空間結構的轉變。全球化導致行政空間和地理尺度成為社會博弈的關鍵場所,不同等級的政區也是被不同社會階層主體占領的空間,其空間范圍大小不一。國家通過劃定省市縣的多尺度政區邊界,將范圍較大的行政區域劃分為更多較小且等級化的地域單元,從而使各級政府之間實現自上而下的權力配置和自下而上的權力集中,進而提高國家的行政效率和治理效能。可見,地級市等行政區劃調整的策略與手段即是國家為使某一政區得以尺度重組或地域重構而發生的治理實踐。中國在相互交織的全球化與地方化過程中,“國家-省區-地市-區縣”多尺度行政區劃的地方條件仍對全球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資本等要素通過權力附著在有界且相對靜止和固定的政區空間,進而實現地域化、去地域化以及再地域化的過程。因此,城市政區的空間規模不是恒久固定的,而需按照其發展的程度、內容、相對重要性及相互關系而不斷重新定義、競爭和重建(Swyngedouw, 2018)。作為空間治理政策工具的行政區劃本身就是一種重要資源(Feng et al., 2021)。本研究認為中國地級市的行政區劃調整有其內在的空間政治邏輯(圖7)。國家在快速推進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實踐中,加快實現了虛級的城市型政區向實級的地域型政區轉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開發區與行政區政策的交互驅動下,地級市逐漸成為地級行政區的空間主體并呈現城鄉二元的“中心-外圍”空間結構。伴隨著鄉村地域(以縣和縣級市等縣級行政區為主)向城市地域(以市轄區為主)的快速空間轉變,地級市的城鄉差異表現為明顯的核心-邊緣、東中西向和南北向的空間格局。加之地方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城市間或區域內的合作趨勢日益凸顯,跨界合作成為地級市優化行政區劃調整的重要訴求。特別是在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區域一體化國家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等背景下,地級市亟需通過區劃調整的創新思路,破解其行政中心設置過近、“小馬拉大車”與“大馬拉小車”等主要問題。

圖7 中國地級市行政區劃調整的空間邏輯Fig.7 The spatial logic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in China's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當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矛盾不斷積累以及要素的跨界流動發生阻滯時,城市空間必須實現適當轉型以促進產業和人口等要素的尺度重組。與此同時,行政區劃使得權力解綁于原先的社會經濟關系并重新進行地域重構,最終通過地級市的階段性優化調整實現新的空間生產。未來的行政區劃調整工作應重視考慮提升地級市合理的規模效應以及區域之間的互動效應,地級市的政區優化設置更應在一定程度上尊重開發區等功能性城市區域的邊界與范圍。
4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采用政區相似系數、標準差橢圓等方法,探討了地級市設置的空間特征及存在的問題,得到的主要結論包括:1)中國地級市基本延續了原地區建制的空間范圍,受政策因素的影響較大,且多是在地級市、縣級市或縣的基礎上進行的地區改地級市,明顯呈現自東向西、由沿海向內陸逐漸推移的過程;2)改革開放后,新增地級市多是在原地區(盟)建制的基礎上進行的調整,包括撤地設市、地市合并、縣或縣級市升格設市、撤盟設市等;3)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地級市設置的“空間”問題開始日益突出,,主要包括地級以上行政中心設置過近以及“小馬拉大車”與“大馬拉小車”等問題,這與地級市設置的過程密切相關;4)在工業化與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地級市逐漸成為實級的地域型政區,并呈現出城鄉二元的“中心-外圍”空間結構,導致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不斷積累以及要素的跨界流動發生阻滯,城市空間必須實現適當轉型以促進產業和人口等要素的尺度重組,這是地級市行政區劃調整的基本邏輯;5)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在突破地級行政邊界的限制,地級市設置的“空間”問題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成本,應適時開展地級行政區劃的調整改革。
中國地級市空間分布生成于工業化與城鎮化背景下的地域型政區,發展于城鄉差異與跨界合作的戰略轉型中,并在地域重構與尺度重組中面臨區劃調整的創新挑戰。與傳統的西方國家不同,中國行政區劃制度具有自身的歷史演化邏輯,行政區劃建制設置的布局直接影響著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行政效率的提升,科學合理的行政區劃調整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具有重要影響。隨著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基于傳統地區建制基礎上的地級市設置,越來越難以滿足新階段的發展需求,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地級市數量多、距離近、建制缺失以及規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亟需從戰略層面進行頂層規劃。應改變整建制調整、地級政區內部調整等思路,從更大范圍統籌考慮生產力布局,對行政層級、政區規模、空間結構進行整體思考,針對國家和地方發展的實際需求進行綜合施策,提出城市問題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成熟一個、推動一個,必要時可開展跨地級邊界的行政區劃調整。這對調整和優化中國經濟空間結構,在更大范圍內集中、有效、合理地配置生產要素,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研究可能的文獻貢獻體現在運用政區相似系數揭示了“地級市與原地區高度相似”,而當前地級市設置存在著距離過近、小馬拉大車等問題均與此相關,最后提出并呼吁未來應高度重視地級市行政區劃調整的重大意義;可能存在的不足是地級市行政區劃調整的空間邏輯與創新思路有待具體深化,在今后的研究中應加強對地級市相關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