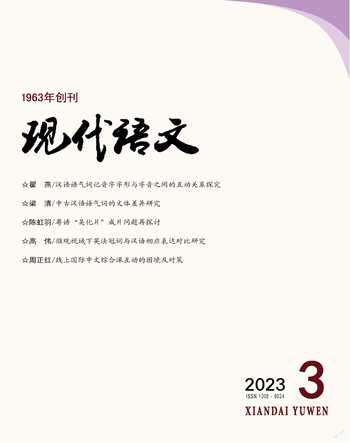《故訓匯纂》校讀札記
劉純 李玉平

摘? 要:《故訓匯纂》是當代學者宗福邦等先生主持編纂的一部高質量的大型辭書,匯集了豐富的故訓資料,由于所涉典籍資料浩繁,在整理過程中難免會有所疏失。以《故訓匯纂》所引鄭玄箋注資料相關條目為主,將其疏漏情況大致分為五類:漏收、誤收、脫文、衍文、訛文,并以舉例的方式加以辨析、考釋。希望通過這一研究,能為辭典使用者或辭典的修訂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故訓匯纂》;鄭玄;疏失;校讀
《故訓匯纂》(以下簡稱《故訓》)[1]是當代學者宗福邦等先生主持編纂的一部高質量的大型辭書,編者歷時十八年,為當代學人提供了豐富的故訓資料,厥功甚偉。該書曾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一等獎等。不過,在使用《故訓》的過程中,學者們也陸續發現了一些問題,并予以專門探討[2]-[10]。同時,我們也發現此書中仍存在著一些編校疏失。有鑒于此,本文以《故訓》所引鄭玄箋注資料相關條目為主,將其疏漏情況大致分為五類:漏收、誤收、脫文、衍文、訛文,并以舉例的方式加以辨析、考釋。希望通過這一研究,能為辭典使用者或辭典的修訂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需要說明的是,《故訓》所收資料均為繁體中文,本文亦一如其舊;為了保持行文的一致性,本文在引用相關古籍時,也采用繁體格式。
一、漏收
就《故訓》的漏收類型來說,又可以細分為三種情況:漏收字目、漏收訓釋或訓釋材料來源、漏引《說文解字》材料。
(一)漏收字目
在《故訓》中,存在著因漏收字目而導致訓釋資料缺失的現象。如《故訓》中并未收錄“朐”字,則該字的訓釋資料亦失收。《儀禮·士虞禮》:“朐在南。”鄭玄注:“朐,脯及乾肉之屈也。”[11](P1174下)《禮記·曲禮上》:“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鄭玄注:“屈中曰朐。”[11](P1242上)《故訓》未收“朐”字,而導致相關訓釋資料的失收。
(二)漏收訓釋或訓釋材料來源
在《故訓》中,亦存在著漏收語詞訓釋或訓釋材料來源的情況。例如:
1.第55頁“于”字訓條下失收:“~嗟者,美之也。《詩·召南·騶虞》:‘~嗟乎騶虞!鄭玄箋”。
2.第2478頁“?”字訓條10下失收:“《詩·小雅·采芑》‘鉤膺~革鄭玄箋”。
3.第231頁“則”字訓條7下失收:“《詩·魯
頌·泮水》‘維民之~鄭玄箋”。
(三)漏引《說文解字》材料
按照《故訓》的體例,所收錄語詞訓釋,凡是有《說文解字》說解資料的,一般都要納入。在使用過程中,我們發現,《故訓》中也有漏引《說文》材料的情況。第224頁“別”字、第241頁“劓”字、第500頁“奪”字、第1004頁“旜”字、第1871頁“膟”字下,皆漏引《說文》材料。如《說文》之《冎部》:“(別),分解也。從冎從刀。”《刀部》:“?,刑鼻也。從刀臬聲。《易》曰:‘天且?。劓,臬或從鼻。”《奞部》:“奪,手持隹失之也。從又從奞。”《?部》:“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從?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旃。旜,旃或從亶。”《肉部》:“,血祭肉也。從肉帥聲。膟,或從率。”
二、誤收
在《故訓》中,由于編者對文獻訓釋內容理解有誤,或者是將訓釋作者弄錯,從而出現了誤收訓條的情況。例如:
1.第1983頁“薺”字條第3條訓釋:“薺,亭藶之屬。《古文苑·董仲舒〈雨雹對〉》‘~麥枯章樵注引《月令注》。”核查原書,《古文苑》卷十一:“《雨雹對》‘薺麥枯由隂殺也宋章樵注:‘《月令》:“孟夏,靡草死,麥秋至。”注:“靡草,薺、亭歷之屬。”薺、麥,蓋二物也。”又核查《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鄭玄注:“舊說云:‘靡草,薺、亭藶之屬。”孔穎達疏:“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由此可知,“薺”與“亭藶”是并列的兩種不同植物,二者都屬于“靡草”,而不是說“薺”是“亭藶”之類的植物。這條訓釋,是由于《故訓》編者對注釋材料的誤解而收入的。
2.第1626頁“稍”字條第9條訓釋:“大禮曰旬,旬之外爲~。《易·豐》‘雖旬無咎鄭玄注。”《故訓》所依據的是南宋王應麟輯、清代惠棟增補本《鄭氏周易注》,原文作:“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
稍.久留非常.(詩有客正義).”[12](P41)這里的斷句較粗。參考標點本《毛詩正義》,此處斷句為:“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
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爲限。
《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13](P1341)、[14](P1973)又核查《儀禮·聘禮》,此處原文作:“夕,夫人歸禮。既致饔,旬而稍。”賈公彥疏:“云‘既致饔,旬而稍者,以其賓客之道,十日爲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逢兇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即有稍禮。”[15](P467)孔穎達《毛詩正義》引《儀禮·聘禮》此文后云:“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14](P1973)可見,鄭注中解釋的是“畢歸大禮曰‘旬而稍”,而不是“大禮曰‘旬”。《故訓》所收訓條斷句有誤,實際上,《故訓》
“旬”字下也并未收錄“大禮曰旬”這條訓釋。
3.第111頁“供”字條第25條訓釋:“~,謂大也。《尚書大傳》卷‘維時~祀六沴鄭玄注。”此條《尚書大傳》的卷數缺失。《故訓》所依據的《尚書大傳》本為叢書集成初編本(清陳壽祺輯校),原文作:“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鄭注:“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16](P62)可知,鄭玄是以“大”釋“洪”字,原文在卷二。故此條訓釋本應列在第1250頁“洪,大也”下,而《故訓》誤列于“供”字條下。
4.《故訓》中有多處將本是鄭箋的訓釋內容當
作毛傳的訓釋收入。如第76頁“亶”字條第7條訓釋下“~,誠也……《大雅·生民》‘胡臭~時毛傳”[14](P1549),第546頁“孔”字條第19條訓釋下“~,甚也……《采薇》……‘玁狁~棘毛傳”[14](P841),第1117頁“棘”字條第36條訓釋下“~,急也……
《小雅·采薇》‘玁狁孔~毛傳”[14](P841),第1633頁“穀”字條第28條訓釋下“~,善也……《大雅·桑柔》‘不胥以~毛傳”[14](P1734),第1744頁“綏”字條第24條訓釋下“~,安也……《周頌·桓》‘~萬邦毛傳”[14](P2020),第2471頁“靡”字條第41條訓釋下“~,無也。《詩經·邶風·泉水》:‘有懷于衛,~日不思。毛傳”[14](P225),以上各條中的“毛傳”皆當為“鄭玄箋”。
三、脫文
由于編校疏失,《故訓》中存在著部分引文或標注引文出處的字、詞、句或標點脫漏的情況。例如:
1.第542頁“嬪”字下第27條訓釋中標注出處時稱“鄭玄注引鄭司農”,按照《故訓》體例,一般是標注為“鄭玄注引鄭司農云”,該條當脫“云”字。
2.第585頁“富”字下第31條訓釋“‘維昔之~鄭玄箋”,當作“‘維昔之~不如時鄭玄箋”,脫“不如時”三字,屬于截取詞句不完整。
3.第977頁“文”字下第239條訓釋“《周禮·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鄭玄注‘瑑,~飾也孫詒讓正義引《典瑞》引先鄭云”,其中的“《典瑞》”當作“《典瑞》注”,《故訓》脫“注”字。
4.第1976頁“薦”字下第53條訓釋“倪璠注鄭康成《庖人》注”,當作“倪璠注引鄭康成《庖人》注”,脫“引”字。
5.第1976頁“鰥”字下第7條訓釋“‘國無鰥民鄭玄箋”,當作“‘國無鰥民也鄭玄箋”,脫虛詞“也”字。又第667頁“帝”字下第23條訓釋“帝,五帝”引《詩·鄘風·君子偕老》“胡然而帝也”鄭玄箋,此處鄭箋原文本作:“帝,五帝也。”故此訓條收錄材料亦是漏掉虛詞“也”。
6.第2345頁“酺”字下第12條訓釋“《周·地官·族師》‘春秋祭~亦如之鄭玄注”,其中書名脫“禮”字,當作“《周禮·地官·族師》”。
7.第469頁“大”字下第391條訓釋“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尚書大傳》卷‘大室有事鄭玄注。”其中《尚書大傳》的卷數缺失。《故訓》所依據的《尚書大傳》本為叢書集成初編本(清陳壽祺輯校),原文作:“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鄭注:“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16](P91)可知,鄭玄所注原文在卷二,訓條中“卷”后脫“二”字,并且所注正文“大室有事”訛誤,當為“大宗已侍於賓”。
8.第285頁“即”字下第5條訓釋中引用注釋文獻“《詩·衛風》‘來~我謀鄭玄箋”,其中的篇目名稱,按照《故訓》體例,當作“《詩·衛風·氓》”,“衛風”二字后脫漏“·氓”。
9.第1223頁“汔”字下引《說文》原文時“《說文·水部》”后少了冒號“:”。
10.第1931頁“茲”字下第8條訓釋“《大雅下武》‘媚~一人鄭玄箋”,其中的“《大雅下武》”當作“《大雅·下武》”,中間脫標點“·”。
11.第2128頁“諏”字下第1條訓釋“《儀禮特牲饋食禮》”,當作“《儀禮·特牲饋食禮》”,中間脫標點“·”。
12.第404頁“圈”字下第30條訓釋“~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禮記·玉藻》‘母沒而杯~不能飲焉鄭玄注”,“屈木所爲”之前漏加標點逗號,應該是“~,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
四、衍文
由于編校疏失,《故訓》中也存在著部分標注引文出處的字詞或標點衍文的情況。例如:
1.第271頁“十”字下第16條訓釋“《考記記·匠人》”,應為“《考工記·匠人》”。《周禮》中有《考
工記》,寫成“考記記”,當因鄰近字干擾而產生的衍文。
2.第1015頁“昏”字第57條訓釋,句尾多了一個右雙引號”。
3.第1144頁“槱”字下引《說文》原文:“《說文·木部》:‘……詩曰“薪之~之。”“薪之~之”前衍一個左雙引號“。
4.第1661頁“端”字下第82條訓釋“|《禮記·玉藻》”,其中的“|”為誤衍的符號。
五、訛文
由于對訓釋材料的分析失誤以及編校不夠嚴謹,《故訓》中還存在著部分注音、字形、句讀等方面的訛誤情況。
(一)注音校對失誤或分析失誤
在《故訓》中,有的注音屬于校對失誤,如第241頁“劉”的注音liù當為liú,第1912頁“芥”的注音jià當為jiè,第2291頁“逵”的注音kuǐ當為kuí,第2456頁“雹”的注音bào當為báo等。不過,也有的是屬于注音分析失誤。例如:
1.第2250頁“輅”字下讀音只列有一個:“《集韻》轄格切,入陌,匣。”音hé。據《漢語大詞典》注音可知,“輅”其實還有另外兩個讀音。一是:“《廣韻》洛故切,去暮,來。”音lù;二是:“《集韻》魚駕切,去禡,疑。”音yà。因此,《故訓》編纂者將所有義項都列在hé音下,是不適當的。如訓條11、13、14、15、16、17、18、19、20、21、26、27、35、37、38等的注音皆當為lù,而不是hé。
2.第1719頁“純”字下有“(五)zī”音。該音下收錄了不少有關鄭玄注釋的資料及贊同鄭注意見的資料,即認為“純”當為“緇”的古字“?”之誤字。不過,在此音下第149和第150條,卻收入了清代王引之《經義述聞》中的兩條釋義。一條作:“純者,黗之借字也。純字自有黑義,無煩改讀爲緇。”一條作:“純,當讀黗。”這兩條材料,按照王引之的觀點,“純”的讀音當同“黗”,音tūn。因此,這里應當補列一個讀音tūn,即《故訓》第2628頁下“黗”的注音:“《廣韻》他昆切,平魂透。諄部。”
3.第2557頁“骴”的注音為zì,其所引《廣韻》注音則為:“疾移切,平支從。支部。”由此可知,該字讀音應為平聲,不為去聲。《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王力古漢語字典》皆注音為cī,這是對的。
4.第1871頁“膞”的注音(二)為chuǎn,其所引《集韻》注音則為:“淳沿切,平仙禪。元部。”由此可知,該字相應義項之讀音應為平聲,不為上聲。當從《漢語大詞典》《王力古漢語字典》注音為chuán更恰當。
(二)音同或音近而致誤
在《故訓》中,由于有些字的讀音相同或相近,可能在錄入時采用拼音輸入法而導致失誤。例如:第1028頁“晤”下訓條7“可以~歌”,其中的“以”應為“與”之誤;第1059頁“朔”下訓條14“《儀理·大射》‘~鼙在其北”,其中的“儀理”當作“儀禮”;第1935頁“莫”下訓條49“《角弓》‘~肯下違”,其中的“違”應為“遺”之誤;第2611頁“鸞”字下引《說文》原文“從鳥、鸞聲”,當為“從鳥、?聲”。
(三)新造訛字
在《故訓》中,有些資料使用的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此本字體較小,個別字形不夠清晰,從而導致編者新造出字典中并沒有的字。例如:
1.第366頁“喪”下訓條56“~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輔之屬。《周禮·地官·鄉師》‘族共~器鄭玄注。”細審原文,其中的“”當作“輁”;又核查其他版本的《周禮注疏》,皆作“輁”。字典辭書中并無“”字,因此,該字應為編纂者對“輁”識別有誤而新造的訛字。
2.第1100頁“桁”字下“~,所以苞筲罋甒也。”核查《儀禮·既夕禮》“皆木桁”鄭玄注原文,“”
當作“庪”。“”字不見字典辭書,因此,該字應為編纂者對“庪”識別有誤而新造的訛字。
(四)形近而致誤
這是由于字形相近,校對不夠細致而造成的失誤。在《故訓》中,此類情況最多,我們共發現20處。
1.第56頁“于”下訓條86“《詩·召南·采繁》‘~以采蘩鄭玄箋”,其中的“采繁”當為“采蘩”之誤。
2.第95頁“任”字下注音內容“(一)rèn《廣韻》汝鳩切,去沁日。侵部。”其中的“鳩”當為“鴆”之誤。
3.第192頁“公”下訓條159“《詩·召南·采繁》‘夙夜在~鄭玄箋”,其中的“采繁”當為“采蘩”之誤。
4.第338頁“和”下訓條131“《後漢書·斑固傳》”,其中的“斑固”當為“班固”之誤。
5.第406頁“圜”下訓條15“《周禮·考工記·輪入》‘取諸~也”,其中的“輪入”當為“輪人”之誤。
6.第426頁“埴”下訓條23、24、26中“《周禮·考工記·總目》‘搏~之工”中的“搏”,皆為“摶”之誤。
7.第509頁“好”下訓條89“《周禮·天官·內饗》”,當為“《周禮·天官·內饔》”。《周禮·天官》中有《內饔》篇,無《內饗》篇。
8.第530頁“婦”下訓條55“~職,謂職紝組紃縫線之事”,其中的“職紝”當為“織紝”之誤。
9.第573頁“宮”下訓條143“《周禮·天宮·小宰》”,當為“《周禮·天官·小宰》”。
10.第631頁“山”下訓條7“《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林川澤丘陵墳衍原濕之名物鄭玄注”,其中的“濕”當為“隰”之誤。
11.第641頁“崇”下訓條45“《衛風·河廣》‘曾不~期鄭玄箋”,其中的“期”當為“朝”之誤。
12.第659頁“已”下訓條36“昊天泰憮”,其中的“憮”當為“幠”之誤;第1236頁“泰”下訓條33“昊天大憮”,其中的“憮”當為“幠”之誤。
13.第680頁“幬”字下“《說文·巾部》:‘~,禪帳也。”核查《說文》原文,其中的“禪”當為“襌”之誤。同樣,“幬”字下訓條1“~,禪帳也”,其中的“禪”亦為“襌”之誤。
14.第966頁“敬”字引《說文》材料“~,肅也。從攴、茍。”其中的“茍”當為“茍”之誤。
15.第1174頁“歌”下訓條33“~以訉之”,其中的“訉”當為“訊”之誤。
16.第1426頁“猶”下訓條74“之子可~”,其中的“可”當為“不”之誤。
17.第1654頁“竈”字引《說文》材料:“《說文·穴部》:‘,軟竈也。”其中的“軟”當為“炊”之誤。
18.第1782頁“繹”下訓條71“《詩·大雅·常武》‘徐方~驛鄭玄箋”,其中的“驛”當為“騷”之誤。
19.第1825頁“考”下訓條6“《小雅·湛露》‘在宋載~鄭玄箋”,其中的“宋”當為“宗”之誤。
20.第2449頁“雜”下訓條23“《禮記·王藻》‘~帶鄭玄注”,其中的“王藻”當為“玉藻”之誤。
(五)鄰近信息干擾而致誤
《故訓》中存在著因上下文相關信息干擾而導致的引文或引文出處疏失。例如:
1.第24頁“並”下引《說文》材料:“《說文·立部》:‘~,併也。從二立。”實際上,“並”在《說文·竝部》,《故訓》很可能因后文“從二立”而誤作“立”部。
2.第39頁“之”下訓條130“《衛風·伯兮》‘~子無裳鄭玄箋”,其中的篇名錯誤,當作“《衛風·有狐》”。致誤原因當是《衛風》中《伯兮》在《有狐》之前,二篇相鄰,十三經注疏本在《伯兮》詩末尾有“伯兮四章章四句”的說明,整理者誤以為這段話是說明后面《有狐》一詩的,因而將篇名弄錯。
3.第1879頁“自”字下第5條訓釋“《詩·大雅·江漢》‘~召受命鄭玄箋”,當為“《詩·大雅·江漢》‘~召祖命鄭玄箋”之誤,可能是受到上一句“于周受命”的干擾,而導致下一句的“祖命”也訛為“受命”。
(六)句讀失誤
《故訓》中存在著因斷句不當而導致的標點疏失情況。例如:
1.第1230頁“沂”字下引《說文·水部》:“~,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從水,斤聲。”此處所引《說文》斷句有誤。依此斷句,則沂水源自東海郡費縣,然后從東西兩個方向注入泗水。試想一下,一條河流怎么可能從兩個相反的方向注入另一條河流呢?因此,這里應斷句作:“~,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只有這樣,才是合乎常理的。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即如此斷句[17](P1520)。
2.第1872頁“膮”下訓條6“膷、臐,~,今時臛也。”當標點為“膷、臐、~,今時臛也。”其中,“臐”后的“,”當作“、”。因為膷是牛肉羹,臐是羊肉羹,膮是豬肉羹,三者屬于并列關系,而臛為肉羹的總稱,這里是對三種肉羹的解釋。
3.第1831頁“耜”下訓條13“~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田器”后應加逗號以斷句,作“田器,”。
(七)繁簡字/異體字校對致誤
《故訓》編纂時采用的是繁體字,但在資料處理過程中,有時會出現繁簡字、異體字照應不周的現象。例如:
1.第256頁“勳”字下引《說文》原文:“勛,古文~從員。”其中的“員”寫作簡體字,當作“員”。
2.第1636頁“稾”下注音:“(三)gào《集韻》居號切,去號見。”其中的“號”寫作繁體字,核查《集韻》原文,作“居號切”,當據改。
3.第1364頁“煩”字下引《說文》原文:“從頁,從火。”按照《故訓》體例,當作“從頁,從火。”
4.第2572頁“鬷”下訓條4“~,總也”,核查原書,“總”本作“揔”,“總”“揔”二字為異體字關系,此處當據改。
(八)其他訛文類型
1.訓條分合處理失誤。如第1452頁“理”下訓條78、79,訓義都是“理,治獄官也”。按照《故訓》體例,應合并為一個訓條,此處卻誤分為兩條。
2.被釋詞設置失誤。如第673頁訓條131:“常服,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詩·小雅·六月》‘載是~服鄭玄箋。”實際上,鄭箋并未直接將“常服”作為被釋詞解釋,因此,《故訓》將“常服”直接列為被釋詞是不恰當的。按照該書體例,應當處理為:“(~服),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詩·小雅·六月》‘載是~服鄭玄箋。”這樣才符合體例要求。
3.反切用字“切”訛為釋義用字“也”。如第1489頁“畚”字下注音內容“běn《廣韻》布忖也,上混幫。諄部。”核查原文,“畚”字在《廣韻》的注音為“布忖切”。可見,《故訓》編者將反切用字“切”訛作釋義用字“也”。
4.版本用字差異而致誤。第659頁“已”下訓條36“‘昊天泰幠鄭玄箋”,當作“‘昊天大幠鄭玄箋”。這里的“大”,有的版本作“泰”,而阮元校勘本作“大”。《故訓》應與它所使用的版本——阮元校勘本保持一致。
《故訓匯纂》的出版,誠如許嘉璐先生在該書序言中所說的那樣:“這是訓詁學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切研究古代典籍與文化者的一大福音。”[1](序,P3)王寧先生在序言中也稱贊此書“不但篇宏幅巨,而且注意信實”[1](序,P6)。因此,該書甫一面世就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好評,成為研究古代語言文字、閱讀古代文獻典籍的必備參考。該書《前言》中說:“避免訛誤是我們努力以求的目標。《經籍籑詁》訛誤過多,前人對此早有批評,而其錯誤,又貽誤了后來的學者……有鑒于此,我們對資料的準確性極為關注……經過多年努力,層層把關,希望《故訓匯纂》將是一部翔實可信的書。”[1](前言,P8-9)不過,“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故訓匯纂》卷帙浩繁,加之書成眾手,出現一些失誤在所難免,相對于全書來說,畢竟是瑕不掩瑜。本文以《故訓匯纂》所引鄭玄箋注資料相關條目為主,對其疏誤情況予以列舉說明,希望能為辭典使用者或辭典的修訂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參考文獻:
[1]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故訓匯纂[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陳亞軍.《故訓匯纂》指瑕[J].古籍研究,2006,(2).
[3]李玉平.鄭玄語詞訓釋材料的纂集與《鄭雅》《鄭玄辭典》《故訓匯纂》[J].辭書研究,2009,(4).
[4]張覺.《故訓匯纂》指誤[J].中國文化研究,2009,(3).
[5]樊啟芬.《故訓匯纂·心部》勘補[D].武漢:湖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6]段然.《鄭玄辭典》所收《禮記注》語詞訓釋研究[D].天津:天津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7]臺艷霞.《鄭玄辭典》所收《儀禮注》語詞訓釋校補及研究[D].天津:天津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
[8]楊晨露.《鄭玄辭典》所收《周禮注》(天官至春官部分)語詞訓釋校補及研究[D].天津:天津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
[9]張清揚.《鄭玄辭典》所收《毛詩箋》語詞訓釋校補及研究[D].天津:天津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
[10]劉丹.《故訓匯纂》注項失誤研究——以口部為例[D].保定: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
[1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 1980.
[12][漢]鄭玄撰,[宋]王應麟輯,[清]惠棟增補,[清]孫堂補遺.鄭氏周易注(附補遺)[A].叢書集成初編:第383冊[C].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13][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A].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4][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唐]陸德明音釋.毛詩注疏[M].朱杰人,李慧玲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5][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A].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標點本)[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6][漢]伏勝撰,[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附序錄辨訛)[A].叢書集成初編:第3569冊[C].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17]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M].長沙:岳麓書社,2001.
Notes on the Reading of Guxun Huizuan(《故訓匯纂》)
Liu Chun,Li Yu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Guxun Huizuan(《故訓匯纂》) is a high-quality large-scale dictionary compiled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Prof. Zong Fubang and others, which brings together a wealth of ancient exegesis materials, and due to the large number of classic materials involved,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omissions in the process of collation. Taking the relevant items of Zheng Xuans(鄭玄) annotated materials quoted in Guxun Huizuan(《故訓匯纂》), the omissions are roughly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omissions, misreceipts, missing texts, derivative texts, and false texts, they are analyzed and explained by example.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research, it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dictionary users or dictionary revision.
Key words:Guxun Huizuan(《故訓匯纂》;Zheng Xuan(鄭玄);negligence;emendation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鄭訓匯纂及數據庫建設”(18BYY158);天津師范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重點項目“基于數據庫的《故訓匯纂》所引鄭玄《儀禮注》語詞訓釋資料編校疏失研究”(2022KYCX048Z)
作者簡介:1.劉? 純,女,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2.李玉平,男,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①本文初稿曾由李玉平以《〈故訓匯纂〉所涉鄭玄訓釋資料編校疏失考》為題,提交2021年在韓國延世大學在線舉辦的世界漢字學會第八屆年會討論,這次與劉純合作又做了較大修訂和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