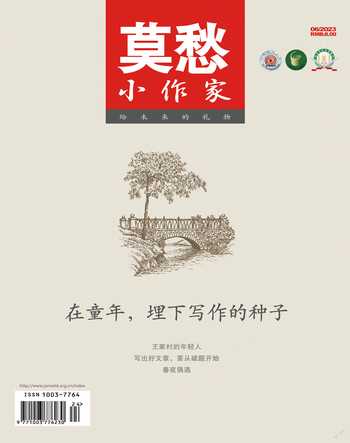草鳴呦呦
1
里巷間拆了一片瓦房,水泥墻拆去,簡單地架以鐵絲網圍著,視覺空敞穿透,里巷變大,一時仿佛城市也可拓寬。一株參天的老榕樹,早先只覺亂蔭紛紛,而今雜蕪盡袪,遠遠地便見其龍華風神垂天如云。我想它虬髭胡髯,怕不少于耄耋之年,濃蔭低垂俯仰寥廓,波濤蔽空似的,車水馬龍里,驚人地彰顯著大地的氣象,瞬時活化了我內在的感官,行在都市也有了某種浩闊的連接,那是喚醒我們看見大地的能力。
漸行漸近,大樹下一片蔚然,細草迎風,草鳴呦呦,其中有鹿奔跑一般的蓬勃興茂。
因于對草木的喜愛,我駐足觀賞,忍不住蹲下來,一一細數相認如故舊。
密密相疊叢集的綠里,葉下珠、馬蹄金、黃鵪菜、牛筋草、孟仁草、王瓜龍葵、黃花酢漿草……碧波相連,無一不有姓氏;間雜大飛揚草、小飛揚草、狗尾草、空心蓮子草……竟然還有刀傷草、菟絲花也躋身其中,波濤動蕩盡是一片綠林“草”漢。這些草籽一路從哪兒浪跡到此間?風吹、鳥飛、行人鞋履走踏、裙擺沾著黏附,或者泥土里便是種子銀行,所有原先埋藏在土中的種子,一霎時全數生發?都市留此曠地,于是生息落戶安歇,成就了這一片“草”民世界。
于大地而言,草是拓荒者的祖先,在艱困中生長,在隙縫中喘息,在城市人行道中伺機,它低伏也昂揚,前仆后繼藉風授粉,與花不同,不那般招展需要誘引授粉的昆蟲。它無華無聲無時無處不在,如是,少有人注意它的春天夏天秋天與冬天。仔細觀之,它的小花有色有形,或紅或白或黃或紫,或唇瓣或五瓣,有的細若芝麻,但其花柱雌蕊雄蕊一樣不少,大自然的精雕細若毫毛,渺渺精微渾然天成,既隨性隨機隨時又無所茍且,乏人聆賞亦不自毀物情,世間小物第一周正自適的就屬它。我市井中蹲踞觀草,亦有它的鄭重其事,默然無昭為其本色。
我蹲了半晌,小綠地既鼓翼也振翅,盡是昆蟲鳥獸世界里的嗡嗡聲與扇翅聲。麻雀舞得迅如閃電,黑頸椋鳥嘰嘰喳喳,在樹間歡快得亦如道途人來人往。因了草地、老榕,有食可覓、有樹可棲,麻雀、鳩鴿、蚱蜢、小灰蝶、黑頸椋鳥上下起落,蓬勃生機好不熱鬧。雖說季節已近霜降,秋日涼風堪稱舒爽,這一小塊夾著石礫、碎水泥的都市,因了草野顯得無比清麗。
地曠、草長、鳶飛,《詩經·小雅》說“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那真是久遠以前的故事了,這些小生物帶來的歡快,不計圍欄。我是個頭無片瓦、腳無錐地之人,偶踏街衢,為這畸零之地所展現的豐饒欣悅不已。
2
一般泛泛統稱的草,是一個偉大而龐雜的族群,它們以啟山林,無畏于石罅巖盤,扎根深化土地,為森林之先導,亦為蟲魚鳥獸獻上禮物。既為草,可為食可為藥,是蟲友,亦是大地溫床。我生長的年代,里巷常民隨手抓把雞屎藤紅糖熬汁,可驅風寒療治感冒。“上山采蘼蕪”是生活,蘼弱繁蕪的草是有故事的。當今,經營園藝的園主,面對非園藝物種一律斬草除根殺無赦。雖說拈花不離惹草,同樣是植物,怎如是天壤之差。
人類侵略土地的歷史起源于農業時代。當耕種萌芽,人類很容易視自生自長的草為惡草時,人類忘了小麥、稻米、甘蔗、粟黍、竹筍等等皆為草本植物。大地喂養一切生靈,草沒有我們也長得很好。除草是因為質疑雜草,但卻沒有人質疑草坪帶來的死寂。
草地不同于草坪。草地開放,如大海不拒細流,廣浩、繁密而多樣;草坪封閉,人自以為是地揀擇改變地貌、拔除一切所不需要的,不與任何物種產生聯結,單一而死寂。草坪第一次出現在花園景觀中,只有五百年歷史,但這歷史一開始便來勢洶洶。因為商業經濟的運作,它披了人類賦予的昂貴盔甲。
我有一暗里戲稱其為“草民”(身無半畝,心有天地,喜愛眾草與大地同在)的朋友,在都會大公園里籌設了一野花野草園區,緣由只為人人除之務盡的雜草,一一皆有名姓,叫得出戶籍。在“草民”眼里,草雖微物,既有名有姓便有科屬棲地,拔不得。
我每每閑觀這片野花野草園區,仿佛活靈活現地翻一本“野草綱目”,遙想那個膠囊藥丸不發達的年代,《本草綱目》里所載的許多皆是這些不可等閑的草芥。
自從“草民”教我認識一種名為金腰箭舅的草,我走到哪都發現金腰箭舅在召喚我,安全島、人行道、溝渠旁,等紅燈的當兒頗不寂寞,它葉腋黃花宛若腰佩金箭、一身本領的武林高手一般,可為地被、可為觀賞,亦列藥用植物名錄,為的是與另一名為金腰箭的相似物種比對區分,以免混淆。草不在乎廢墟,墻根隙縫亦有看不盡的動人瞬間。天下豈有無名草,無名是因為我們沒有認得它,有所識便有所情商,面對眾草不難于情商,而難于有所識知,故動輒掄刀上陣不問情由。
3
與“草民”論草,方知草亦有草性,野草雖野也選自己高興的時、地潑灑,不是任隨人意、想種便草草輕率也種得活。行于里巷,常見鐵線蕨在舊墻土石縫隙間奮力扎根,時不時有人打理墻面,一一掃去,不多時, 風微雨潤,它又盈盈一片青綠盎然。如是蹂躪經年歷久不衰,但亦有人從來沒種活過它。“草民”說,草與草看來濟濟一堂,卻各有其不同生長條件。四季流轉,誰為誰先做鋪路前鋒是個微分細膩的問題,植物自己知道。
我查了書,草和植物一樣,依其光合作用中需要碳原子數量的多寡,大致可分為寒季與暖季;所以我在野地里,晚冬看到的假吐金菊,夏日就消失了蹤影。寒季生長的,暖季消失,讓出地表;暖季生長的,寒季消失,讓出地表。這個說法固顯粗略,但小草來去隨心,自有季節,不喜歡人類插手,除非它自己想要的地方,干枯是對人類最大的宣告。春原亦有衰草,秋谷閑花草芥亦要臭味喜相投。
我喜歡大地閑花草野興茂,亦自列為“草民”一族。靜觀草野,喜的是草野的隨機任運而無為。有人想專門種高貴的花,我也喜得我也賞得,是大地的我都愛。細細檢索這個傷痕累累的大地,農作、化肥消耗土地,恢復地力最好的方式是休耕,放任所有埋藏在土中的種子成長,讓土壤被雜草接管,休養生息是恢復地力最好的方式。
可不是,城中有人,亦有草野。關于草,《植物與動物的互動》一書中說:任何一種草,只要被吃都會馬上生長,有蹄動物的嚙咬與唾液會刺激幼草的成長。
只可惜這兒是城市,沒有羊群與牛群。
草鳴呦呦,我惋惜這片意外生得的城市草野。它在夾縫中生,亦在夾縫中消無,終始盡情奮力。設若有朝,大地劫毀,世間最先返首的必然也是它。高閣樓宇盡去,但寒煙翠草凝綠。
王小梅:90后,現從事幼兒英語教育工作。2016年開始創作,已在多家刊物發表小說、散文、兒童文學等文學作品數十篇。
編輯? ?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