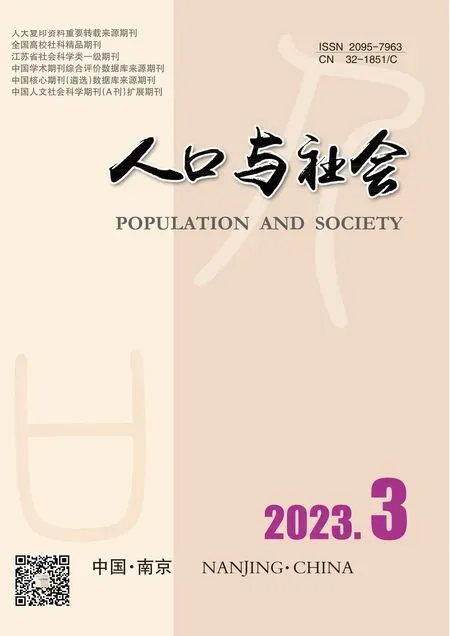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狀況及影響因素
王雅潔,駱洪梅,閆 曉
1.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 ,北京 100191;2.河北金融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和人口流動政策的變遷,有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到其他地區工作生活。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不斷增多,我國進入了各民族跨地區大流動的活躍期。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充實了流入地的人力資源,為少數民族地區的脫貧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極大地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但是,由于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等方面存在差異,大部分少數民族群眾進入城市后需要面對比漢族流動人口更復雜的社會融入問題。
社會參與是社會成員在制度與組織層面參與公共事務的過程,是社會融入的重要維度。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而言,社會參與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溝通的有機紐帶,是他們了解和適應城市生活并參與城市治理的權利意識及行為能力的呈現,也是他們城市歸屬感的外在表現。因此,社會參與通常被當作是評估流動人口社會融入情況的核心指標之一。
從以往的研究來看,學界單純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為研究對象、針對該群體在流入地的社會參與情況開展的研究較少,多是將其作為社會融合的一個重要維度進行分析。李丹選取了兩個少數民族自治縣作為調研點,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移民的經濟融合與社會融合情況進行研究,發現遷入地的經濟產業結構和就業環境影響了移民的生計發展,使得移民社會參與不活躍,不利于他們的社會融合[1]。劉玉蘭基于民族社會工作視角,利用2013 年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合調查數據開展研究,提出城鄉之間、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加劇了流入地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的排斥程度[2]。淦宇杰基于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狀況進行分析后發現,流動距離較短、流動范圍相對較小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社會參與方面更為活躍,能更好地適應流入地的社會文化,進行社會交往、獲得心理認同的障礙相對較少,更容易在流入地產生身份認同感[3]。
本研究利用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聚焦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群體,分析他們在流入地的社會參與現狀,揭示影響他們社會參與程度的因素,從而提出改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效果的對策建議,進一步提升城市民族工作成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概念界定和數據來源
(一)概念界定
國內外學者對社會參與的概念沒有統一的描述。Berger認為,社會參與是公民參與的重要方面,指人們對各種組織、協會的參與。關于組織的定義,Berger引用了托克維爾的說法,即那些沒有政治目的的民間生活中的組織[4]。日本總務廳統計局發布的《平成8年社會生活基本調查報告》認為,社會參與是一種“社會活動”,這種活動可以分為專為他人服務的“社會奉獻活動”和包含個人目的的“社會參與活動”[5]。楊風雷等認為,社會參與是參與者在社會互動過程中,通過社會勞動或者社會活動的形式,實現自身價值的一種行為模式[6]。王兵則認為社會參與是社會成員以某種方式參與、干預、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社區的共同事務,從而影響社會發展的過程[7]。在中國語境下研究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參與情況,必須要考慮少數民族的特殊性。
(二)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是國家衛生健康委流動人口服務中心的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簡稱CMDS)2017年的統計數據,該調查采用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PPS抽樣方法,在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流動人口較為集中的地區進行調查,具有較強的代表性。調查樣本總計169 989個,其中包括蒙古族、滿族、回族、壯族、藏族、維吾爾族、苗族、彝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瑤族、朝鮮族、白族、哈尼族、黎族、哈薩克族、傣族等少數民族有效樣本15 997個,回族、壯族、藏族有效樣本量位居前三,分別占比22.0%、13.2%、9.7%。
(三)變量選擇
1.因變量
根據2017年CMDS數據指標設置,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情況主要包括社會組織參與和社會活動參與兩個維度,本研究的因變量分別為是否參與社會組織和是否參與社會活動。社會組織參與維度中,社會組織的種類包括“工會”“志愿者協會”“同學會”“家鄉商會”“老鄉會”和“其他”六種,少數民族受訪者可在這些選項中進行多項選擇,若受訪者至少參加其中一類具體組織,則該樣本編碼為1,一類都未參加,則編碼為0。社會活動參與維度中,社會活動的種類包括“給所在單位/社區/村提建議或監督單位/社區/村務管理”“通過各種方式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提出政策建議”“在網上就國家事務、社會事件等發表評論,參與討論”“主動參與捐款、無償獻血、志愿者活動等”和“參與黨/團組織活動,參加黨支部會議”五種,少數民族受訪者針對每個種類的參與情況可在“沒有”“偶爾”“有時”“經常”四個選項中進行單選。若受訪者對于各項社會活動均選擇“沒有”,則該樣本編碼為0,否則編碼為1。
2.自變量
從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自身屬性、經濟水平以及流動特征出發,本研究選取的自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戶口性質、婚姻狀況、健康狀況、住房狀況、就業狀態、收入水平、流動范圍、居留意愿以及參與醫療保險情況,分析各指標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情況的影響程度,變量詳情見表1。

表1 自變量定義及描述
(四)研究方法
根據2017年CMDS數據指標設置,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情況主要包括社會組織參與和社會活動參與兩個維度,所以本研究的因變量分別是是否參與社會組織和是否參與社會活動,設置為二分類變量,本文采用logistics回歸模型對其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具體模型如下: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的條件概率為:
其中,P(Y=1|X=x)為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的條件概率(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戶口性質、婚姻狀況、健康狀況、住房狀況、就業狀態、收入水平、流動范圍、居留意愿以及參與醫療保險情況的概率),α為截距項,β為自變量的系數向量,其符號方向代表了自變量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的影響方向。模型參數通過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
三、結果分析
(一)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狀況
1.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以參加初級社會群體為主,參加次級社會群體的比例較低
社會群體根據群體成員間關系的親密程度可分為初級群體和次級群體。初級群體是指面對面互動所形成的、具有親密的人際關系和濃厚的感情色彩的社會群體,主要有家庭、鄰里、朋友和兒童游戲群體,這些群體在人的早期社會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現實社會中,血緣群體、友誼群體與地緣群體是初級群體的重要類型。次級群體指的是其成員為了某種特定的目標集合在一起,通過明確的規章制度結成正規關系的社會群體。次級群體中成員間的正式關系較多,受明文規定的規章制度的限制,群體間的社會互動是以完成某種工作任務為前提的,群體成員間的情感聯系較為淡薄,主要是因職業和工作聯系而結成的業緣群體。
對于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來說,他們多在以本民族人口或文化、地域相近民族人口為主的區域聚居,在流入地的社交群體主要以友誼型和地緣型的初級社會群體為主[8],參與的社會組織主要是同學會和老鄉會。根據表2可知,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社會組織參與情況方面與其他流動人口群體具有共性,參加老鄉會、同學會比例最高,分別為21.3%、20.1%,參加工會、志愿者協會、家鄉商會等正式組織的比例均在10%以下。

表2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參與各類社會組織情況
2.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政治活動參與不足,參加社會公益活動較為活躍
社會活動參與主要是參與政治活動和公益活動兩個方面。政治活動方面,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政治參與可理解為具有少數民族身份且不具備居住地戶籍的流動群體通過一定的渠道進行政治參與,在流入地試圖影響當地政治決策的行為[9],參與目的是在公共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利益。經濟收入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礎保障,也是個人經濟地位的決定性因素,更是個體參與政治活動的物質基礎。有研究基于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得出全國范圍內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月均收入為3 367.37元,低于漢族流動人口月均收入3 782.40元[10]。同時,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職業層次較低,多為非正規就業,無法享有與正規就業的職工同等的待遇,無法參加單位職工代表大會、工會組織等[11-12]。參與公益活動方面,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社會形象,以及城市居民對他們的認知和態度關系到雙方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如果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能主動參與公益活動進行形象構建,可以改變其在城市居民心中的刻板印象,更好地與城市居民互相適應接納[13]。從表3的數據來看,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參加各類社會活動的比例普遍較低,給政府/相關單位/社區/村提建議、反映情況、進行監督管理,參與黨/團組織活動及黨支部會議,在網上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件等發表評論、進行討論等政治活動的參與程度明顯不足,90%以上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表示未參與上述活動。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參與捐款、無償獻血、志愿者活動等公益類社會活動的情況相對較多,近35%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曾有參加社會公益活動的經歷。

表3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參與各類社會活動情況 %
(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情況影響因素分析
表4是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情況的logistics回歸分析結果。模型1是社會組織參與模型,模型2是社會活動參與模型,P值均為0.000,模型總體有意義。以0.05的顯著性水平為準,性別、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就業狀態、家庭收入、流動范圍、參與醫療保險情況等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情況均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受教育程度的影響最為明顯。相對于小學及以下學歷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初中學歷、高中及中專學歷、本科及以上學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參與發生比分別是其1.5倍左右、2倍左右和3倍左右。教育是最重要的提升人力資本的途徑,不僅關乎人口流動行為,而且也影響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生存發展與市場際遇。人力資本偏低直接制約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就業競爭力。相反,受教育程度高意味著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稟賦,高學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工作機會更多,就業更穩定,經濟狀況更好,具有更高的社會地位,會進一步使得他們對流入地有更為強烈的歸屬感,在社會參與過程中也會更加活躍。就業不僅可以提高個體收入水平,也能增加個體與他人、社會的聯結,進而增強社會參與效能感,增強個體的社會參與意愿。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參加本地基本醫療保險,可以讓他們享有更高質量的社會保障,提升他們的居民身份認同感,弱化其邊緣化的心理感受,更利于他們進行社會參與。此外,男性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比女性社會參與度高,具有黨團身份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度更高。與跨省流動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相比,省內流動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社會組織參與方面更加積極,說明相近的地域文化和生活習慣有利于促進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與流入地人群的交往,增強兩者之間的互動。無配偶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參與社會活動方面也比有配偶的更為積極,這是由于無配偶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擁有更多的空閑時間,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社會活動中。

表4 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情況的logistics回歸分析結果
四、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統計數據,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參與情況進行初步分析,并進一步探析其影響因素,得出如下結論:(1)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程度不高,這也是流動人口群體的共性問題。(2)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參與同學會、老鄉會這兩種社會組織的更多,他們的政治活動參與明顯不足,更愿意主動參與捐款、無償獻血、志愿者活動等社會公益活動。(3)性別、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就業狀態、家庭收入、流動范圍、參與醫療保險情況等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社會參與情況均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受教育程度。男性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比女性的社會參與度更高;已就業、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參與本地基本醫療保險、具有黨/團員身份對促進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參與起到積極作用;省內流動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參與社會組織方面比跨省流動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更加積極;無配偶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參與社會活動方面比有配偶的更為活躍。
(二)政策啟示
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少數民族的人口流動和社會融合問題。2014年9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指出,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不能采取“關門主義”的態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應讓城市更好地接納少數民族群眾,讓少數民族群眾更好地融入城市。在2021年8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充分考慮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實際,統籌城鄉建設布局規劃和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完善政策舉措,營造環境氛圍,逐步實現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論述為我們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結合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的各類教育和職業培訓力度。加大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支持與投入,擴大“雙語”教學覆蓋范圍,在少數民族文化課程的基礎上開展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提升少數民族人力資本,增加少數民族人口就業機會,提高他們的就業質量,讓他們有能力、有條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會。
二是加快實現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均等化。流入地相關部門要重視少數民族的特殊性,從他們的需求和切身利益出發,在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就業、醫療、教育等重要方面完善服務,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比如,營造公平公正的就業環境,探索靈活就業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依法參保形式,保障少數民族流動家庭中的子女獲得良好的基礎教育,在文化活動和設施的設計上加入少數民族元素,豐富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業余文化生活等,讓他們有更多的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增強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
三是完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體系。相關管理部門應以服務好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為出發點,完善流出地和流入地兩頭對接工作機制,加強管理部門之間的支持與配合,努力實現對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無縫銜接;依托社區開展民族工作,為轄區內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提供就業服務、政策宣傳、心理疏導、法律援助等多方面的社會支持,組織有利于民族團結進步的主題活動,加深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時,也可以邀請少數民族代表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讓少數民族流動人口“進的來、留得住、過得好、能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