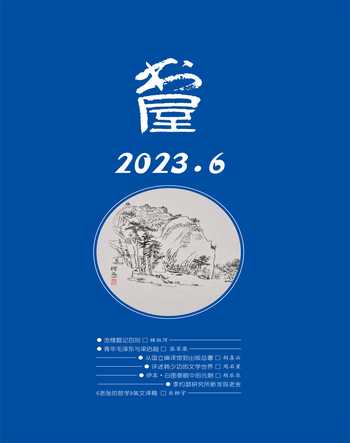2023年第6期書屋絮語
邵水游
學(xué)者寫小說,著名的如錢鍾書《圍城》。近現(xiàn)代小說之興盛,實多學(xué)者所為,因為學(xué)者能駕馭語言,文白夾雜,詞語經(jīng)濟(jì),把語言張力和審美性推向極致,即言詞意義的片刻孕育著豐富性,能恰如其分,又能出乎意料。或者說,金庸、梁羽生、古龍的武打小說,抑或老輩學(xué)者的自傳,亦可如是觀。而歷史小說應(yīng)為學(xué)者的當(dāng)行,典型如唐浩明的曾國藩三部曲,這一路數(shù)的小說很注重史實的尊嚴(yán),在史料的爬梳與整理中尋找故事的繁復(fù)性和歷史細(xì)節(jié)的真實性,事有所本,情有所歸,其間的演繹又賦予文學(xué)的色彩,讓枯燥的史料生動起來,讓每一句話、每一歷史事件都化為故事元素,并將情節(jié)的推進(jìn)在歷史、文學(xué)和哲學(xué)的高度融合中,體現(xiàn)出學(xué)者文史哲通達(dá)的功力。
郁龍余先生長篇歷史小說《黃道婆》、電影劇本《譚云山》等應(yīng)屬此類。眾所周知,郁先生是研究印度文化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大家,在學(xué)界頗有聲望,他創(chuàng)作《譚云山》,應(yīng)是分內(nèi)事。因為現(xiàn)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湘人譚云山父子、徐梵澄以及研究古代交通史的向達(dá),是無法繞過去的人物,甚至說缺少他們,這部交流史無從下筆。而其耗費五十年的功力,專門為故鄉(xiāng)歷史人物黃道婆立碑作傳,卻難以想象。滕文生先生評價這部長篇小說寫道:“郁龍余教授積五十年之功力,旁搜博征,妙筆成趣,寫就了一部反映黃道婆生平與業(yè)績的長篇歷史小說,使這位創(chuàng)業(yè)于宋末元初的巾幗巨子顯于當(dāng)今民族復(fù)興的新時代,其心志與才情誠可欽矣!”而作為湖湘子弟,我更愿意《譚云山》能引起重視,再現(xiàn)一代人物的文化風(fēng)流。
同是對文化前輩的崇敬,張建智先生著有《絕版詩話三集》和《一門風(fēng)雅——王世襄家族的藝術(shù)世界》。前者是張先生父女對現(xiàn)代文學(xué)史被忽略詩人的拾遺,一、二集應(yīng)如是,讓我們重新對現(xiàn)代詩的整體有個更清晰的認(rèn)知、更完備的評述,并對這些遺漏的詩人的人生和才情能抱同情之理解,他們詩的重新闡讀和故事的探究,能圓滿現(xiàn)代詩史,作更大的包容。后者是為鄉(xiāng)賢王世襄先生作傳,能得到傳主的充分肯定,這是學(xué)者作傳的福氣,也因為同鄉(xiāng),予以特別授權(quán),更是難得。把傳主置于整個家族史當(dāng)中,淵源有自,脈絡(luò)分明,沿襲而下,各有精彩,然藝術(shù)氣息始終盤踞在家族人物之中,人文精神與家族成員的成就息息相關(guān)。
收到萬里先生所贈《唐宋時期湘贛禪宗網(wǎng)絡(luò)研究》上、下二冊,我是門外漢,真的不敢置喙。僅限于他是《書屋》的審稿專家,每次看到他指出將刊文章中的硬傷,引經(jīng)據(jù)典地更正,多種史籍信手拈來,感佩不已;也僅限于他書中的若干篇什,在雜志上首發(fā),說實話,讀了則了,欽慕他的考證功夫和巨細(xì)不遺下蠻力的做派,這是典型的舊式訓(xùn)詁學(xué)風(fēng),當(dāng)下很少見了。而我,面對這二冊厚厚的著作,只看了序言、后記及參考書目,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讀完,辜負(fù)先生的盛情了。讀書講緣分,更講相對應(yīng)的知識和水準(zhǔn),除此,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