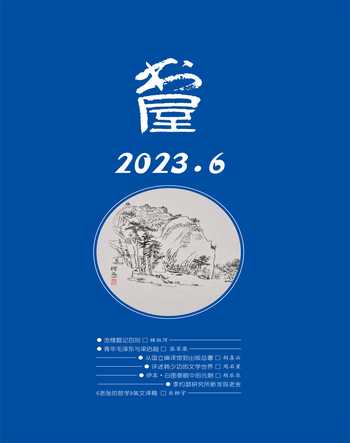青年毛澤東與梁啟超
張家康
青年毛澤東告別省立高等中學堂,寄居在湘鄉會館,開始自修自學。這期間,他的自修課堂就是湖南省立圖書館。他在這里自修了半年,廣泛涉獵十八、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書籍。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和達爾文關于物種起源方面的書,還讀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文藝作品。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師范。次年春,第四師范并入第一師范。一年前,他考入省立高等中學堂的作文,就是以梁啟超的“以教育為主腦”之說而立意。現在他之所以選擇師范學校,也是在踐行“以教育為主腦”的信念,有意當一名教員,獻身教書育人的事業。他在一師很得一些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老師的喜愛,如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王季范、黎錦熙等。楊昌濟在一師的學生中尤為喜愛和欣賞毛澤東、蔡和森,他在日記中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楊昌濟以毛澤東的出身與曾國藩、梁啟超相似,而以“異材”勉勵和期待。楊昌濟和梁啟超都崇拜曾國藩。梁啟超有言:“吾以為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得救矣。”楊昌濟反復研讀曾國藩著作,手抄曾國藩的《求闕齋日記》。青年毛澤東深受他們的影響,不僅讀曾國藩的書,而且寫了不少批語和筆記。他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曾推薦曾國藩的養生法:“曾文正行臨睡洗腳、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1917年8月23日,他在給亦師亦友黎錦熙去信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
梁啟超推崇康德哲學,曾撰寫《近世第一大哲學家康德之學說》,宣揚康德的先驗主義。梁啟超還將康德的先驗主義與宋明理學相提并論:“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學說之基礎全同。”青年毛澤東也深受其影響,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也說:“吾國宋儒之說與康德同。”1916年12月9日,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世界之外有本體,血肉雖死,心靈不死,不在壽命之長短,而在成功之多寡。”這顯然是受梁啟超的啟發,梁啟超把人的生命分為“現象我”與“真我”兩部分,前者是肉體,受自然法則的支配;后者是靈魂,可以超越時空而不朽。
梁啟超信服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說:“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經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經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青年毛澤東極為贊同,他在《講堂錄》中寫道:“毒蛇螫手,壯士斷腕,非不愛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家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梁啟超一生多變善變,慣于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康、梁雖并稱,可卻并不完全合流。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卻“太無成見”,認為“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青年毛澤東對此十分贊同。他在《講堂錄》中就寫下這樣的話:“天下事物,萬變不窮。”他在《體育之研究》中提出:“天地蓋唯有動而已。”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對康、梁二人都有所論及,說康有為是“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信中又說:“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從何而來?故某公常自謂‘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來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挑戰與否,亦未可知。蓋研究日進,前之臆見自見其妄也!”“某公”即梁啟超,可見他在康、梁之間已有明顯的傾向性了。
梁啟超認為國民素質太差:“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青年毛澤東對此十分認同,1917年8月23日,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青年毛澤東當仁不讓,擔當起這“摧陷廓清”的使命。
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時,花了不少的工夫研讀了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并寫下了諸多的批語,這些批語往往又多聯系到他所欣賞的梁啟超。他在《倫理學原理》中的一段文字旁批注:“梁任公有將來觀念與現在主義之文,即此段之意。”這便是他所熟讀的梁啟超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梁文說:“進化之義,在造出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一過渡之方便法門耳。”“十九世紀者,平民主義之時代也,現在主義之時代也。”毛澤東讀書向來是融會貫通,覺得泡爾生、康德和梁啟超都說出了一個道理。
青年毛澤東對梁啟超給湖南思想界鼓蕩起的思想火花極為向往和振奮。1897年,蔣德鈞、熊希齡等發起創辦湖南時務學堂。當年11月,就延聘時任上海《時務報》主筆梁啟超到學堂主講。梁啟超在講課和給學生的批語中激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觀念,宣傳民權平等的學說和變法主張。從時務學堂走出了兩百名左右的杰出人才,他們之中就有蔡鍔、楊樹達、范源濂、方鼎英、李復幾等。梁啟超自己也說:“新舊之哄,起于湘而波動于京師。”青年毛澤東斯時年幼未能欣逢,但對這段歷史十分熟悉和神往,他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中寫道:“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來,黯淡已極。二十年前,譚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學會,招集梁啟超、麥孟華諸名流,在長沙設立時務學堂,發刊《湘報》《時務報》。一時風起云涌,頗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則彼時因幾千年的大帝國,屢受打擊于列強,怨痛愧悔,激而奮發。知道徒然長城渤海,擋不住別人的鐵騎和無畏兵船。中國的老法,實在有些不夠用。”
1918年8月,毛澤東來到北京大學,這里是新文化運動的重鎮,面對撲面而來的各種主義思潮,更激發起他對新文化的渴求和對救國道路的尋找。特別是在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下,視野更開闊了。他和斯諾所說“我早已拋棄了康、梁二人”,應該正是在北大時期,這個時期他經歷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組織湘人驅逐張敬堯運動等。實踐斗爭已經表明梁啟超的辦法救不了中國,毛澤東只能另找道路,這條道路就是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