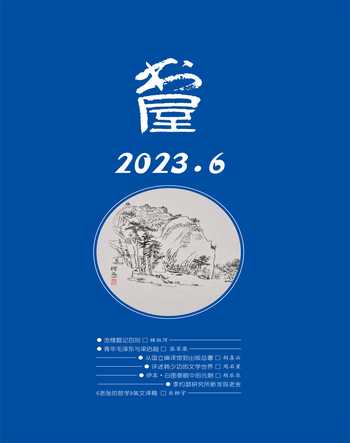從童年反芻生命的詩(shī)意
鄧雅晴
河合隼雄是日本著名臨床心理學(xué)者、心理治療師。《愛(ài)哭鬼小隼》是河合隼雄臨終之際完成的自傳體兒童小說(shuō)。
河合隼雄常常苦惱于人們對(duì)童年日常的漠視。在《孩子的宇宙》一書(shū)中,他記錄了這樣一件事:當(dāng)自己把孩子們寫(xiě)得非常精彩的詩(shī)分享給其他人看時(shí),卻遭到了他們的質(zhì)疑:“不管怎樣,這不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事嗎?”他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有太多的人連稀松平常的事也一無(wú)所知,讓我覺(jué)得僅僅談?wù)撘幌逻@一點(diǎn)也有著充分的意義。”他認(rèn)為孩子的宇宙以無(wú)限的深度和廣度存在著。如果漠視孩子生活的日常,我們就不能了解“孩子的宇宙”,更無(wú)法從中重新發(fā)現(xiàn)自我生命的奧秘。選擇在彌留之際寫(xiě)《愛(ài)哭鬼小隼》,是因?yàn)閷?duì)個(gè)體而言,愈臨近生命的終點(diǎn),童年的記憶愈清晰地浮現(xiàn),童年也愈能顯示出其非凡的意義和蔥郁的詩(shī)意來(lái),同時(shí)此種生命體驗(yàn)的反芻也能給他人以啟示。
《愛(ài)哭鬼小隼》敘寫(xiě)的是小男孩城山隼雄那些極其普通的日常,如嬉戲、交友、打架、學(xué)習(xí)、文藝匯演等,但這些日常卻蘊(yùn)含著重要的教養(yǎng)啟示和深刻的童年哲學(xué)思考。比如小隼因?yàn)橄饦?shù)果實(shí)回不了家而悲傷甚至哭泣,是因?yàn)樾■腊严饦?shù)果實(shí)的處境當(dāng)成了自己生命的影子。這解釋了為什么人在年幼的時(shí)候最容易對(duì)萬(wàn)事萬(wàn)物產(chǎn)生共情,因?yàn)樗鼈兊脑庥鲇成渲啄陼r(shí)種種焦急、無(wú)奈、無(wú)助、憂傷和絕望的情緒。比如小隼和班上的男孩開(kāi)始玩“秘密基地”的游戲之后,他變得更加積極和勇敢了,這揭示了“秘密基地”對(duì)孩子非同一般的意義,那是他們建立友誼和自信的“必需品”。還有,小隼喜歡的人先后離去,他開(kāi)始感受到籠罩全身的孤獨(dú),不知不覺(jué)地開(kāi)始害怕黑夜,反映了孩子成長(zhǎng)過(guò)程中難以言說(shuō)的寂寞和困擾。河合隼雄把這些日常娓娓道來(lái),描繪了一個(gè)孩子隨年歲變化著的、復(fù)雜而奇妙的心路歷程,體現(xiàn)了一個(gè)心理學(xué)家對(duì)孩子心理的敏銳認(rèn)知和準(zhǔn)確把握。更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對(duì)孩子的內(nèi)心永遠(yuǎn)懷著溫柔的尊重與支持,他相信來(lái)自孩子自身的力量能使他們往正確的方向成長(zhǎng)。
童年是一個(gè)人最具有旺盛的感受力的時(shí)候,兒童的內(nèi)心常常充斥著各種情緒,但是又無(wú)法言說(shuō)。橡樹(shù)果實(shí)掉進(jìn)池塘、與克拉伊博先生像朋友那樣交談、桑村老師的離去、小道哥哥和阿良打架等種種生活的日常都能攪動(dòng)小隼的內(nèi)心,引得他淚水漣漣。然每一次的淚水所包蘊(yùn)的情緒都是不一樣的,哪怕同樣是離別,也會(huì)因?yàn)槌砷L(zhǎng)階段的差異而引發(fā)不同的心理體驗(yàn)。面對(duì)這些復(fù)雜而幽深的情緒,作為孩童的小隼能夠深切地感知,卻無(wú)法言明。兒童豐沛的情感與他們尚且貧瘠的表達(dá)之間形成了巨大的缺口,以至于他們只能用“哭”這個(gè)行為去做徒勞的填補(bǔ),因而往往陷入一種“孤苦無(wú)告”“無(wú)所依傍”的境地。
法國(guó)哲學(xué)家加斯東·巴什拉有言:“在生命最后的四分之一時(shí)期,人們將老年的孤獨(dú)反射到被遺忘的童年孤獨(dú)上,才理解到生活最初四分之一時(shí)期的孤獨(dú)。”這種“孤獨(dú)”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關(guān)乎存在的焦慮:“我”是否存在,以何種方式存在。橡樹(shù)果實(shí)回不了家,其實(shí)是作家對(duì)童年個(gè)人存在焦慮的一種隱喻。河合隼雄在他的回憶錄中提道:“本來(lái)別人看我像是一個(gè)哭屁蟲(chóng),自己也非常地自我厭棄。”“上小學(xué)的時(shí)候,我一直心里煩惱:是不是只有我一個(gè)不是這個(gè)家里的孩子?”再加上五歲的時(shí)候即經(jīng)歷弟弟的離世,河合隼雄相比其他的孩子更容易聯(lián)想到“死亡”,更容易產(chǎn)生對(duì)生存的疑慮和對(duì)消逝的憂懼,這些感知也生動(dòng)地體現(xiàn)在愛(ài)哭鬼小隼身上。然而,在文本中,讀者依然能覺(jué)察到這種焦慮如何被一次又一次地?fù)崞健P■缽募胰四抢锏玫搅岁P(guān)于自我存在的確證,作者也與幼年那個(gè)脆弱敏感的自己和解。這種和解出于對(duì)童年心性的深刻理解,飽含走過(guò)漫漫人生所生出的無(wú)限感激。
河合隼雄曾經(jīng)那么厭棄自己是一個(gè)“哭屁蟲(chóng)”,但他恰恰就把小隼塑造成了一個(gè)極易受觸動(dòng)的“愛(ài)哭鬼”。因?yàn)樯鼓褐畷r(shí),他已懂得童年和童年的自己給人生帶來(lái)的無(wú)限意義:“接連不斷地、不加過(guò)濾地、純真地感動(dòng)著,實(shí)在讓我的人生受益不淺”。“哭”在個(gè)體生命層面上,是對(duì)宇宙萬(wàn)物的一種積極回應(yīng),也是尋求宇宙萬(wàn)物回聲的一種呼喊。河合隼雄以滿懷包容和欣賞的目光,注視著自己筆下那個(gè)常常哭泣的小隼,同時(shí)被小隼的柔軟善感所觸動(dòng)。這就解釋了河合隼雄何以擁有非凡的教育哲思,以及他筆下的童年為何像美麗的詩(shī)篇,他回望童年的姿態(tài),正像一位詩(shī)人。河合隼雄對(duì)童年的描寫(xiě)超越了童年本身,他帶著一生的生命體驗(yàn),給童年注入了詩(shī)性的光輝。
河合隼雄把豐厚的生命體驗(yàn)化作詩(shī)意的童年日常書(shū)寫(xiě),塑造了“愛(ài)哭鬼”小隼這一形象,并以小隼對(duì)日常事物的獨(dú)特體察為基礎(chǔ),揭示兒童內(nèi)心情感的豐富性和隱秘性,并以滿懷贊賞的目光刻畫(huà)了獨(dú)屬于童年的那份敏感、孤獨(dú)和美好,呈現(xiàn)出“童年即詩(shī)”的美學(xué)思考和生命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