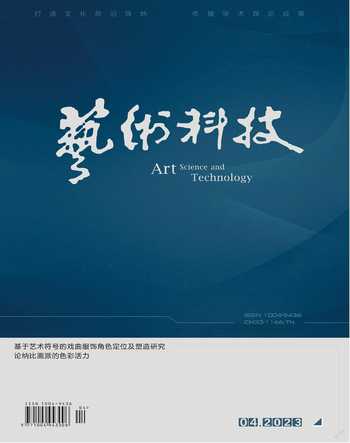人工智能時代藝術創作的主觀價值探究
葉思琪 夏添一
摘要:人工智能在為藝術提供新的創作載體的同時,其強大的創作功能引發了藝術界懷疑論者的恐懼和思考,藝術創作的主體是否會被碎片化、被技術破壞或異化,人類的藝術創造力是否會被顛覆,成為重要問題。回顧藝術發展的歷史,從歷史的邏輯和發展的動力分可以看出,新的藝術范式的建立和轉變,很大程度上基于技術和媒介的進步所引起的社會轉型和生產。在20世紀大工業生產的合作機制下,藝術價值被重新定義,思想表達成為現代藝術、后現代藝術的核心,成為歷史藝術敘事的核心。自此,藝術不再僅僅是一個視覺問題,而是與社會整體環境密切相關、受社會影響的產物。從藝術發展史的角度來看,由于人類藝術的發展并沒有邏輯規律可循,而人工智能僅能對現有數據庫進行學習創造,因此無論從實用技術上還是哲學理念上,人工智能都很難取代人類創造的藝術價值。但是,隨著整個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如果未來技術的發展超出了人類的控制,如果人類藝術目前賴以生存的人文價值體系因為技術的發展而消亡,那么人類社會的底層結構將發生質變。這種變化也將導致藝術的徹底重塑。當藝術處于自身人文傳統與人工智能發展對抗的初期,藝術的思考必須從更宏觀的層面去關注人類現實對人類藝術主體性的保持,應該成為當代藝術創作的核心理念。基于此,文章對人工智能時代藝術創作的主觀價值展開研究。
關鍵詞:人工智能;藝術創作;主體性
中圖分類號:TP18;J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4-0-03
近年來,人工智能在許多以前被認為需要由人類智能控制的領域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在藝術領域,人工智能在視覺表現方面的突破性嘗試引起了廣泛思考和討論。人工智能創作的藝術是否擁有社會意義和精神價值?在人工智能時代,藝術的價值是否會因為新技術的介入而面臨瓦解?人工智能會重新建構“藝術”嗎?作為當代藝術從業者,應當如何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新挑戰?
1 當代藝術的核心價值
1.1 當代藝術史研究的轉向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藝術史理論研究的主要趨勢更加傾向于社會學的理論探索,呈現出從藝術內部向藝術外部觀察的轉變[1]。藝術不再表現為媒介的更新,也不試圖通過全新的形式再現一個哲學概念,而是強調再現決定藝術和藝術生產的背景,事實上成了對文化和政治背景的批判。所以,藝術理論已經成為同類的文化和政治語言學。
以討論現代藝術的價值為例,工業革命的社會背景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是現代藝術史起源的背景,現代藝術的理論圍繞著19世紀中期開始的技術革新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而建構[2]。繪畫工具、生產和供應、媒體到媒介的變化是如何影響藝術創作的研究的?厘清現代藝術與過去有何不同,需要在一個獨特的價值體系中思考。
1.2 當代藝術的核心價值
印象派通常被認為是古典藝術到現代藝術的轉折點。現代藝術理論對印象派藝術價值的研究多側重于技術、社會和藝術之間的密切聯系。
首先,印象派作品從題材和思想上代表了隨著工業革命出現的新興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畫廊的代理銷售制度逐漸取代了以往以教會和貴族為主體的贊助制度;攝影技術的完善和現代化學工業的興起帶來的顏料的標準化生產也對印象派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現代藝術在與新技術和新社會形態的互動中開啟了深刻的變革。
1912年,福特汽車公司創造了以汽車流水線為標志的20世紀資本主義高效工業化生產場景,與之相對應,杜尚在1917年創造了著名的“噴泉”。很明顯,杜尚的現成藝術與現代工業的大規模生產之間存在著直接而密切的聯系[3]。隨著工業生產方式的迅速拓展,大量廉價的工業產品作為景觀出現在現代城市中,生活在城市中的藝術家們自然而然地成為藝術生產和藝術消費行業的一部分。這迅速導致以杜尚為源的裝置藝術的發展,以一種完全破碎的姿態重新定義了藝術。藝術作品的核心價值也從此轉變為對象背后的思想表達。
2 人工智能參與藝術的現實
2001年,英國藝術家大衛·霍克尼證明,自15世紀以來,許多西方藝術家的繪畫都是依靠光學設備完成的,其中就包括漢斯·荷爾拜因的畫作《大使們》[4]。毋庸置疑,在西方藝術史上,科學技術的進步總是為藝術創作提供新的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藝術范式的建立和變化。但在人類社會進入人工智能時代后的今天,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累積效應在給藝術家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日益引發了懷疑論者的恐懼和思考:人類藝術的獨特價值會不會被科技抹殺?
2.1 人工智能藝術介入的問題
通過與互聯網、大數據結合,人工智能正迅速介入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過去,人們對利用科學技術和儀器來幫助觀察和繪畫,始于設想,終于視覺。然而,參與藝術創作的人工智能可以模擬人類的視覺思維機制,進行圖像學習、分析、識別,甚至是圖像創作。長久以來,藝術創作因涉及復雜的人類情感、生活經驗等,一直被認為是人類的特殊能力。但如今,這種能力的獨特性正在受到人工智能技術的質疑和挑戰。
近10年來,人工智能技術在藝術領域的應用不斷擴張。2012年,人工智能畫家在學習了8萬多幅現代繪畫之后,創作了不同于傳統藝術流派的繪畫,并且在針對畫作的意義和視覺結構的評分中得到了比人類畫作更高的分數。2017年“雙11”購物節期間,阿里的“魯班”系統通過數據庫學習,實現了每秒8000張海報的設計。2018年,第一幅被拍賣的人工智能作品《埃德蒙·貝拉米畫像》在拍賣行以43.25萬美元成交。
如今,人工智能在藝術界引起的爭論包括:除了人工模擬藝術史的現有風格外,人工智能是否能創造出具有社會和精神意義的藝術?人工智能會取代藝術家嗎?人工智能會重新定義藝術嗎?
2.2 人工智能藝術創作的爭論
2.2.1 人工智能作品創作的困難
有一種觀點認為,無論是在今天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工智能在技術上和哲學上都無法取代人類創作的藝術價值。
首先,藝術的價值在于藝術的創造性。雖然人工智能制作的“下一個倫勃朗”使用了非常復雜的計算技術和圖像識別技術,但即使它創作出了接近原作的作品,至多也只是復制品。
其次,藝術不僅是一個視覺問題,還是整個人類社會綜合影響的產物。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及人們對它們的理解都會影響到藝術的范式[5]。
再次,如何理解藝術的歷史變遷,預測未來的范式轉換,是人工藝術創作的最大障礙。從現代藝術開始,藝術的形式和判斷藝術價值的標準已經不同于過去深刻和破碎的變化,這種變化無跡可尋,不能為人工智能的思維方式所產生。就像達·芬奇難以預測和理解杜尚,現實中藝術范式的轉變并無可循的規律。因此,目前人工智能的信息處理模式無法預測藝術的未來,也無法創作出具有獨特哲學內涵或視覺風格的藝術作品。
最后,從目前藝術的定義來看,其基礎是人類的創作,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是基本要求。從文藝復興到現代社會,人類在精神上需要由人創作的、以人為主體的純藝術。這不僅是對藝術的哲學表達,還是對其社會功能的表述。所以,藝術是徹底的人類社會的產物。
2.2.2 人工智能作品評價的困難
另一種觀點認為,人工智能并不總是客體或是人類的鏡像,其產生的藝術創作是獨立于人的,這才是其獨特的藝術價值所在。
在談到人工智能和藝術時,人們往往會陷入一個誤區:對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和藝術家創作的作品進行比較。但其實機器并不需要像人一樣創作。人類藝術家通過自己的生活經歷、文化背景、時代背景來構建自己的藝術語言,但機器的創造力只與它所能涉及的數據和算法有關,這是其與人的藝術創作規律不同的邏輯。人工智能藝術實際上是以算法為內核,在后人類語境下建構起一種虛擬性的藝術空間。
將來,高度發達的人工智能和人類可能發展出一種平等的關系。當人工智能發展到非常先進的水平時,機器會產生情感,理解美學,并能表達自己,創造出真正的具有個人意志的機器人公民。
藝術的定義決定了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能否被稱為藝術。但藝術是一個不斷拓展的概念。如果藝術賴以生存的人文體系、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而消亡,那么人類社會的底層結構就會發生質的變化,目前所有的運行機制如勞動、價值、經濟等都需要重新建立。在人工智能和經濟社會共振的趨勢下,藝術的邊界將被徹底重塑。
3 人類藝術的主體性和價值
3.1 藝術的主體性危機
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逐漸變得難以預知。未來,藝術創作的主體性很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6]。
因此,對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塑造不僅有關科學和哲學,而且關乎倫理和社會政治。人類所擁有的知識體系,甚至是價值體系,都將受到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巨大沖擊和挑戰。然而,在科技高速發展的當下,社會結構仍存在弊端。在很多層面,人類都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來應對這樣一場新的技術革命可能給人類倫理、人類行為和人本身帶來的影響和挑戰。
新技術革命正在改變人類現代文明的文化生態,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沖擊人類社會,甚至徹底改變人類的日常生活。而人工智能作為技術的抽象,極大程度上受到科技公司的影響。技術分化帶來的明顯的標準化和多樣化導致新的極權主義的產生。2018年誕生的新詞“技術備份”,入選牛津年度詞典,旨在強調對科技巨頭的批評和抵抗。2018年谷歌刪除了該公司一貫的座右銘“不要作惡”,代之以“做正確的事”。如果說“邪惡”是對過去某種共識的描述,那么未來的“正確”標準似乎被證科技巨頭們定義[6]。算法可以預測人們的欲望,操縱人們的情緒,甚至為人類作決定。數字獨裁的境地似乎已不止于科幻作品中。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對虛擬狀態下的人們現實處境的關懷。虛擬技術給人們提供了脫離現實的可能,而新的現實也隨之產生,如身體的延伸和疏離、認知的收縮和拓寬等。技術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切斷了人與世界的關系。
3.2 藝術主體性的意義
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指出,世界上有兩種驅動力:由概念驅動或由工具驅動。“如果我們人類的探索和發現是由‘概念驅動的,那么人們往往會用新的角度來解釋舊的東西;如果是由‘工具驅動的,人們會用舊的想法來解釋新的發現。”
藝術家需要保持敏銳的時代感和對時代的總體認識。大多數關注和應用新技術的當代藝術家仍然缺乏對數字時代激活的大眾傳媒、消費主義和尖端技術的思考,沉溺于作品的戲劇性效果的創造中,試圖調動各種感知力創造出強大的視覺沖擊[7]。互動性和沉浸式參與已經成為混亂的現代主義最重要和最流行的特征之一。但正如讓·鮑德里亞所指出的,這種感官刺激實際上是完全空洞和無意義的。居伊·德波認為,“以視覺效果為導向的‘場景展示顛覆了原有系統的價值。‘場景利用視覺洪流沖擊觀眾的感知系統,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追求變化,追求刺激”。
藝術家對未來的想象力不能被當前的科技現實所限制。在技術失控的時代,每個人都要重新思考生活是如何發展的,以及生活將朝什么方向發展。人工智能可以打敗李世石和柯潔,但如果它不能為莫扎特和貝多芬感到興奮,就不會為了一句悄悄話或一首好詩而展開有感情的創作。藝術應該從更宏觀的層面去觀照人類現實,彰顯人類主體的尊嚴和驕傲。保持人類藝術的主體性應當成為當今藝術的核心理念。
4 結語
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工智能將成為改變藝術的范式和塑造藝術新范式的一個重要因素,為人們提供另一種想象力和對藝術的認知。人類和人工智能之間在保持動態平衡的同時,相互定義、互相塑造。人類創造和人工智能之間的關系證實了拉康的鏡像理論:從來沒有真正的自我。人們總是通過外部世界的變化來感受和塑造自己,并通過技術建立新的自我。
但技術不應該是決定性的。人工智能在人類面前打開了無數的可能性,但藝術的未來、人類的未來還需要由人類自己選擇。
參考文獻:
[1] 孫曉霞.藝術概念史研究與藝術學理論的學科困境[J].南京社會科學,2018(12):123-130.
[2] 盧迎華:生產模式本身只是表面東西[J].東方藝術,2010(11):83.
[3] 顧亞奇,王琳琳.具身、交互與創造力:認知傳播視域下AI藝術的實踐邏輯[J].中州學刊,2023(1):170-176.
[4] 盛葳.從視覺機器到人工智能[J].藝術工作,2018(2):27-30.
[5] 王鋒,李偉.藝術與科技融合對人類生活改變的研究[J].文化產業,2023(5):149-151.
[6] 顧亞奇,王立銳.可供性視角下虛擬現實藝術的實踐與思考[J].美術研究,2022(2):109-113.
[7] 王甦.從主體間性到語境性:數字時代的藝術轉型[J].北京社會科學,2022(6):71-79.
作者簡介:葉思琪(2002—),女,江蘇泰州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殘疾人社會工作。
夏添一(2001—),男,江蘇南京人,本科在讀,研究方
向:技術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