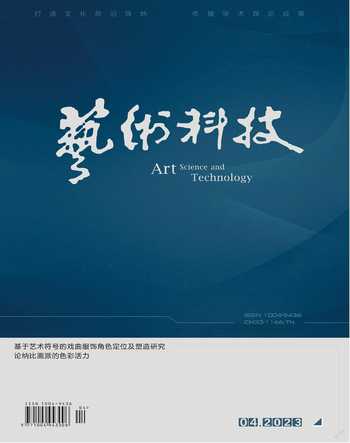東西方審美差異對(duì)音樂(lè)藝術(shù)的影響探析
摘要:音樂(lè)作為人類情感的表達(dá)形式,源自人的內(nèi)心。其借助樂(lè)器和歌聲,可以傳遞人的內(nèi)心情緒及感悟,因此有著獨(dú)特的魅力。各個(gè)國(guó)家、民族雖然在文字、語(yǔ)言、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水平方面存在差異,但是在音樂(lè)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東西方的音樂(lè)藝術(shù)雖然在演唱技巧、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方面存在一定的聯(lián)系,但是總體來(lái)看,在音樂(lè)審美上的差異較為明顯。這種差異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東西方在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中,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表達(dá)內(nèi)涵的演繹技法和遵循的思維模式不同。我國(guó)的民族音樂(lè)最早起源于勞動(dòng)人民,它是表達(dá)勞動(dòng)人民生活與情感的一種藝術(shù)形式,與美國(guó)的鄉(xiāng)村音樂(lè)存在相同點(diǎn)。但與此同時(shí),我國(guó)與西方音樂(lè)的藝術(shù)審美上又有較大的區(qū)別。基于此,文章對(duì)東西方音樂(lè)文化審美的共通性進(jìn)行分析,闡述東西方音樂(lè)文化審美的獨(dú)特性,并以黃自的《玫瑰三愿》和舒伯特的《野玫瑰》為例,對(duì)東西方審美差異對(duì)音樂(lè)藝術(shù)的影響展開(kāi)研究,以供參考。
關(guān)鍵詞:東西方;審美差異;音樂(lè)藝術(shù);審美影響;音樂(lè)審美
中圖分類號(hào):J60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9436(2023)04-00-03
0 引言
中國(guó)音樂(lè)藝術(shù)走過(guò)亙古漫長(zhǎng)的發(fā)展之路,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音樂(lè)文化審美[1]。因此,加強(qiáng)對(duì)東西方音樂(lè)文化審美共通性以及獨(dú)特性的解讀,可以為東西方音樂(lè)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共同進(jìn)步提供理論參考。
1 東西方音樂(lè)文化審美的共通性
1.1 東西方音樂(lè)語(yǔ)言文化的共通性
音樂(lè)作為一種聽(tīng)覺(jué)藝術(shù),在文化審美的形成上,主要是基于人的聽(tīng)覺(jué)器官,刺激人的身體反應(yīng),進(jìn)而調(diào)動(dòng)人的各種情緒。音樂(lè)是由一連串樂(lè)音構(gòu)成,綜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所在地域,可以展現(xiàn)出不同人的行為意志和社會(huì)情感。不管是什么樣的音樂(lè),都可以歸屬于人格情操范疇。東西方音樂(lè)均是綜合性藝術(shù),其中既包含情感和表演,又融合了語(yǔ)言和聲音。因此,不論是西方古典音樂(lè),還是我國(guó)的民族傳統(tǒng)音樂(lè),其音樂(lè)語(yǔ)言目的都在于體現(xiàn)本民族和本地域的文化,同時(shí)反映出音樂(lè)家的情感,只是這種反映方式是通過(guò)音樂(lè)符號(hào)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的。
1.2 東西方音樂(lè)情感表現(xiàn)的共通性
關(guān)于我國(guó)音樂(lè)和西方音樂(lè)作品,除了可以分析其中的音樂(lè)語(yǔ)言,掌握其中的音樂(lè)規(guī)律性之外,還可以通過(guò)分析音樂(lè)情感,找出其中的共同規(guī)律。雖然可能聽(tīng)不懂對(duì)方的音樂(lè)大意,但是可以通過(guò)樂(lè)曲曲調(diào),了解其中的情感變化,這便是東西方音樂(lè)的共通性。在情感表達(dá)上,我國(guó)音樂(lè)和西方音樂(lè)不論是詮釋樂(lè)曲情感,還是表達(dá)作者的感情,均是借助時(shí)代創(chuàng)作背景,利用一定的演唱技巧來(lái)達(dá)成目標(biāo)的。舉例來(lái)說(shuō),19世紀(jì)之前,西方地區(qū)在音樂(lè)創(chuàng)作上更加流行真實(shí)主義的創(chuàng)作、演唱技巧,尤以賈科莫·普契尼為代表,掀起了一陣熱潮。在旋律創(chuàng)作上,伸縮性特征十分突出,這也是演唱歌曲時(shí)的主要特點(diǎn)。在演唱的過(guò)程中,隨著音符增長(zhǎng)或縮短,演唱速度和音值發(fā)音會(huì)出現(xiàn)明顯變化。這些不同音樂(lè)要素的表達(dá),可以借助不同的音樂(lè)演唱技巧來(lái)實(shí)現(xiàn)。例如,演唱快樂(lè)的歌曲時(shí),聲音要明快、活潑;而若要表達(dá)作者的莊嚴(yán)情感和沉重情緒時(shí),則要保證聲音的渾厚。與此同時(shí),還要適當(dāng)運(yùn)用混合輕聲。另外,演唱明快的歌曲時(shí),要適當(dāng)融入相應(yīng)的語(yǔ)氣和感情,實(shí)現(xiàn)和創(chuàng)作背景的有機(jī)結(jié)合[2]。
2 東西方音樂(lè)文化審美的獨(dú)特性
2.1 東方音樂(lè)審美重空靈,西方音樂(lè)審美重厚重
東西方音樂(lè)在創(chuàng)作背景上存在差異,審美理念有所不同,這種差異在音樂(lè)主題內(nèi)涵上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東方音樂(lè)強(qiáng)調(diào)空靈和雋永,而西方音樂(lè)則需要保障旋律的厚重。制造意義始終是西方音樂(lè)家們樂(lè)此不疲的創(chuàng)作重點(diǎn),在表達(dá)音樂(lè)主題時(shí),更加趨近于實(shí)有。而東方音樂(lè)的表達(dá)則更加注重意象,將意義消解在音樂(lè)里,音樂(lè)表達(dá)趨向于虛無(wú)。
在西方的文化體系中,自然有著高度的獨(dú)立性,被看作具有一定現(xiàn)實(shí)意義的實(shí)體。西方音樂(lè)家在觀察和討論自然時(shí)非常細(xì)致,夢(mèng)想是征服大自然。體現(xiàn)在音樂(lè)中,有較為明顯的主題和觀點(diǎn),情感表達(dá)單一。對(duì)于音樂(lè)情感的題外之意以及音樂(lè)可以表達(dá)出來(lái)的弦外之音,其創(chuàng)作熱情相對(duì)較弱。因此,在進(jìn)行音樂(lè)表達(dá)時(shí),西方注重表達(dá)固定的實(shí)體內(nèi)容。除此之外,西方的音樂(lè)體系有較為細(xì)膩的織體,可以在縱橫交叉的音樂(lè)旋律中突出音樂(lè)的時(shí)代性。
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東方在音樂(lè)表達(dá)上更加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的空靈。在我國(guó)音樂(lè)體系中,就算音樂(lè)的創(chuàng)作主題是實(shí)體,也會(huì)通過(guò)各種旋律的調(diào)整,使音樂(lè)展現(xiàn)出不同層次的空靈之境。再加上東方音樂(lè)崇尚“虛”,不管是佛教提出的“空”,還是道教追求的“無(wú)”,抑或是儒教強(qiáng)調(diào)的“仁”,均是東方文化尚虛的重要表現(xiàn)。與此同時(shí),我國(guó)的音樂(lè)體系受到過(guò)去“致虛”“求同”文化的深遠(yuǎn)影響,音樂(lè)表達(dá)的空靈之感以及塑造的意境,成為音樂(lè)主題創(chuàng)作的重點(diǎn)。基于深層次意義來(lái)分析,中國(guó)音樂(lè)表達(dá)出來(lái)的空靈是人內(nèi)心與自然界空靈之景的有機(jī)結(jié)合,從而達(dá)到“天人合一”的表現(xiàn)效果[3]。
2.2 東方音樂(lè)深度主要表現(xiàn)為深邃,西方表現(xiàn)為深刻
深度與力度是衡量音樂(lè)作品質(zhì)量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但是在音樂(lè)的深度和力度表達(dá)上,目前東西方尚未制定出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綜合東西方音樂(lè)的實(shí)際特征,我國(guó)音樂(lè)在進(jìn)行深度表達(dá)時(shí)以深邃為主,而西方音樂(lè)則以深刻為主。西方音樂(lè)的深刻多是指音樂(lè)主題的深刻,而我國(guó)音樂(lè)的深邃則多用于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要表達(dá)的厚重情感以及人們通過(guò)音樂(lè)獲得的感悟。例如,《英雄交響曲》表達(dá)了革命的斗爭(zhēng)意象,突出的主題在于英雄,這便是西方音樂(lè)的深刻。而我國(guó)的《梅花三弄》則注重分析梅花的內(nèi)在氣質(zhì)以及其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高潔品質(zhì),這一表現(xiàn)形式在我國(guó)得到了普遍認(rèn)同。
西方音樂(lè)在力度表達(dá)上側(cè)重于強(qiáng)調(diào)強(qiáng)度,我國(guó)音樂(lè)則側(cè)重于強(qiáng)調(diào)深度。音樂(lè)作品需要塑造出空靈之感以及可以讓人想象的意境,并使用音樂(lè)來(lái)展現(xiàn)某種意象,讓人沉醉于音樂(lè),通過(guò)音樂(lè)來(lái)洗滌心靈。在處理多聲部關(guān)系時(shí),西方音樂(lè)多運(yùn)用主調(diào)音樂(lè)體系,實(shí)現(xiàn)主干音調(diào)和其他聲部之間的有機(jī)融合;而我國(guó)音樂(lè)則更加強(qiáng)調(diào)聲部韻律的獨(dú)立性,以對(duì)比和模仿的方式,保障獨(dú)立旋律得以整合。
3 東西方審美差異對(duì)音樂(lè)藝術(shù)的影響——以黃自的《玫瑰三愿》和舒伯特的《野玫瑰》為例
3.1 崇尚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
中國(guó)和西方國(guó)家由于地區(qū)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歷史和文化沉淀,所以在音樂(lè)審美上也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美學(xué)思想。
中國(guó)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最早源自西周時(shí)期,為禮樂(lè)思想。發(fā)展到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出現(xiàn)百家爭(zhēng)鳴的局面,儒家、墨家、法家均提出了音樂(lè)美學(xué)觀點(diǎn)。到了漢代后期,佛教也對(duì)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總體來(lái)說(shuō),儒家、道家的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貫穿了2000多年的發(fā)展歷程,對(duì)后世的音樂(lè)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我國(guó)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成熟時(shí)間較早,但是受到過(guò)去封建思想和等級(jí)制度的嚴(yán)重限制,在魏晉之后發(fā)展速度便越來(lái)越慢,同時(shí)也更加保守和陳舊。
西方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源自古希臘,畢達(dá)哥拉斯認(rèn)為,音樂(lè)之美在于其和諧性,可以讓人內(nèi)心免于騷亂,并通過(guò)音樂(lè)來(lái)獲得沉靜。中世紀(jì)時(shí)期,西方音樂(lè)美學(xué)受到嚴(yán)重限制,但是到近現(xiàn)代時(shí)期,一直發(fā)展到20世紀(jì)初期,西方的音樂(lè)美學(xué)逐步走向?qū)I(yè)化、科學(xué)化的發(fā)展之路,越來(lái)越多的音樂(lè)思想逐漸涌現(xiàn),音樂(lè)藝術(shù)也獲得了繁榮發(fā)展。自此,音樂(lè)美學(xué)研究更加側(cè)重于強(qiáng)調(diào)解決審美中的實(shí)際問(wèn)題。總而言之,西方音樂(lè)美學(xué)思想是在不斷批判傳統(tǒng)的過(guò)程中獲得發(fā)展的,始終保持著積極創(chuàng)新的態(tài)度。
《玫瑰三愿》和《野玫瑰》兩首歌曲,雖然都是以玫瑰為靈感創(chuàng)作的作品,但是兩者的時(shí)代背景、文化內(nèi)涵和美學(xué)思想不同,且東西方作曲家的音樂(lè)表達(dá)視角也對(duì)其產(chǎn)生了影響,故二者的音樂(lè)審美和情感表現(xiàn)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玫瑰三愿》創(chuàng)作于1932年,淞滬會(huì)戰(zhàn)結(jié)束之后,由于戰(zhàn)況較為慘淡,社會(huì)情緒低迷,在這樣的時(shí)代背景下,作者運(yùn)用小提琴和鋼琴伴奏創(chuàng)作而成,其在旋律上比較淡雅和平靜,隱藏著較為憂郁的情懷,更代表著對(duì)未來(lái)新生活的期許。而《野玫瑰》創(chuàng)作于1815年,旋律較為簡(jiǎn)潔明快,表達(dá)了較為活潑的情感,歌詞是由德國(guó)民謠改編而成,講述了少年想要摘下嬌艷的野玫瑰的故事,體現(xiàn)了非常深刻的浪漫主義情懷[4]。
3.2 表達(dá)內(nèi)涵的演繹技法
演唱是表達(dá)歌曲內(nèi)涵的主要方式,使用不同類型的演唱技巧會(huì)給人帶來(lái)不同的審美感受[5]。我國(guó)的音樂(lè)藝術(shù)歌曲多使用美聲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戲曲民歌有機(jī)結(jié)合的民族唱法,充分展現(xiàn)歌曲的情感,更加契合漢語(yǔ)的發(fā)音特征,同時(shí)注重淡雅、高潔,創(chuàng)造出獨(dú)具特色的藝術(shù)審美意境,也符合我國(guó)上千年來(lái)的審美要求。而西方藝術(shù)歌曲的演唱主要運(yùn)用美聲唱法,演唱時(shí)不要求聲音有多戲劇、音量有多宏大,而是更加強(qiáng)調(diào)感情的心理描繪,表現(xiàn)出歌曲的意境。
例如《玫瑰三愿》這首歌曲,歌詞咬字位置靠前,更加側(cè)重于強(qiáng)調(diào)歌詞的反復(fù),展現(xiàn)出強(qiáng)弱規(guī)律的變化過(guò)程,以含蓄內(nèi)斂的情緒為主,速度較慢。演唱時(shí),除了要表現(xiàn)出女性的柔情,還要確保音色的高度統(tǒng)一[6]。在主旋律上,側(cè)重于強(qiáng)調(diào)力度弱起,曲子中嬌艷的玫瑰就像是在訴說(shuō)對(duì)年華的哀婉以及對(duì)過(guò)去的留戀,能讓人感受到寧?kù)o傷感的情緒。而《野玫瑰》使用的則是美聲演唱技巧,演唱時(shí)需要保證吐字清晰、音色高度統(tǒng)一,聲音要有強(qiáng)大的穿透力,以展現(xiàn)出歡快活潑的音樂(lè)情緒。
3.3 遵循的思維方式
中國(guó)音樂(lè)在審美理念上,側(cè)重于非邏輯性思維,不受固定邏輯的限制和影響,以感性思維為主,講究創(chuàng)造出音樂(lè)的意境美,在創(chuàng)作上更加注重追求深遠(yuǎn)的意境,需要為人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間,同時(shí)讓人的思想情感得到升華。而西方的音樂(lè)審美更加強(qiáng)調(diào)邏輯思維和音樂(lè)實(shí)體。進(jìn)入20世紀(jì),西方音樂(lè)美學(xué)開(kāi)始融入心理學(xué)、數(shù)學(xué)和生理學(xué)等科學(xué)思想,因此吸納了大量的邏輯思維方法[7]。在創(chuàng)作音樂(lè)作品時(shí),需要注意調(diào)式和聲的布局方法以及織體技巧的使用創(chuàng)新,崇尚理性思維。
黃自的藝術(shù)歌曲風(fēng)格較為高雅,結(jié)構(gòu)十分鮮明,技巧較為細(xì)致,大量運(yùn)用調(diào)式和聲,同時(shí)還保留著我國(guó)的傳統(tǒng)識(shí)字文化。《玫瑰三愿》這首歌曲屬于單二部的曲式,結(jié)構(gòu)選取主要?jiǎng)澐譃閮纱蟛糠帧5谝徊糠质菍?duì)綻放的玫瑰花進(jìn)行描述,使用E大調(diào),旋律較為優(yōu)美,其中略帶傷感,描繪的是絢麗多彩的玫瑰花景象。第二部分則圍繞玫瑰花的愿望展開(kāi),襯托出創(chuàng)作者想要表達(dá)的情感。此時(shí),調(diào)性開(kāi)始轉(zhuǎn)變?yōu)殛P(guān)系小調(diào),曲子開(kāi)始走向高潮,并展現(xiàn)出未來(lái)的美好愿景。
舒伯特的藝術(shù)歌曲側(cè)重于調(diào)式和聲的使用,尤其是需要實(shí)現(xiàn)轉(zhuǎn)調(diào)、變和弦、變和聲上的全方位創(chuàng)新。《野玫瑰》的歌詞分為三段,使用的是G大調(diào),旋律清新,同時(shí)具有一定的邏輯性。曲調(diào)較為流暢明快,并運(yùn)用臨時(shí)升降記號(hào)來(lái)轉(zhuǎn)換調(diào)性,使用鋼琴作為伴奏,并運(yùn)用裝飾音和頓音,襯托出歌曲的歡快氛圍[8]。
4 結(jié)語(yǔ)
藝術(shù)在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的眼中呈現(xiàn)出不同樣貌,有不同的色彩,既是各民族重要的精神財(cái)富,更是人類社會(huì)的瑰寶。因此,相關(guān)從業(yè)者要了解東西方審美差異對(duì)音樂(lè)藝術(shù)的影響,在掌握其共通性、獨(dú)特性的同時(shí),為世界音樂(lè)的發(fā)展作出貢獻(xiàn)。
參考文獻(xiàn):
[1] 徐嗣宇.東西方審美差異對(duì)音樂(lè)藝術(shù)的影響及研究[J].黃河之聲,2022(6):72-74.
[2] 費(fèi)元洪.從東西方審美看中國(guó)音樂(lè)劇的未來(lái)[J].歌劇,2019(8):86-93.
[3] 侯曉.美學(xué)對(duì)音樂(lè)表演藝術(shù)的啟示[J].中國(guó)民族博覽,2022(12):165-168.
[4] 邵冀陽(yáng),孫偉.西方音樂(lè)史中審美認(rèn)同的個(gè)性問(wèn)題研究[J].戲劇之家, 2021(32):71-72.
[5] 王恪居.現(xiàn)代音樂(lè)美學(xué)研究對(duì)音樂(lè)表演藝術(shù)的啟示[J].散文百家·教育百家,2022(3):83-84.
[6] 李雨昕.音樂(lè)美學(xué)對(duì)音樂(lè)表演的影響探究[J].戲劇之家,2021(25):81-82.
[7] 李姝.中西音樂(lè)美學(xué)的比較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xué),2007.
[8] 孔彥夫.論長(zhǎng)笛藝術(shù)中東西方音樂(lè)的融合[J].音樂(lè)生活,2015(8):91-92.
作者簡(jiǎn)介:強(qiáng)小雪(2000—),女,內(nèi)蒙古包頭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音樂(lè)表演、音樂(lè)學(xué)、音樂(lè)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