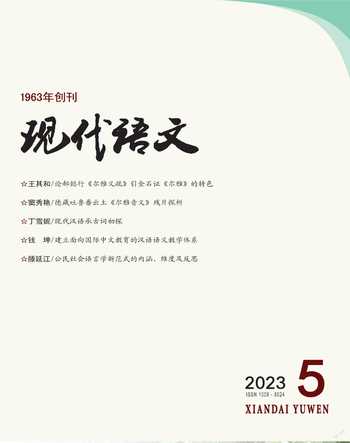法藏敦煌寫卷郭璞《爾雅注》回傳中國考述
曾令香,祁賽,任開迪
摘? 要:二十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17號藏經洞出土了六朝時期抄本郭璞《爾雅注》殘卷,編號分別為P.2661和P.3735號。由于諸種因素,兩者當時就被拆散,致使它們相隔上千個編號。目前,關于《爾雅注》敦煌寫卷的抄寫時代、文獻價值研究成果較多,但對《爾雅注》在法編目、回譯、綴合、影印出版等的研究還比較少。從敦煌寫卷《爾雅注》最初由不知名的字書、類書到被識認、被公布于世的過程,再現了敦煌文獻回傳中國的艱辛歷程。通過對這一學術史個案的探討,不僅有利于雅學史研究,也有利于百年敦煌學的全面研究。
關鍵詞:《爾雅注》;敦煌寫卷;法藏;回傳中國
二十世紀初,在敦煌莫高窟出土了南北朝至宋初文獻5萬多卷,其中,儒家經典寫卷9種300多件,在這些儒家經典寫卷中就有《爾雅》,包括《爾雅》郭注1部、白文《爾雅》2部,均為殘卷,分別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和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所藏均為伯希和劫掠品,主要有2種:一是P.3719號白文《爾雅》,存《釋詁》90條,《釋言》全部,《釋訓》83條,三篇連接不斷,只是《釋詁》前、《釋訓》后均殘缺,為同一部抄本①;一是郭璞《爾雅注》,大致有P.2661和P.3735兩個編號,后來綴合為一部,自《釋天》第8.4條“秋為收成”始,包括《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共五篇。英國藏斯坦因劫掠品S.12073白文《爾雅》,僅殘存一片,起《釋言》“懈怠也”條,至“間俔也”條,約9條。值得注意的是,P.3719和S.12073白文《爾雅》由于抄寫時代明確,書法水平不高,或是殘損嚴重,因此,研究者較少。而P.2661和P.3735《爾雅注》大約抄于六朝時期,書法俊秀,唐時又經過多人遞藏,同時,經注校勘輯佚價值較大,因此,學界頗為關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過,關于敦煌寫卷《爾雅注》出土后的收藏、目錄著錄、編目綴合、轉寫翻譯、影印出版等問題研究較少。對這些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探討,不僅可以豐富《爾雅注》寫卷的文本研究,同時也能夠為敦煌學學術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
一、敦煌寫卷《爾雅注》的編目及回譯
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不僅是精通多國語言的語言學家,也是學識淵博的漢學家。他憑著深厚的漢學功底和豐富的考古知識,把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所有的遺書通檢一遍,因此,他所劫掠的寫卷的學術性、藝術性價值頗高。1907至1908年,伯希和在新疆、甘肅等地盜掘西北文獻時,就已經開始了文獻編目工作,大約在1913年前已經有個簡目;后來日本學者、中國學者抄寫翻譯的,及伯希和本人帶在身邊的,都應該是這個簡目。
(一)伯希和所編《巴黎國家圖書館敦煌書目》著錄2661號
1908年,伯希和把6000余件敦煌寫卷運到法國,收藏于巴黎圖書館東方部。據楊劍宇《伯希和檔案整理討論》一文記載,“伯希和在中亞和敦煌收集文物過程中,‘都是拿起一個卷子就編一個號,后人在編目時,按此原始編號編目”,“1908年伯希和從敦煌回國后,就開始對漢文寫本編目,直到1920年才出版此簡目”[1](P80-81)。日本學者狩野直喜曾于1913年抄寫該簡目,可見,伯希和于1913年之前大概已經完成簡目初稿。實際上,1920年該簡目并未正式出版,1935年王重民曾應巴黎圖書館之請而予以補苴。又據《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載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分部部長郭恩序稱,1910年4月,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挑選的6000余份敦煌遺書入藏法國國家圖書寫本部,“伯希和把前二〇〇〇號留作藏文手稿的編號,然后親自進行自二〇〇一號開始的漢文文獻編號……其他文字如粟特文、于闐文或回鶻文書寫的文獻數量不多,很早就編在三五〇九號以后,伯希和好像認為有一千五百個編號足夠漢文文獻使用了”,“伯希和開列的原始清單非常簡短,他沒有時間全部完成,更說不上去為文獻編目了”[2](序,P2)。通過上述信息可知,伯希和編目的前2000號是藏文編號;2001號以后是漢文編號,大約有1500個,即2000號至3500號為漢文寫本編號。同時,該目錄最初只有編號、書名等簡單信息,是賬目式的“原始清單”。郭璞《爾雅注》的兩個編號中的P.2661應該是在這一時期編定的,而P.3735號則極有可能是后人續編的。據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載,伯氏的簡目原名應該為《巴黎國家圖書館敦煌書目》,最初并未出版,為寫本,中、日學者均曾抄錄過,并最早由羅福萇、陸翔翻譯給國內學界。
(二)羅福萇所譯為“伯希和原始清單的摘錄”
羅福萇(1895—1921)為羅振玉第三子,“年未冠,既博通遠西諸國文字,于法朗西、日耳曼語,所造尤深”[3](卷23,P702)。1923年,《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刊載了羅福萇遺作《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上)》,這是伯氏簡目的第一個中譯本。羅福萇的翻譯頗費周折,據羅振玉《亡兒福萇遺著三種序》稱:“英法兩京所藏敦煌石室《書錄》各
一卷、《寫經后題錄》一卷,亡兒福萇所輯錄也。英
京《書錄》乃得之法儒沙畹博士寫寄,及臨時陳列之目錄見之雜志中者,會最成之;法京《目錄》則就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游歐時錄本、與得之伯希和博士者,參考移錄。”[4](P160)由此可知,羅福萇曾翻譯英、法兩國所藏敦煌文獻目錄,其中,法藏伯希和簡目分別是由日本學者狩野直喜與伯希和本人所提供的,在此基礎上“參考移錄”而成,實際上,羅福萇的翻譯工作大致經過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在1919年以前完成了初譯本。1911至1919年間,羅氏父子曾寓居日本,與狩野直喜過從甚密,初譯時的資料就是由狩野直喜提供的。狩野直喜(1868—1947)是日本著名漢學家,1910年曾來中國調查甘肅運抵北京的敦煌寫卷,與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相識交好。1912年9月至1913年間,狩野直喜曾奉東京帝國大學之命,赴歐洲考察中國學和東方學。1912年10月至法國,當時一些敦煌文獻資料尚在整理之中,一般不對外公開,在伯希和的關照下,被特許入巴黎國家圖書館查閱敦煌遺書。他的工作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翻閱敦煌古書,二是抄錄伯希和所作的目錄。1913年1月,他在給桑原騭藏、內藤湖南的信中報告了在巴黎的工作情況,并介紹了伯希和編撰的敦煌文獻目錄。他說:“這份目錄并未出版,是伯希和先生自己整理書寫的。假如是漢字目錄還好一些,遺憾的是,他是根據漢語發音用羅馬字拼寫的,題目下面加入一些法語的解題注解,加上伯希和先生的字跡不好辨認(對我來說),所以進展不是很順利。……十二月底好不容易全部完成,權且作為帶回日本的禮物……全部藏書共有一千五百多份,到底無法都一一看遍。”[5](P79)可見,狩野直喜見到的是伯希和簡目的手稿,它是根據漢語發音用羅馬字拼寫的,題目下有“法語的解題注解”,同時,這個簡目確實是著錄了1500余號。由于識讀、抄寫比較復雜,狩野直喜應是頗費了一番轉寫功夫的。1913年,狩野直喜回國后把自己所抄的敦煌資料提供給時在京都的羅振玉、王國維研究,羅福萇不但協助狩野直喜整理出所抄英國藏本《沙州文錄補》,而且得到了狩野直喜所轉抄的敦煌文獻目錄,并著手翻譯,在1919年回國前應當是完成了譯本初稿。
第二個階段,得到伯希和本人親自贈送的簡目,最后完成翻譯定稿。1919年春末,羅振玉全家從日本回國,在上海“忽與伯希和博士邂逅,亂后重逢,相得益歡……福萇手錄其所訂敦煌古籍目錄。鄉人(羅振玉)略依四部類次,記之于凝清室日札中(壬戌七月稿,未刊)”[6](P76)。伯希和于1916至1919年調任法國駐華使館陸軍武官次官,1919年離任之前與羅氏父子在上海相遇。這次重逢,伯希和把漢文寫本目錄(P.2001—3511號)出示給羅福萇,羅福萇對校了在日本時的譯稿,至此全部簡目翻譯完成。
1923年,羅福萇遺作《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上)》在《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發表,收敦煌漢文寫本自2001號至2700號,共700號,其中即有2661號,但伯氏簡目只題為“殘類書二篇”,譯作“一歲名,月名,風雨。一釋地,十藪,八陵,九府,五方,野”[4](P747),并未指明它為《爾雅》,信息也比較簡略。1932年,羅福萇所譯伯希和氏書目續篇在《國學季刊》第三卷第四號發表[7](P733-772),收入2701—3511號,兩期共翻譯了1511個編號。羅福萇所譯的《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最早向國內公布了法國藏敦煌漢文文獻的總體情況,推動了國內敦煌學的研究。
羅福萇所譯《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應該是伯希和簡目的簡譯本,只有編號、書名、卷數,部分編號曾用括號形式加以簡單地說明。狩野直喜所說“題目下面加入一些法語的解題注解”,這部分羅福萇并未翻譯,與陸翔譯本相比,羅譯本刪節較大,這也使其所譯目錄的價值大打折扣。羅福萇才華橫溢,精通法文、日文,羅馬字對于他來說亦非難事,大概節刪原則在翻譯之初就已確定,或許是他長期抱病在身、精力不濟的緣故吧。因此,伯希和簡目比較完整的譯作是由陸翔完成的。
(三)陸翔所譯伯氏書目可見P2661號全貌
陸翔(1883—?),字云伯,江蘇吳江人,著作有《敦煌學著述考》,譯作有《敦煌石室訪書記》《中國西域探險報告書》等。陸翔翻譯的底稿是他震旦大學時的同學張鳳提供的。張鳳(1887—1966),字天方,浙江嘉善人,1922至1924年曾留學法國,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期間曾經協助馬伯樂整理斯坦因所劫掠西域簡牘,1931年出版了《漢晉西陲木簡匯編》。張鳳在巴黎求學時,曾經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抄錄伯希和敦煌文獻目錄一部。1930年于滬上與陸翔重逢,并把所抄目錄贈予陸翔。陸翔精通法語,當時僅見到羅福萇翻譯的《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上)》的前700號,而“羅譯于伯氏按語,頗多漏略”,于是決定重譯伯氏目錄,在翻譯時,“伯氏按語,悉遵原文,不敢刪節,以存其真”[8](P12)。1931年冬翻譯完成,1933年發表于《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七卷第六號[9]。在陸氏所譯還未及刊發時,由羅福萇翻譯的《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下)》于1932年發表。兩個譯作條目大致相同,但繁簡差別較大。從陸譯本來看,不但補出了伯希和的注解文字,而且糾正、增補了一些內容,同時還添加了按語,如訂正書名、補充了殘損程度的描寫,其學術價值、應用價值更大。二人所譯的P.2661號如下:
羅譯:二六六一 殘類書二篇(一歲名,月名,風雨。一釋地,十藪,八陵,九府,五方,野。)[4](P747)
陸譯:二六六一 華文。兩節極殘損,而字卻佳,最遲當為八世紀所書。中為類書二篇。今存歲名、月名、風雨(第八篇)及第九篇《釋地》之一分:十藪,八陵,九府,五市【方】,野。搜集之書頗為詳備,(修補后可攝影)背為星占書。”[9](P66)
由此可見,伯希和編目時僅把2661號定名為“類書”,羅譯比較簡單,而陸譯的內容則更為豐富。我們從陸譯中可以獲知以下信息:第一,P.2661包括《釋天》“歲名,月名,風雨”,《釋地》“十藪,八陵,九府,五方,野”,并且“兩節極殘損”。第二,伯希和斷此殘片“最遲當為八世紀所書”,最早提出其抄寫時代問題,也就是其下線為唐中期前。第三,伯希和還交代了P.2661號殘片背面是“星占書”,它“修補后可攝影”,或許已經列入伯氏攝影計劃中。
總之,羅福萇、陸翔所譯目錄雖然簡單,尤其是《爾雅注》尚未識別定名,卻為中國學人提供了域外搜求敦煌文獻的線索,功不可沒。
二、敦煌寫卷《爾雅注》收藏信息的發布與綴合
如前所述,羅福萇、陸翔所譯均為伯氏簡目,即2001號—3511號目錄,因此,并未包括P.3735號;同時,P.2661號也尚未識別定名。那么,是哪位學者首先將P.2661號判定為郭璞《爾雅注》的?P.3735號最早又是由誰整理公布,并與P.2661號綴合的?下面,我們就對這些問題一一解答。
(一)董康最早發布了敦煌出土文獻《爾雅注》的信息
1907年、1908年,敦煌卷子分別被斯坦因、伯希和捆載至倫敦、巴黎。自1909年始,中外學者就開始了訪求、拍攝、出版、研究工作。其中,中國學者董康就是較早奔赴巴黎、倫敦訪求敦煌遺書的學者之一。
董康(1867—1947),字授經,江蘇武進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藏書室名“誦芬室”,自號誦芬主人,是中國近代著名藏書家、刻書家、法學家。董康曾說自己“一生以影印異書為唯一之職志”[10](P2),
著有《誦芬室叢刊》等。1909年,羅振玉輯錄的《敦煌石室遺書》即為誦芬室刊行。1922年,董康赴歐洲考察,曾在歐洲調查敦煌遺書,撰成《敦煌莫高窟藏書錄》,記錄了在歐洲所見漢籍173種,并拍攝了60多張影片。不過,董康此行并未見到《爾雅》①。董康的《東游日記》(又稱《書舶庸譚》),記載董康1926至1936年間四次東游日本訪書的經歷,其中記錄了他與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的交往,以及在內藤湖南處觀看敦煌遺書影片的經過,并最早發布了敦煌遺書中有關《爾雅》的信息。
1924—1925年,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攜董康《敦煌莫高窟藏書錄》赴巴黎、倫敦訪求敦煌遺書,手錄釋文,并拍攝了1000多張影片,收獲頗豐。1926—
1927年,董康避難日本期間,曾參觀內藤湖南所搜集的敦煌遺書資料,見到了《爾雅》影片。據《東游日記》記載,1927年1月2日,董康拜訪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倒履相迎,“復出敦煌遺書影片,約二百余種。中有余未寓目者,懇以每日借攜回寓校錄,得其首肯”[10](P3)。1月9日日記載:
閱敦煌影片,內六朝本《爾雅》一卷,存《釋天》八、《釋地》九。首尾殘缺,取與阮刻本互校,除別體字及注語尾增加助詞從略外,可以是正刻本者約三十四條。如“十月為陽”下注云“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以名之”,今本作“純陽”,則與下句抵觸,此訛謬之顯然者也。又古本形似之字,每多通用,如唐人寫本“循”“備”“脩”三字互書,閱者繹其文義,當可明晰。此本“戴”“載”二字雖近似,然“戴”則注之于首,“載”有載重之義,本卷各“戴”字,皆含注于首之義,刻本作“載”,非是,是以知《禮記》之“載鴻載鳴鳶”,亦宜從“戴”也。[10](P12)
董康并未言明內藤湖南拍攝影片之編號,但它顯然與羅福萇、陸翔所譯的伯希和編目之P.2661號相合。其研究成果很快就刊登于《國學(上海)》1927年第一卷第四號上[11](P12),題為《六朝本爾雅》,內容與《東游日記》相同。此文雖然僅200余字,但具有多項開創意義。首先,它最早向國內學界發布了敦煌出土文獻中有關《爾雅》的信息;其次,關于抄寫時代,伯希和的下線是“最遲當為八世紀所書”,而董康則定為“六朝本”,王重民亦持此觀點,但該文比王先生的論文(1935年)刊發要早;第三,它最早對《爾雅》殘片作了校勘,肯定了其版本、學術價值。
(二)王重民首次綴合了P.2661號和P.3735號
第一個把P.2661號與P.3735號《爾雅注》綴合的是中國學者王重民。王重民(1903—1975),河北高陽人,目錄學家、敦煌學家。1934年,北平圖書館選派王重民、向達二人分別赴巴黎、倫敦查閱、抄錄和拍攝敦煌文獻。王重民在巴黎研讀了2000多份敦煌卷子,為一些卷子撰寫了《敘錄》,拍攝了近3000張縮微膠片,并為伯希和簡目作了“注記”,其成果就是著名的《伯希和劫經錄》。
《伯希和劫經錄》是1934至1939年王重民在巴黎期間,為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漢文文獻2001號至5579號編目所作“注記目錄”的副產品。王先生校對、訂正、補充伯希和原有“賬簿式”的編目,即在伯希和簡目的基礎上校正原卷之題名,為未定名的無題目卷子定名,并加上若干注釋性質的記錄。在《伯希和劫經錄》中②,王先生對2661號的注記為:“《爾雅殘卷》(郭璞注),存釋天至釋地。背為方技書,名《諸雜略得要抄子》。”[12](P269)對3735號的注記為:“《爾雅卷中殘卷》(郭璞注),存釋地至釋水,與2661號為同卷。背為方技書,名《諸雜略得要抄子》。”[12](P294)王先生首次明確提出兩個編號均為郭璞《爾雅注》,并標明為同一部書的殘卷。
1935至1940年,王重民在《北平圖書館館刊》《圖書季刊》《金陵學報》等刊物上陸續發表敦煌寫卷提要80余篇,并編成《巴黎敦煌殘卷敘錄》第一輯、第二輯,向國內及時發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嘉惠國內廣大學者。其中,《爾雅郭注殘卷敘錄》于1935年發表在《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該文稱:
《爾雅》郭璞注殘卷,存《釋天》至《釋水》第十二。自《釋地》“岠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句,斷為兩截。今《巴黎國家圖書館敦煌書目》上截著錄在二六六一號,下截著錄在三七三五號,驗其斷痕與筆跡,實為一卷。唐諱不缺筆,蓋為六朝寫本。卷末有天寶八載題記,大歷九年書主尹朝宗記,乾元二年張真記,并是閱者所題,不得據以定為唐寫本也。持與今本《爾雅》相較,經文之異者……昔有唐本《說文》本部,流出人間,咸同學者,詫為稀世之珍,況此《爾雅》五篇更為六朝寫本乎?復活節日記。[13](P75-76)
“復活節”為此文的撰寫時間,即1935年4月21日。從此文來看,王先生主要作了以下工作:第一,明確了2661號、3735號為郭璞《爾雅注》,并斷定兩個編號出自一書;第二,從避諱、卷后題記、與今本對校等,判定《爾雅注》為六朝寫本;第三,對《爾雅注》經、注與今本作了對校,并對“丘背有丘”“厓內為隈,外為?”等6條經、注作了疏證,充分肯定了古本《爾雅》的價值。
王重民當時也拍攝了2661號、3735號影片,現藏國家圖書館。這些影片由于拍照年代較早,與上世紀50—70年代法國國家圖書館拍攝的縮微膠卷相比,也更為完整。許建平《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爾雅之屬》“《爾雅》(釋天—釋水)校記”,多以王先生照片為對勘,引證十余例。如《釋地》郭注“醫無閭山名”,許校記云:“‘醫字縮微膠卷左邊小半殘泐,此據國家圖書館藏王重民所攝照片。”[14](P2058)至此,關于敦煌寫卷《爾雅》郭注的著錄逐漸完善。
1935年,姜亮夫曾自費去法國留學,在巴黎調查敦煌遺書時,遇到王重民,于是主動放棄攻讀博士的機會,加入到研究敦煌文獻的行列。在此期間,他也目驗了2661號和3735號《爾雅》郭注;在其后撰寫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一書中,姜亮夫提出了與王先生不同的看法[15](P132-133)。相關內容可參見《從敦煌寫本〈爾雅〉郭注用字看其抄寫時代》一文[16],此不贅述。
三、敦煌寫卷《爾雅注》的影印出版
很多敦煌寫本原件被禁錮在歐洲的巴黎、倫敦,對于絕大多數研究者來說,親赴英、法訪求是很不現實的。因此,敦煌文獻圖片資料的結集、影印出版,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內藤湖南、王重民等在巴黎拍攝的上千張影片均未出版,最早刊印敦煌資料影片的是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
神田喜一郎(1897—1984)受業于內藤湖南,是日本著名的漢籍目錄學家。1935年,赴歐洲調查敦煌遺書,拍攝了1000余張影片;歸國后,于1938年由日本京都小林寫真制版所出版了《敦煌秘籍留真》。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自序》云:“三十年來,東方學者先后訪之,著錄亦美備矣。顧其有景本者,除羅氏雪堂所印行數十種外,寥寥無幾。至若蔣氏《沙州文錄》、羅氏《石室碎金》、劉氏《敦煌掇瑣》諸書,皆唯迻錄文字,不具寫照,即其文字,未必無違失,讀者猶有憾焉。乙亥春,余奉官命游學巴黎,滯留逾年,日課閱書于館,每觀奇帙善本,輒自攝影,次第枚舉,殆以千記。乃不忍終秘,欲付景印,以廣流傳……
而事繁費巨,苦其難舉。茲擇其尤精者,輯為書景,先餉諸世,曰《敦煌秘籍留真》。”[17](P153-154)其中,第一輯共出版63種書籍的書影,分為上、下兩卷。需要指出的是,《敦煌秘籍留真》只是選取每種書中的一二頁影印,如《爾雅注》僅影印了2661號與3735號《釋山》《釋水》相鄰的一頁,以及卷后尹朝宗、張真題記的一頁[17](P178-179),讀者無法獲睹全貌,令人遺憾。正如周一良所指出的:“每種影印一二葉,有題記者兼存其題記。惜只鱗片羽,復不注明原存行數。足供談書法源流者之考鏡,而裨益于學術研究者無多。唯其所收殘卷之題記頗有值得注意者,在王有三先生所照巴黎之寫本未印行發表前,此書要亦為治敦煌之學者所不廢也。”[18](P150)
陸志鴻指出:“(《敦煌秘籍留真》)各為單篇零葉,嘗鼎一臠,未盡饜人望;于是出其全部,復擇尤景印,計得二十三種,名曰《敦煌秘籍留真新編》,雖種類較寡,而每種葉數,則大有增多,蔚為巨帙。”[17](序一,P245)
為了彌補《敦煌秘籍留真》的遺憾,神田喜一郎又選擇了23種書籍予以影印,名為《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共兩卷),于1947年出版。《爾雅注》2661號和3735號也得以入選,在卷下,共12頁,這是兩個殘卷首次綴合影印。此次綴合雖然12張殘片的順序沒有問題,但殘片上下、左右的對接還比較松散,同時也略有殘缺,如《釋天》“為皋六月為且”至“婁也大梁昴也”20行闕如[17](P521-532)。因此,這次綴合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敦煌秘籍留真新編》的影片是黑白色,經文文字比較清晰,注文要稍差一些,但同王重民拍攝的影片一樣,因其時代較早,與后來法國國家圖書館所拍攝的縮微膠卷相比,殘卷的頁邊文字要相對完整一些。如《釋地》“歫齊州”中的“齊”字,法國國家圖書館拍攝的底片僅存左側殘畫,“州”字右上角殘泐,而這兩個字在《敦煌秘籍留真新編》中均保存完好。因此,《敦煌秘籍留真新編》至今仍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1981年,黃永武編纂出版了《敦煌寶藏》,其中,第123冊第167—172頁始收入完全綴合的2661號、3735號《爾雅注》影片,題為《爾雅卷中》。其影片以巴黎國家圖書館所攝縮微膠卷為底卷,較為清晰。1986年,黃永武又編纂出版了《敦煌古籍敘錄新編》,此書為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之文配上影片資料,首次影印了3719號白文《爾雅》,在第四冊第296—303頁,而2661號和3735號郭璞《爾雅注》在第四冊第304—337頁。至此,法藏敦煌出土的《爾雅》敘錄、影片全部收齊。
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其影片為法國國家圖書館所拍攝的高清晰度的微縮膠卷,2661號和3735號《爾雅注》位于第17冊第125—129頁,3719號白文《爾雅》位于第27冊第110—111頁,兩種《爾雅》的圖片資料均比此前出版的圖片資料更加清晰。
2018年,中國國家圖書館網站發布了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贈的5300余號文獻、共3.1萬余張影片,皆為敦煌遺書高清數字資源,其中也包括了法藏的《爾雅》2種8張,圖片清晰,可放大觀看,毫厘畢現,相對于紙質文獻來說,使用也更加便利。雖然如此,研究寫本《爾雅注》文字,仍需把王重民、神田喜一郎、黃永武所攝所印影片與國圖高清影片進行比較,只有這樣,才能使研究成果更為科學、準確。
綜上所述,經過中外學者的持續努力,敦煌寫本郭璞《爾雅注》殘卷終于回傳故土,成為《爾雅》學研究的重要資料。與此同時,我們也為敦煌寫本《爾雅注》的殘損而深感遺憾。當年敦煌寫本發現時是成捆地堆放于藏經洞中的,此時《爾雅注》應該是保存完好的,由于伯希和等的盜掘而使這些文獻人為地分離。伯希和雖然是漢學家,從他編目時將此書定為類書和2661號與3735號相隔上千個號碼來看,他對《爾雅》并不熟悉。伯希和之所以會選擇《爾雅注》,大概主要是看重了該寫卷的書法價值及其有別于佛經的特征。羅福萇、陸翔翻譯敦煌文獻目錄,使國內學者得以了解法藏敦煌文獻的大致情況,具有重要意義。董康、王重民等學者親赴巴黎探訪敦煌遺書,為《爾雅注》殘卷的面世、綴合作出了杰出貢獻。神田喜一郎、黃永武等中外學者編撰、刊行敦煌文獻,則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敦煌寫卷郭璞《爾雅注》的編目、回譯、綴合、影印出版,實際上也是敦煌文化研究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是當時中外學者多方搜求、精心考釋、辛勤付出的真實寫照。在國力昌盛、文化繁榮的新時代,我們要繼承前輩學者的奉獻精神,秉持家國情懷,堅持人民立場,進一步推動《爾雅》學研究和敦煌學研究,向國際社會展示我國敦煌文物保護和敦煌學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學研究的話語權。
參考文獻:
[1]楊劍宇.伯希和檔案整理探討[J].檔案學通訊,2005,(4).
[2]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3]王國維.觀堂集林[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羅福萇譯.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上)[J].國學季刊,1923,第一卷第四號.
[5][日]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M].高野雪,初曉波,高野哲次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6]甘孺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M].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內部發行).
[7]羅福萇譯.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下)[J].國學季刊,1932,第三卷第四號.
[8]陸翔.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序[J].國學論衡, 1934,(3).
[9][法]伯希和編,陸翔譯.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J].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33,第七卷第六號.
[10]董康.董康東游日記[M].王君南整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董康.六朝本爾雅[J].國學(上海),1927,第一卷第四號.
[12]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A].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二冊)[C].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13]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敘錄(一):爾雅注[J].國學季刊,1935,第二卷第二號.
[14]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8.
[15]姜亮夫.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16]曾令香,竇秀艷.從敦煌寫本《爾雅》郭注用字看其抄寫時代[A].華東師范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華東師范大學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中國文字研究(第三十六輯)[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17][日]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敦煌秘籍留真新編[A].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十三冊)[C].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18]周一良.敦煌秘籍留真[J].清華學報,1948,第十五卷第一期.
Research on the Guo Pus Erya Zhu(《爾雅注》) of the French Collection Dunhuang Manuscript Spread back to China
Zeng Lingxiang,Qi Sai,Ren Kaid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ragments of Guo Pus Erya Zhu(《爾雅注》)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manuscript were unearthed in the No.17 Zangjing Cave of Dunhuang, numbered P.2661 and P.3735 respectively. Due to the discoverer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Erya(《爾雅》), it was dismantled at that time, resulting in them being separated by thousands of number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era of transcription and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in Erya Zhu(《爾雅注》). The process of Erya Zhu(《爾雅注》) from an unknown word book and classification book to being recognized in the world reappears the path and difficult process of the return of Dunhuang literature, which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Ya Xue, but also conducive to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Dunhuang Studies for a hundred years.
Key words:Erya Zhu(《爾雅注》);Dunhuang manuscript;French collection;spread back to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