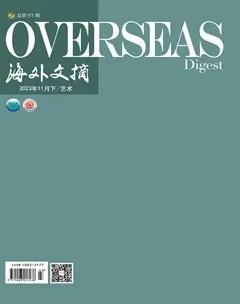“外江戲”的演變與粵東客家文化的交織
王子熙 李恩卉
外江戲,最初指清朝同光年間以皮黃為主聲腔的潮梅外江戲,后由廣東大埔人錢熱儲于1933年正式命名為漢劇。本文詳細回顧了漢劇的起源、發展,以及它如何深受皮黃漢調的影響,并最終北上成就京劇,南下影響粵劇等地方戲曲。同時,本文著重分析了漢劇與客家文化間的互動:從經濟不發達的客家山區到繁榮的潮汕地帶,漢劇不僅獲得客家人的深厚喜愛,而且在客家文化的支持下得以保存和發展。此外,本文還討論了客家人對漢劇的情感寄托和文化認同,以及漢劇如何成為客家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而深化了兩者之間的相互成就與促進關系。
0 概念釋義
外江戲,廣義是指清初以來廣東地區對外來戲曲樣式的統稱,狹義則指從外地來到本地演出的戲班。清朝同光年間(1861年-1908年),外江戲特指一支分布在“贛之南,嶺之東,閩之西部”、以皮黃為聲腔主體的潮梅外江戲。1933年,廣東大埔人錢熱儲提出外江戲改名漢劇。他在1933年出版的《漢劇提綱》“作書緣起”中開宗明義:“何謂漢劇?即吾潮梅人所稱外江戲也。外江戲何以稱漢劇,因此種戲劇創于漢口故也。”隨后他還講,“漢劇作于漢口,流行于鄂皖之間,經安徽石門桐城、休寧間,人變通而仿為之,又稱徽調。自是而后,乃復分支,流而北上者經北京人將唱白弦樂鼓樂悉易高亢之音,稱為京劇。今亦稱平劇。流而南下者,至廣州一帶,又經粵人易以喧鬧之音,稱為粵劇。惟在贛之南,嶺之東,及閩之西部者,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故特標其名曰外江。試觀今之平劇粵劇,與夫外江劇,其皮黃曲調,皆大同小異,其舊傳劇本,皆十九相同,可以證明其同源異派。又吾南方人俗語,稱長江一帶人皆曰外江人,今以戲劇特稱外江劇,則其中音節關目,皆屬漢劇真傳不加易變,更可了然。[1]”
1 外江戲的歷史和發展
清代中葉,漢劇在湖北形成,原以秦腔經襄陽南下演變出來的西皮為主要腔調,后來又吸收了安徽傳來的二黃。早期同徽劇經常相互影響,形成了“徽漢河流,皮黃交融”的皮黃腔風格。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又逐漸形成了襄河、荊河、府河、漢河四支流派。分別以襄陽、沙市、德安(今安陸市)、漢口為中心。襄河派以襄樊為中心,沿漢水向外傳播,上至鄖陽,下至鐘祥,流播到陜西,河南南陽、許昌等地。府河派主要流播于隨州、棗陽、孝感、黃陂以及河南信陽、駐馬店和山西晉陽等地。漢河派主要傳播于鄂東南的成寧及鄂東的黃岡地區,并向外流播安徽、江西等省。最值得注意的是,荊河派,以沙市為中心,不斷向周邊輻射,不僅在湖北境內向西形成了南戲,還沿荊河流播至湖南,并進一步傳播到廣東、江西、福建、廣西、四川等地。在這一過程中,荊河派的皮黃調被荊河戲、常德漢劇(后改名武陵戲)、湘劇、祁劇和桂劇等地方戲種吸收,形成了各自的主要聲腔。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不同劇種對皮黃腔的稱謂均為“南北路”[2],展現了驚人的一致性。
清嘉慶、道光年間,漢調流傳到北京,加入徽調班社演唱,逐漸融合演變而成京劇。而粵劇的形成相對較為復雜。從明中葉到清中葉在廣東流行過的戲曲品種,有切實資料可查的有弋腔、昆腔、梆子、徽調 (石牌 )、漢調( 楚腔 ) 等。除昆腔外有時把其他品種稱為 “亂彈 ”“梆子亂彈 ”“亂彈諸腔 ”這些戲班統稱為 “外江班 ”[3]。“乾隆末年,外江班達到高峰,上會戲班達50余個,從業人數保守估計兩千(以每班40人計)開外,徹底改變此前昆班主宰廣州劇壇的局面,而形成了以徽班、湘班為主的亂彈時代。”清代興建的廣州梨園會館的碑記中,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粵44個外江班中,徽7班,湘18班。這說明,在乾隆年間來粵的“外江班”中,徽和湘所占比例很重[4]。而歐陽予倩、周貽白、黃鏡明等學者認為皮黃腔早在乾隆年間就已隨徽劇陸續傳入了廣東。此外,這些湘班又都以漢調自名,雖有長沙班、祁陽班、常德班、岳陽班之分,其腔調都稱 “南北路 ”,只祁陽班雜有昆腔,長沙班兼唱高腔,因此粵劇又籠而統之地將“南北路”稱為漢調。綜上所述,粵劇在演變過程中,以徽班和湘班為媒介,深受皮黃漢調的影響。
咸豐八年(1858年),潮汕汕頭被正式開辟為英法與粵東的通商港口,由此迅速崛起,成為粵東、贛南、閩西地區的重要港口與商貿集散地,一躍成為粵東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遵循“商路、官路即戲路”的理念,這里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文化需求吸引了眾多外江戲班來此演出,以滿足不斷壯大的觀眾群體的文化需求。隨著外江戲班的大量涌入,潮汕地區逐漸成為了一個戲劇文化的交匯點。到了光緒元年(1875年),為了適應這一文化交流的需要,外江戲班在潮州上水門區域捐資興建了“外江梨園公所”。這里不僅是他們的集會場所,也是各類文化活動的舉辦地。
康保成、陳志勇認為,外江戲進入粵東潮汕地區,其中一條重要的路線是從贛南,經閩西,再至大埔、梅縣,最終抵達潮、汕。另外兩條路線,一條由廣州至海陸豐,至梅州,再順梅江、韓江到潮汕;另一條是直接從陸路,即從贛南的贛縣,再經尋烏,陸路80里進入梅屬諸縣。三條不同的路線圖都傳達出一個共同的信息:即外江戲進入粵東,首先到達的就是以大埔、梅州為代表的客屬聚居地,并在此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駐點[5]。此觀點與民國時期潮戲研究專家蕭遙天的論述相契合。他曾明確指出:“外江戲之入廣東……其流入之路線必由閩西贛南經客家繁布之梅屬諸縣。[6]”“外江則自安徽播贛南、閩西,經客族嘉應州而至。[7]”
鑒于當時梅屬客家地區經濟基礎尚處于發展階段,大多數具備實力的外江戲班并未選擇在此長期發展,而是轉向了粵東經濟中心——潮汕。但不可忽視的是,從此時起,客家人便深信外江戲正是他們的祖先南遷之前,在中原地區所演唱的戲曲。穿越客屬各縣市,這些外江戲班無疑也感受到了客家民眾對外江戲藝術的濃厚熱愛和期盼。
2 漢劇與客家文化的融合
在清代同治至抗日戰爭前的近百年時期,外江戲在潮汕地區達到了繁榮的高峰。這背后的成功源于多方面的推動。首先,潮汕當時經濟繁榮且社會穩定,為外江戲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加之潮州的本地戲劇相對較為落后,外江戲因此得以迅速崛起,填補了文化空白。再者,由于清代的“回避制度”[8],導致大量在潮汕的官員都來自外省。這些官員自然偏愛他們熟悉的、使用中州官話的外江戲。他們對外江戲的娛樂需求和喜愛,無疑提高了其在潮州的影響力。此外,外江戲以其儒雅細膩的風格與潮汕文人尚雅的文化審美完美契合,因此深受他們的青睞。許多文人因此紛紛組織各類社團,如外江音樂社、漢樂儒樂社等,進一步推動了外江戲在潮汕的普及和流行。可見,光緒年間,外江戲在潮汕地區已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展現,更是體現了當地士紳崇尚古典雅致品位和社會地位的象征。這種戲劇形態匯聚了那個時代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之精髓,深得坐轎、有閑的社會精英們的鐘愛,外江戲也被賦予了高雅精英文化的屬性。
進入民國時期,隨著清朝統治政權在潮汕地區的逐步崩潰,原來熱捧外江戲的外籍清廷官員相繼離開粵東。與此同時,使用當地方言的潮劇開始崛起并逐漸成形。潮劇不僅吸納了外江戲等各種藝術的精髓,更在對其藝術形式的創新中,敏銳捕捉到了時代的脈搏,滿足了潮汕觀眾的審美需求,迅速受到潮州觀眾的喜愛。另一方面,曾經盛行的外江戲,因其守舊的藝術態度和遠離革新,逐步在潮汕文化中失去影響力。為了開辟新的生存之路和藝術路徑,外江戲開始從潮汕城市向客家山區轉移。此后,外江戲班只是在每年重要的賽神活動時節,才由墟鎮趕回潮州,候場待聘[9]。這不僅是地域的轉移,更是一場深度的文化融合與轉型。外江戲與當地的民俗活動及習俗的交融,使其不再僅僅是士紳精英的藝術品位,而是滲透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與他們的傳統和文化習慣緊密相連。換言之,如果“娛樂”僅僅是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為豐富多彩以提高生活質量的話,那么,習俗的需求就不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奢侈,而是生存的必需品。
抗日戰爭爆發后,尤其在1939年潮汕淪陷后,粵東的外江戲遭遇了空前的危機,導致多數戲班解散。在這關鍵時刻,客籍藝術家羅梅波與蕭道齋站出來,分別成立了“同藝國樂社”和“新老福順班”。這兩大社團不僅傳承了廣東漢劇的演出傳統,更關鍵的是,在逆境中保全了外江戲的核心成員,為該劇種的延續提供了條件。到了1950年,基于客屬之地的這兩大戲團的底蘊,大埔與梅縣相繼成立了“大埔民聲漢劇社”與“梅縣業余漢劇研究會”,兩者逐步演變成今天的廣東漢劇院。
3 結論
綜上所述,從民國到建國期間,客家人錢熱儲將外江戲正式命名為漢劇。這一改變不僅涉及到名稱,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地理和受眾的廣泛轉型。漢劇的舞臺中心從潮汕向客家山區轉移,其主要受眾也由潮汕城市的上層精英轉為客家地區的廣大民眾。這標志著漢劇從精英文化走向了民間大眾文化,并與客家的民間文化和民俗活動緊密結合。此外,當漢劇遭遇歷史低潮,客家人以其深厚的包容性接納了這一藝術,為其提供了避風港;而當漢劇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客家人再次挺身而出,確保了其傳統得以延續。
究其背后,粵東客家族群與漢劇之間存在深刻的歷史和文化緣由。客家族群,經歷了從東晉五胡亂華到南宋末年元蒙南侵的五次大規模南遷,前后累積了近千年的漂泊與遷徙歷程。這種歷史沉淀為客家人打下了一種對故土、對歷史的深沉情感基礎。漢劇,源于中原,其使用中州官話作為戲曲語言,對于南遷的客家人來說如同鄉音般親切。這不僅喚起了他們對祖地的懷舊情懷,更與他們的審美追求——崇尚古樸與典雅的風格相呼應。漢劇的舞臺語言和審美取向與客家人的文化和審美心態產生了共鳴,為兩者之間建立起一種情感與文化的雙重連接。更進一步,漢劇為客家人提供了一種對于族群來源的追溯與情感寄托,成為了他們自我身份的重要標識。在這樣的互動中,客家人與漢劇形成了一種相互促進與成全的關系:客家人為漢劇提供了新的生命力,而漢劇則在文化上滋養了客家族群,加深了他們的自我認同。■
引用
[1] 錢熱儲.漢劇提綱[M].汕頭印務鑄字局,1933.
[2] 陳志勇.廣東漢劇研究[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
[3] 余勇.明清時期粵劇的起源、形成和發展[D].廣州:暨南大學,2006.
[4] 冼玉清.清代六省戲班在廣東[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3(3):105-120.
[5] 康保成,陳志勇.廣東漢劇與客家文化[J].學術研究,2008(2): 146-152+160.
[6] 蕭遙天.潮州戲劇音樂志[M].馬來西亞:檳城天風出版公司,1985.
[7] 蕭遙天.潮州志·戲劇音樂志[M].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
[8] 劉嘉林,何憲出.回避制度講析[M].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 1990.
[9] 謝雪影.潮梅現象[M].汕頭:汕頭市地方志辦公室資料科.民國廿四年鉛印本,1935.
本文系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藝術民俗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之子課題“口頭語言類民俗藝術研究”(22DZ06)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王子熙(1988—),男,甘肅慶陽人,博士,就職于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
通訊作者:李恩卉(1993—),女,安徽亳州人,博士,就職于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