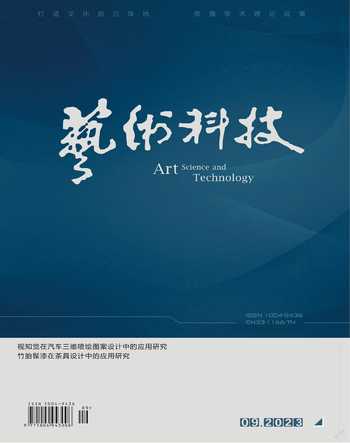論當代中國電影中的鄉(xiāng)土敘事
鄭蒙 陳巖
摘要:當代中國電影的鄉(xiāng)土敘事立足于黨的二十大背景,具有時代特色。隨著鄉(xiāng)土與鄉(xiāng)村概念的不斷具體化和分化,鄉(xiāng)土逐漸成為文化藝術的烏托邦,鄉(xiāng)土電影也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敘事傾向,進而發(fā)展延伸。早期鄉(xiāng)土電影的概念被提出之后,我國歷代電影導演將其電影敘事扎根于鄉(xiāng)土,進行深刻且具體的敘事討論和影像呈現(xiàn),從而形成了早期獨特的中國式鄉(xiāng)土影像敘事風格。隨著文化強國目標的提出,當代中國鄉(xiāng)土影像呈現(xiàn)出不同方向的敘事偏移,使得鄉(xiāng)土敘事研究有了更加豐富的時代意義。除此之外,當代導演與鄉(xiāng)土新的情感與生存關系,給予了鄉(xiāng)土敘事更大的空間。當代鄉(xiāng)土電影在人物的“神性”覺醒、生存空間的轉移和崇敬死亡的儀式表達等方面呈現(xiàn)出獨特的敘事角度和敘事內容。這種呈現(xiàn)所看重的不僅是電影故事和場景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將傳統(tǒng)鄉(xiāng)土放置在現(xiàn)代文明中反思,使當代鄉(xiāng)土敘事更具時代性和社會性。
關鍵詞:鄉(xiāng)土敘事;當代中國電影;“神性”覺醒;生存空間;生死儀式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9-00-03
1 鄉(xiāng)土與鄉(xiāng)土敘事
1.1 從鄉(xiāng)村到鄉(xiāng)土
“村”是中國歷史上家國一體的重要載體,與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唇齒相依。作為文明與文化的溫床,村落具有傳播與發(fā)展文化以及繁衍人口的功能,由此逐漸形成社會意義上的人口聚集地。這一概念在誕生之初就體現(xiàn)出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傾向性,其內在依托于地域之內的血緣關系和家長制,從而形成一種穩(wěn)固的社會單位。“鄉(xiāng)土似乎更多聯(lián)系著美好的自然風光、淳樸的民風民情;而農村則聯(lián)系著貧窮落后的社會學意義、守舊的文化以及階級斗爭和社會變革等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色彩。”[1]
鄉(xiāng)土依托于村落概念,在社會政治化和階級性中延伸出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和情感走向。鄉(xiāng)土的概念,其一指家鄉(xiāng)或故鄉(xiāng),《列子·天瑞》中“有人去鄉(xiāng)土,離六親”的“鄉(xiāng)土”指的就是家鄉(xiāng)、故鄉(xiāng);其二指地方,曹操《土不同》中“鄉(xiāng)土不同,河朔隆寒”的“鄉(xiāng)土”指地方,直接與地域特色、氣候景物相聯(lián)系[2]。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鄉(xiāng)土意識歷史悠久,以鄉(xiāng)土文化或鄉(xiāng)土精神為母體誕生了不同的藝術類別。從早期的文學到現(xiàn)代的電影,藝術家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對鄉(xiāng)土的思考和情感,同時鄉(xiāng)土也成為創(chuàng)作者們高度理想化和浪漫化的烏托邦。
1.2 延伸的鄉(xiāng)土敘事
中國早期電影的發(fā)展根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兩大電影公司(明星和聯(lián)華)對中國式生活圖景的“競爭性展現(xiàn)”,將置于時代潮流下社會底層人民對生活微末的、無效的掙扎展現(xiàn)出來,構成了中國特色的哀而不怒的電影風格。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文化強國的目標,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黨和國家立足我國強大的民族和地域文化自信提出來的。同時,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闡明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本質內涵和核心要義,這不僅打下了中華文明、中華文化自信自強的烙印,還是指導中國建設實踐的一種文明新形態(tài)[3]。新的文化要求明確了當代電影藝術的總體方向,也意味著作為最能體現(xiàn)中國社會文化的鄉(xiāng)土電影有了更新、更廣闊的話語空間。
“鄉(xiāng)土電影”這一概念最早出現(xiàn)于20世紀80年代初,劉紹棠首次提出“鄉(xiāng)土電影”后,號召電影界多創(chuàng)作具有民族風格、中國氣派、地方特色的農村題材電影[4]。20世紀80年代,以吳天明、胡柄榴等人為代表的第四代導演,創(chuàng)作了一大批描繪鄉(xiāng)土風情的電影,接壤“十七年電影”,表現(xiàn)出具有強烈矛盾感的“田園牧歌式”現(xiàn)實主義敘事風格,敘事主體在城鄉(xiāng)對立發(fā)展中發(fā)出對自身處境和時代的叩問。
此后,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在鄉(xiāng)土電影創(chuàng)作中表達了對中國不同鄉(xiāng)土地域的文化反思,呈現(xiàn)出現(xiàn)實與浪漫交織的矛盾特點。之后,被稱作第六代導演的一群青年導演創(chuàng)作了更個人化的電影作品。這一時期,他們對農村和鄉(xiāng)土的認識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割裂感和主觀性,觀眾從中認識到負面和反叛的鄉(xiāng)土文化,同時這造就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更加尖銳和叛逆的創(chuàng)作氛圍。
2 “神性”覺醒:人物的受難式悲憫
進入新時期以后,新一代導演的創(chuàng)作具有更強的自我傾向性和作者性,形成了鄉(xiāng)土電影從早期純精英式的向下俯瞰,到現(xiàn)代脫胎于泥土之中向上凝望的創(chuàng)作轉變。年輕導演對鄉(xiāng)土生活有情感的向往和個體生存上的依賴,不同于早期電影創(chuàng)作將農村當作一個文化反思和身份遺棄之地,他們更多尋找和歸置自我身份。因此,當代鄉(xiāng)土電影所呈現(xiàn)的話語人物更像一位悲憫的受難者,生于鄉(xiāng)土之中的“卑賤”群體,在苦難中被迫覺醒“神性”,固執(zhí)地以英雄主義的悲憫去接納苦難的命運,人物從客觀的消逝者變成主觀的捍衛(wèi)者,在時代逆流中完成了身份的覺醒和置換。
《平原上的夏洛克》以樸實荒誕的敘事手法塑造了特立獨行的父輩農民形象,人物設定極具包容和悲憫的“神性”品質,由此形成了一個充滿“神性”的受難式農民形象,這是具有東方傳統(tǒng)色彩的俠民的“神性壯舉”,呈現(xiàn)出大時代背景下淳樸且俠肝義膽的鄉(xiāng)土文化。超英和占義是鄉(xiāng)土空間的“神性”化身,電影給予主人公超英“俠味農民”和“土味偵探”的雙重設定。建房子是超英置身于鄉(xiāng)村土地之上作為一個農民的生存意義,查案是兩人置身于新生的城市空間中進行的“神性突圍”,這種在個體和社會關系之間實現(xiàn)的意識轉變助推了當今簡單卻又多面的鄉(xiāng)土人物形象的形成。電影將這種轉變具化為現(xiàn)實的人情往來,超英和占義在村里靠著人情關系得到了便利。進城之后,這種黏性的關系被稀釋,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獨立的利益鏈條。兩人作為城市的外來者無法共享利益鏈條,人物的“福爾摩斯”“華生”身份無法確立,也就喪失了話語權。這是一種“神性”的偏向與磨損,在以兩人為一個單位的共同體話語里,導演極力呈現(xiàn)的是隱藏在超英和占義背后豐滿的生命形象,由此在現(xiàn)代化的文化荒地之中,發(fā)出對鄉(xiāng)土農耕文明由衷的禮贊。
《北方一片蒼茫》則以一種更加魔幻荒誕的方式讓主角作為“半神”執(zhí)行正義,王二好經歷了“人—神—鬼”的角色轉換。作為“人”時被驅逐和欺辱,此后,她被迫覺醒成為“神”,在神賦予她的權力場中成為規(guī)則的制定者和文化的捍衛(wèi)者。王二好妄圖在這種關系里矯正扭曲的人性,獲得救贖。但“神”無法拯救“人”,她只能“死”在自己信徒的手里變成“鬼”。這種單一關系里的角色,是當代鄉(xiāng)土電影中被重新確立的身份主體。他們誕生在鄉(xiāng)土之中,在經歷過苦難后,經營著自己重新覺醒的身份,掙扎求得生存,從而在前現(xiàn)代或現(xiàn)代性的社會之中以“神性”的俯瞰完成對人性的拷問。
3 權力的崩壞:生存空間的轉移
“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談論了鄉(xiāng)土的權力種類,他認為封閉的鄉(xiāng)土社會中權力曾主導著鄉(xiāng)土的變遷:一是從社會沖突中所發(fā)生的橫暴權力,二是從社會合作中所發(fā)生的同意權力,三是從社會繼替中所發(fā)生的長老權力。”[5]這里所說的“長老權力”即傳統(tǒng)部族中教化性的大家長權力——父權/母權。在現(xiàn)代文明社會成型以前,主導村落和土地的是被賦予權力的人,這種權力模式被現(xiàn)代秩序排斥,導致封閉的鄉(xiāng)土文化分崩離析,原住居民被迫轉移自己的生存空間,因此當代電影面臨的鄉(xiāng)土是一個失序和缺失的世界。這種缺失通過影像傳達出來,構成了當代鄉(xiāng)土電影獨特的敘事風格和表現(xiàn)特色。
《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以一個即將在草原上消失的民族——裕固族為表現(xiàn)對象,通過一種冷靜疏離的方式實現(xiàn)對鄉(xiāng)土文明的持續(xù)關注。這種關注是極具現(xiàn)實性和隱喻性的,傳統(tǒng)的家庭結構在影片中從未顯現(xiàn),取而代之的是父權的衰微和母位的缺失。過去單一的權力支配結構被打破,靜止在土地上的人被迫出走,踏上尋找母親的道路,在找尋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早已妥協(xié)的父親。塵土飛揚的淘金之地,阿迪克爾眼中代表著草原和鄉(xiāng)土精神的父親形象不可挽回地走向崩塌,他從而逐漸意識到傳統(tǒng)家園消逝的不可逆性。這種大家長式單一權力形象的崩壞所折射的是傳統(tǒng)鄉(xiāng)土模式的解體,父親或者母親的形象是具有關照意味的傳統(tǒng)話語象征,他們所代表的權力是相對現(xiàn)代力量的一種主體地位的消退,現(xiàn)代體驗的主體在失去庇護的同時被迫流浪。
除了父母形象的隱喻,族長或村長是傳統(tǒng)話語結構中最有力量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引導著鄉(xiāng)村宗法倫理的發(fā)展和建設。當代鄉(xiāng)土電影中,這一身份權力始終游離在鄉(xiāng)土和城市之間,無法作為繼承者保護鄉(xiāng)土,轉而成為時代的“幫兇”,成為現(xiàn)代文明吞噬鄉(xiāng)土文化的管道。《北方一片蒼茫》中的村長不顧王二好的勸阻,帶領村民開采礦山,一盆“百家尿”趕走了阻攔的“神靈”,將王二好逼到絕境,其自身也被困在礦山之下,走向死路。《一個勺子》中的村長無視村民的請求,無助的拉條子被迫成為西北荒原上流浪的“失根者”,變成眾人口中的“一個勺子”。《hello,樹先生》中的樹被剝奪欺壓,失去生存的依仗,最終走失在蒼茫的雪地里。在這些影片中,傳統(tǒng)意義上家長式的人物沒能成為庇護者,反而成為鄉(xiāng)土生活的破壞者和精神的施暴者。這在一定意義上折射出鄉(xiāng)土權力結構的崩壞,在外來權力侵入和本土權力崩壞的情況下,原住居民被迫迷失或轉移,放棄肉體的成為“王二好”,只留存肉體游蕩的成為“樹先生”。
4 文化逆行:崇敬死亡的儀式表達
當代鄉(xiāng)土電影所折射的傳統(tǒng)文化具有一定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隱含著鄉(xiāng)土社會幾百年來對生命不同層次的認知和崇拜。這種崇拜轉化為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里的基礎欲望和訴求——生和死。生死的儀式性歷來被中國人重視,這種儀式性構成了中國鄉(xiāng)村特有的文化景觀,它充斥在中國鄉(xiāng)村幾千年來的文化脈絡中,逐漸演變成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話語體系。這種特殊的情結隨著時代和環(huán)境的變遷逐漸被淡化,當代年輕人強力的時代黏性和淡漠的生死觀都使這種老式的生死儀式逐漸被簡化,甚至被省略,無法隨時代前進的老一輩則陷入無力、荒涼的境地。
《清水里的刀子》以一種非常現(xiàn)實、冷靜的手法展現(xiàn)了一個回族老人面對生死抉擇時的細膩感受。影片以低反差的視覺效果,展現(xiàn)了宗教儀式般的畫面,從孩子的出生到老牛的死亡,無不表現(xiàn)出人類對生死充滿憂思且敬畏的復雜感受。“我們還不如一個牛,牛知道它的死,我們作為人卻不能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牛同時擁有人和神的意志,在預知了自己的死亡之后,它坦然接受了即將到來的命運。老人卻無法面對即將死亡的牛,因為他無法在族群和生命倫理之間作出一個合理的選擇,只能被動承受痛苦。作為宗教信徒的老人置身于“向死而生”的處境,因而認可搭救亡人的儀式。在這種儀式中,死去的魂靈可以擺脫塵世的污濁和罪惡,得到應有的歸宿,被神化的信仰賦予了儀式超越生死的意義和價值。
《喜喪》以更加真實殘酷的敘事手法討論了人的衰老和死亡,導演力圖在虛浮殘碎的表象下挖掘更深層次的東西,衰老仿佛成了原罪,腐朽的身體終究變成苦難。老人到了年紀還活著是一件茍且的事,因此死亡被賦予光榮的意味,死亡的儀式被認為是“喜事”。影片結尾沒有悲痛的哭喪儀式,取而代之的是充滿現(xiàn)代性的歌舞表演,喜喪背后支撐的是子女稱作“面子”的東西,這是民族在演化了千百年后深深扎根于普通百姓頭腦中得以衍生之物的集中概括,也是現(xiàn)代視角下死亡的最終歸宿。
在《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中,死亡的儀式性得到了進一步展現(xiàn),“人死為重,死者為大,入土為安”,不能入土對老人來說是一件遠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老馬迫切地想隨鶴而去,入土為安,追尋完成一種他認可的死亡儀式。這是老馬對現(xiàn)實的逃避和迫切想返回過去的欲望,是一種超越了當下社會文化的“非理智追尋”,這種尋求被子女漠視乃至摧毀,從而使得電影具備深刻的跨時代人文性。電影強化了老人對死亡儀式的執(zhí)拗追尋,形象表征了個體生命形態(tài)和社會進程的錯位和對立,影像敘事中夾雜著導演對此類命題和社會現(xiàn)象的象征性體驗與反思。
5 結語
當代中國鄉(xiāng)土電影中的敘事呈現(xiàn)出更貼近時代精神的特點。在新的環(huán)境下,鄉(xiāng)土電影中的人物、景觀及文化有了更廣闊的表現(xiàn)空間。充滿現(xiàn)代性神話色彩的《長江圖》,以當代人類想象完成了一場浪漫的文化尋根;探討城鄉(xiāng)關系的《撥浪鼓咚咚響》,以公路電影的外殼展現(xiàn)了失獨父親和留守兒童的鄉(xiāng)土故事,構建了現(xiàn)代視域下西北黃土地上人們的生存群像。長期以來,鄉(xiāng)土電影所展現(xiàn)的農村景觀和農民形象都被看作國家文化的符碼,因此對鄉(xiāng)土電影的研究具有時代價值,其是最能展現(xiàn)時代特征和社會標識的藝術形式。
參考文獻:
[1] 凌燕.回望百年鄉(xiāng)村鏡像[J].電影藝術,2005(2):87-92.
[2] 程歗.晚清鄉(xiāng)土意識[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98.
[3] 祁吟墨.以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學習貫徹二十大精神 文化建設專題理論研討會”綜述[J].圖書館論壇,2022,42(11):1-7.
[4] 李煥征.新時期鄉(xiāng)土電影的概念與話語修辭[J].藝術百家,2019,35(3):122-129.
[5] 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7.
作者簡介:鄭蒙(1999—),女,山東單縣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電影敘事、電影美學。
陳巖(1979—),男,江蘇徐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電影美學、電影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