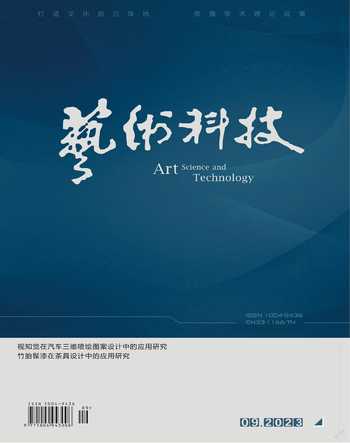新世紀(jì)紅色電影的敘事空間與價(jià)值表達(dá)研究
李紅坦 張?jiān)?/p>
摘要:紅色電影是宣揚(yáng)和繼承紅色文化和紅色精神的有力載體,是主流文化建設(shè)中不可或缺的傳播介質(zhì)。紅色電影擁有獨(dú)特的文本優(yōu)勢,具備穩(wěn)定的政治價(jià)值和文化價(jià)值,凝聚著偉大的革命精神和先進(jìn)思想,長期為社會(huì)輸出主流價(jià)值觀,為社會(huì)大眾樹立先進(jìn)思想標(biāo)桿。作為思想政治建設(shè)與文化建設(shè)的主要媒介,紅色電影的精神內(nèi)涵是隨時(shí)代進(jìn)步的,紅色電影的思想導(dǎo)向功能是不容破壞的。步入新世紀(jì)以后,全新的時(shí)代賦予了紅色電影全新的創(chuàng)作靈感和表達(dá)思路,紅色電影不再拘泥于重大革命題材與傳統(tǒng)敘事思路,在兼顧作品藝術(shù)性的同時(shí),產(chǎn)出了一系列易于被觀眾接受的富有感染力的紅色作品,在主題和敘事上呈現(xiàn)出多元的創(chuàng)作手法,逐漸從情感入手,以受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展開敘事,以藝術(shù)感染代替?zhèn)鹘y(tǒng)說教,以作品魅力傳遞價(jià)值觀念,抒發(fā)家國情懷,致敬時(shí)代英雄,在滿足觀眾審美傾向和情感需求的基礎(chǔ)上,乘時(shí)代之東風(fēng),完成紅色價(jià)值觀念的有效輸出。文章通過類型界定,分析紅色電影自身文本空間的表達(dá)功能,從視聽語言與意境空間、形象設(shè)定與人物空間、開放理念與異域空間的融合和轉(zhuǎn)向等角度出發(fā),審視新世紀(jì)紅色電影獨(dú)特的敘事藝術(shù)和價(jià)值傳遞,從中研究新世紀(jì)紅色電影的發(fā)展前景與活力源泉。
關(guān)鍵詞:紅色電影;敘事空間;價(jià)值傳遞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9-0-03
0 引言
作為構(gòu)建紅色文化話語的重要力量,自20世紀(jì)誕生伊始,“紅色電影”這一概念就具備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訴求和獨(dú)特的文化性格,承擔(dān)著傳遞時(shí)代價(jià)值的重要任務(wù)。正因如此,紅色電影應(yīng)成為一個(gè)與時(shí)俱進(jìn)的概念。進(jìn)入新世紀(jì),伴隨著電影技術(shù)的逐漸成熟與大眾審美需求的顯著提升,紅色電影開始不斷革新敘事策略,優(yōu)化敘事角度、意境表達(dá)以及價(jià)值傳遞,力圖在新世紀(jì)展現(xiàn)新的生機(jī)與活力。
1 意境構(gòu)筑:建筑空間與音樂語言
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xué)中的特殊范疇和中心范疇,對意境的研究和概述貫穿于中國藝術(shù)的進(jìn)程之中,在豐富作品本身結(jié)構(gòu)和層次的功能上有“更上一層樓”的效果。電影本身雖然區(qū)別于文學(xué)、繪畫等傳統(tǒng)概念上與意境綁定的藝術(shù),但同樣具有對意境空間的追求,這樣的追求輻射到新世紀(jì)紅色電影的敘事上時(shí),視聽語言就成為重要的表達(dá)通道。
1.1 建筑空間的意識表達(dá)
建筑作為電影文本中的“第二表達(dá)”,在電影的意境構(gòu)筑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實(shí)體的建筑作為一種電影語言出現(xiàn)在熒幕上時(shí),就脫離了其本身的物質(zhì)功能,擔(dān)任作品的意象構(gòu)建功能,承載作品所表達(dá)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成為具有生命意義的存在。在電影作品中,某種風(fēng)格、某種類型的建筑通常會(huì)成為特定的空間符號,參與電影意境的生成。
建筑是非自然的符號,是人的意志的外化表現(xiàn),是文化的產(chǎn)物。建筑既能承載記憶,也能傳遞記憶,尤其是標(biāo)志性的建筑,所展示的強(qiáng)大記憶能量是不容忽視的。紅色電影是講好中國故事、展示中國形象、傳播中國文化與精神的重要載體[1]。
在電影《建國大業(yè)》中,承載著中國人民偉大信仰的天安門廣場就是標(biāo)志性的紅色建筑。作為展現(xiàn)紅色文化最典型的建筑,天安門所蘊(yùn)含的政治意味和歷史象征使其可以最直接地將每一個(gè)觀眾對革命意義、家國情懷、民族自豪的感動(dòng)和震撼調(diào)動(dòng)起來,從而構(gòu)建出聯(lián)系家國命運(yùn)的空間,觸動(dòng)觀眾的心靈,喚起屬于中國人的紅色情感。
1.2 電影配樂的氛圍營造
電影音樂可以為電影營造出特定的氛圍,以深化視覺效果。在發(fā)揮這項(xiàng)功能時(shí),音樂并不帶有主觀的引導(dǎo)和評價(jià),也并非單一解釋某部分文本,而是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完整的、動(dòng)人的意境空間,輔助受眾感受抽象的作品情感,從而使故事內(nèi)容深入受眾心中。
電影和音樂并不是天然的綁定關(guān)系,電影走過默片時(shí)代后,音樂才逐漸開始作為靈魂元素與電影共存共生。作為聽覺藝術(shù),音樂是最能表現(xiàn)情緒的載體。就本質(zhì)來講,音樂能夠在有機(jī)的結(jié)構(gòu)創(chuàng)意之下參與到電影情節(jié)中,對電影整體基調(diào)的奠定和風(fēng)格的把握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電影與音樂的配合煥發(fā)出的能量,能給民眾帶來獨(dú)特的情感體驗(yàn)和價(jià)值熏陶,為踐行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觀提供助力[2]。
在電影《1912》中,青年毛澤東在上海街頭奔跑,背后是法國慶祝國慶煙花飛揚(yáng)的法租界,落寞中激蕩起無窮的信念,音樂的旋律由低沉轉(zhuǎn)向高昂,和大步奔跑的人物完美契合,畫面與音樂相互成就。在這個(gè)過程中,電影中的音樂不但承擔(dān)了渲染氣氛、烘托人物的功能,還進(jìn)一步豐富了作品敘事,拓展了畫面空間。
意境是中國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重要美學(xué)傳統(tǒng)[3],視覺畫面提供了看得見的實(shí)景,音樂創(chuàng)造了超越本身旋律意義和電影物理空間的情感的虛境,虛與實(shí)的結(jié)合統(tǒng)一,使人物形象和聯(lián)想空間更加立體,表現(xiàn)出音樂在電影作品中發(fā)揮出的獨(dú)特的意境建構(gòu)功能。新世紀(jì)紅色電影在敘事中對建筑和音樂的把握,有利于為觀眾營造感性的意境審美空間,在這樣的意境中,與劇中人物同呼吸、共命運(yùn),最終實(shí)現(xiàn)理性的升華。
2 故事安排:崇高格調(diào)與平凡人物
講好故事,塑造好人物,是電影文本表述須考慮的核心要?jiǎng)?wù)。紅色電影是以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歷程中真實(shí)的革命事跡和英雄人物為內(nèi)容所創(chuàng)作的電影類型,有真實(shí)的歷史背景和特殊的歷史記憶作為基礎(chǔ),借助熒幕呈現(xiàn)給觀眾。進(jìn)入新世紀(jì),紅色電影在以革命史詩為題材的基礎(chǔ)上,將人物的設(shè)定逐漸向平民化、人性化靠攏,拉近觀眾與人物的距離,引發(fā)觀眾共鳴。
2.1 以崇高格調(diào)演繹史詩
在歷史時(shí)空中,紅色故事的再現(xiàn)是深化受眾體驗(yàn)最常見也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再現(xiàn)的過程中,電影藝術(shù)作品所蘊(yùn)含的精神文化將潛移默化地影響受眾的思想,由此產(chǎn)生的場域觀感也會(huì)逐漸自內(nèi)而外地影響受眾的認(rèn)知和行動(dòng)。紅色電影的發(fā)展植根于特定的社會(huì)文化發(fā)展進(jìn)程及其訴求,格調(diào)昂揚(yáng),充滿了精神光輝,在消費(fèi)文化盛行的今天,從過度追求利益、迎合低級趣味的商業(yè)電影中脫穎而出,在堅(jiān)守崇高史詩敘事的同時(shí),照顧到電影本身的可觀賞性,平衡了娛樂和格調(diào)的雙重空間,實(shí)現(xiàn)了內(nèi)容質(zhì)量與商業(yè)影響的良性互動(dòng),并且從精神上帶給社會(huì)群體現(xiàn)實(shí)的理想信念。
革命的信念和戰(zhàn)爭的殘酷記憶流淌在每一個(gè)中國人的骨血中。《長津湖》作為我國目前公開上映的第一部采用文獻(xiàn)記錄式的抗美援朝戰(zhàn)爭電影,將宏大主線與微觀敘事完美結(jié)合,用全景拍攝的手法構(gòu)建出完整的環(huán)境空間,炮火連天的戰(zhàn)場、狂轟濫炸的敵機(jī)和凍成冰雕的志愿軍戰(zhàn)士,單薄的棉衣與裝備精良的敵人之間的對比,都能夠最直觀地喚醒觀眾對歷史的共同記憶。以史詩為背景的崇高敘事能夠讓觀眾通過觀看那段艱苦且充滿犧牲的歲月,體會(huì)到信仰的巨大力量,從而傳承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紅色文化精神,高揚(yáng)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懷。
2.2 以微小視角創(chuàng)作人物
紅色類型的影視在發(fā)展初期,致力于打造神化的完美主角,以此為模板產(chǎn)出的部分作品在今天不時(shí)被冠以“神劇”的稱謂,受到嘲諷。人物是故事發(fā)展的核心,人物形象的刻畫決定了故事的展開和格局。新世紀(jì),紅色電影在對人物進(jìn)行創(chuàng)作表達(dá)時(shí),立足于當(dāng)今受眾的審美觀,將切入點(diǎn)放在日常的事件中,讓人物敘事向生活化的表達(dá)靠攏,減輕過分追求偉岸人設(shè)而造成的不真實(shí)和距離感,弱化肅穆單一的人物形象,以貼近生活的細(xì)節(jié)表現(xiàn)出角色的平凡人性。
《長津湖》中作為電影線索之一的伍家三兄弟的感情線、《八佰》中害怕槍炮聲甚至一開始想逃跑的戰(zhàn)士端午、《金陵十三釵》中對出身煙花的十三釵避之不及的女學(xué)生,這些設(shè)定都反映出最真實(shí)最平凡的人物所具有的特點(diǎn),角色的人設(shè)越貼近煙火里的生活,越能夠與受眾產(chǎn)生聯(lián)結(jié)。
進(jìn)入21世紀(jì),審美經(jīng)驗(yàn)的累積使觀眾擁有更加挑剔的眼光和更加淡泊的情感。情感是人類最基本的心理活動(dòng),是人類對客觀事物是否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產(chǎn)生的體驗(yàn)。以平凡的視點(diǎn)展開故事敘述,以父親、丈夫等日常的身份和觀眾建立共鳴,構(gòu)筑充沛的情感空間,能夠更深入地將紅色價(jià)值觀扎根于觀眾心底。
3 形式包容:異域空間與開放理念
紅色電影始終堅(jiān)持在每個(gè)年代都緊貼社會(huì)主題。革命年代,紅色電影反映了人民對和平美好的向往與期待;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時(shí)期,正向的國際交往始步,紅色電影展現(xiàn)出更加豐富的內(nèi)容;改革開放以后,紅色電影的素材更加豐富,開始嘗試以不同類型的劇情述說主題;進(jìn)入新世紀(jì),國家實(shí)力和國際地位空前提升,影視媒體業(yè)態(tài)也在不斷進(jìn)步,新的時(shí)代賦予電影藝術(shù)更多的發(fā)展機(jī)會(huì)。
科技和時(shí)代的進(jìn)步加速了受眾價(jià)值觀的轉(zhuǎn)變,時(shí)代主題更新,時(shí)代語境變遷,紅色電影要以更新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受眾面前,在堅(jiān)持紅色電影一貫紅色作風(fēng)的基礎(chǔ)上,以家國精神為內(nèi)核,引入更多時(shí)代性元素,為新世紀(jì)中國的精神文化建設(shè)提供動(dòng)力。
3.1 國家想象的更新豐富
傳統(tǒng)紅色電影在選取題材時(shí),常采用經(jīng)典的革命事跡作為背景,這樣有利于增強(qiáng)劇本本身的完整性和調(diào)性。然而對于觀眾來說,觀影預(yù)備期間的心理期待基本可以透視整部電影的劇情,套路化的劇本和程序化的思想升華在如今的時(shí)代背景下不免有消費(fèi)愛國情感的嫌疑,過度的重復(fù)是對情感最大的消耗,會(huì)影響觀眾的觀影感受。紅色電影作為文化的承載體,也是塑造國家形象和提升文化軟實(shí)力的重要手段[4]。
新世紀(jì)的紅色電影選取跨國題材作為劇本,在敘事中打造一個(gè)陌生的空間,將故事放在遙遠(yuǎn)的陌生國度,由此形成的異域空間可以用尖銳的矛盾和危險(xiǎn)的沖突將觀眾帶入其中,與影片中的人物產(chǎn)生情感聯(lián)結(jié)。受眾是真實(shí)生活在新世紀(jì)的人民大眾,電影表述的是當(dāng)前時(shí)代祖國對人民大眾真切的維護(hù),更容易引發(fā)受眾強(qiáng)烈的共鳴。
以也門撤僑事件為背景拍攝的《紅海行動(dòng)》、以中國船員遇害事件為背景拍攝的《湄公河行動(dòng)》以及以中國外交真實(shí)撤僑事件為背景拍攝的《萬里歸途》,都是將異域空間作為電影主要敘事手段的代表作品。電影中軍隊(duì)、外交官、國旗成為異域空間特殊的符號,他們代表著國家的力量,代表著傳承紅色精神的中國永遠(yuǎn)竭力守護(hù)每一個(gè)中國人的和平生活。這些鮮明的國家符號將個(gè)人命運(yùn)與國家命運(yùn)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激起受眾的民族認(rèn)同感和家國自豪感。
3.2 電影理念的開放發(fā)展
開放包容一直是文化發(fā)展最顯著的主題。進(jìn)入21世紀(jì),審美包容度提升,審美需求更加多樣化,國際交流更加密切。為適應(yīng)時(shí)代的更新與發(fā)展,紅色電影在理念上顯示出更加包容的姿態(tài)。
新世紀(jì)包容的風(fēng)格拓寬了紅色電影的發(fā)展道路,不同題材、不同視角的影片走上熒幕,重構(gòu)了受眾心中對經(jīng)典紅色電影的視野期待。在對外的交流借鑒中,新世紀(jì)的紅色電影也表現(xiàn)出積極的態(tài)度,不斷吸納西方電影理念中可以適用的元素和電影制作方面先進(jìn)的技術(shù),在學(xué)習(xí)與交流的同時(shí)打開紅色電影的國際市場,將紅色電影推向世界。
新世紀(jì)的紅色電影在開放理念的同時(shí),兼顧了題材本身的格調(diào),避免了過度消費(fèi)經(jīng)典革命題材所造成的低俗化,在商業(yè)性與思想價(jià)值之間達(dá)到了巧妙的平衡,從文化關(guān)系、社會(huì)背景和地位利益三方面貼近了今天的主流觀眾[5]。無論是將故事放在異國他鄉(xiāng),還是對影片類型和視角進(jìn)行全新打磨的嘗試,都使觀眾“重新調(diào)整心理定式,以一種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對象的生動(dòng)性和豐富性”[6],體現(xiàn)出紅色電影愈加開放和包容的理念。將紅色電影推向更加廣闊的舞臺,不僅能夠重構(gòu)觀眾對國家的形象想象與身份認(rèn)同,而且能夠促進(jìn)紅色文化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輸出。
4 結(jié)語
電影作為重要的大眾媒介,具備重要的傳播功能,既肩負(fù)著對抗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嚴(yán)重影響和商業(yè)化大潮的沖擊的責(zé)任,又要負(fù)責(zé)建立和引導(dǎo)社會(huì)整體價(jià)值觀念。紅色電影特殊的主題使其更應(yīng)擔(dān)負(fù)起意識傳達(dá)的功能,在處理電影元素時(shí),也就更容易將文本空間作為傳播紅色精神、紅色思想的通道。
進(jìn)入新世紀(jì),紅色電影在創(chuàng)作上進(jìn)行了諸多嘗試和創(chuàng)新,從不同角度研究和展現(xiàn)紅色故事的熒幕表達(dá),一定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社會(huì)主流價(jià)值觀的良性傳播和社會(huì)群體的積極引導(dǎo)。紅色電影的發(fā)展前路是被寄予厚望的,創(chuàng)作前路是任重而道遠(yuǎn)的。新世紀(jì)的紅色電影作品融合了革命精神和家國敘事,為當(dāng)代中國大眾提供了強(qiáng)大的精神信念和優(yōu)秀的精神養(yǎng)分。紅色電影理應(yīng)更加不忘使命,講好紅色故事,傳揚(yáng)紅色文化。
參考文獻(xiàn):
[1] 彭濤,陳月異.新時(shí)代現(xiàn)象級新主流電影的敘事策略與審美傾向[J].四川戲劇,2022(10):127-132.
[2] 梁文珊.文化強(qiáng)國背景下紅色電影音樂的時(shí)代價(jià)值及有效實(shí)踐[J].棗莊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40(1):106-111.
[3] 毛霞,甘慶超.意境與中國電影[J].電影文學(xué),2021(4):31-34.
[4] 張斌.空間跨越與主流電影重構(gòu):論《紅海行動(dòng)》的三重創(chuàng)新[J].藝術(shù)評論,2018(5):69-76.
[5] 彭濤,劉逸飛.父與子的擁抱:新主流電影建構(gòu)情感認(rèn)同的敘事路徑[J].電影文學(xué),2022(18):79-85.
[6] 趙一凡,張中載,李德恩.西方文論關(guān)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6:342.
作者簡介:李紅坦(1980—),男,河南新鄭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紅色文藝專題、思政教育、民族史學(xué)與社會(huì)史學(xué)。
張?jiān)?999—),女,河南南陽人,碩士在讀,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紅色文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