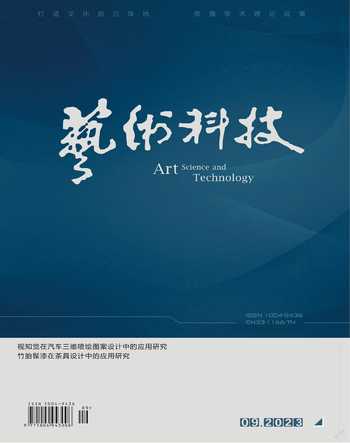新媒體視域下河南形象的建構(gòu)與傳播研究
摘要:城市形象是一個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要素的具象化體現(xiàn)。作為公眾認(rèn)知的“窗口”,媒介的持續(xù)變革為城市形象的重新書寫提供了可能。新媒體環(huán)境下,“只有河南·戲劇幻城”立足于本土文化和區(qū)域特點,分別從內(nèi)部價值取向和外部操作形態(tài)兩個方面展開對河南形象的建構(gòu)與傳播。從內(nèi)部實踐來看,其致力于對傳統(tǒng)文化心理和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度挖掘,在講好河南故事的同時,以平民化的視角和多模態(tài)的組合方式將受眾納入主體間的傳播關(guān)系,增強(qiáng)了受眾的文化認(rèn)同感和身份歸屬感,進(jìn)而為河南形象的有效傳播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chǔ);從外部操作來看,其突破了以往單向度、機(jī)械化的傳播方式,在融合多種媒介形態(tài)的情況下,形成了以受眾為中心的多元輻射格局,從而實現(xiàn)了傳播渠道和傳播方式的變革。與此同時,還依靠技術(shù)賦能,在精準(zhǔn)定位受眾群體的基礎(chǔ)上,借由影像化的呈現(xiàn)方式和沉浸式的場景營造,聯(lián)通了人的全部感覺器官,這不僅使受眾的心理認(rèn)知和審美體驗上升到更高層次的目標(biāo)領(lǐng)域,更因其特有的傳播形式而為新時代河南形象工程建設(shè)注入了新的內(nèi)容與活力。可以說,正是基于媒介自身和媒介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改變,才使河南形象的發(fā)展擁有了更廣泛的意義空間和更高的價值。文章基于新媒體視角,對河南形象的建構(gòu)與傳播進(jìn)行探究,以供參考。
關(guān)鍵詞:河南形象;中原文化;媒介傳播;只有河南·戲劇幻城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9-0-04
河南作為華夏文明的發(fā)祥地,比其他地區(qū)更早進(jìn)入了文明時代,無論是始祖伏羲、河圖洛書等神話傳說,還是裴李崗、仰韶等史前文化,大多肇始于此。然而,與其優(yōu)秀文化基因不同的是,河南的城市形象日漸低迷,資源優(yōu)勢并沒有完全轉(zhuǎn)化為形象優(yōu)勢,存在歧視和偏見。如明代王守仁所言,“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rèn)定以為道止如此”[1],刻板印象已成為河南形象發(fā)展的桎梏。在美國學(xué)者李普曼的研究中,特別強(qiáng)調(diào)了大眾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在他看來,大眾媒介不僅是“擬態(tài)環(huán)境”的主要營造者,還是社會刻板印象的生成者和維護(hù)者。基于此,在媒介深度變革的背景下,本文以“只有河南·戲劇幻城”為研究樣本,通過對其傳播內(nèi)容和傳播模式的具體分析,探討在新媒體視域下如何把握河南形象的建構(gòu)與傳播。
1 打造傳統(tǒng)文化符號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融媒體時代,城市形象傳播的基底在于文化。錢穆先生提到,“除卻歷史,無從談起文化”。自“禹別九州”始,豫州“閫域中夏,道里輻輳”[2]的地位就被確立下來。今言河南者,大抵為古之豫州之地。時至唐宋,河南一直都是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中心,以至于漢人司馬光都發(fā)出“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的感慨。由此可見,將河南視為中國歷史文化的縮影絕非空談。
1.1 發(fā)展“拳頭”產(chǎn)品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yuǎn)者,必浚其泉源。”[3]尋根敬祖是人之天性,唯有“根”才是集束河南優(yōu)勢的強(qiáng)大力量。早在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河南就曾以“根”文化作為“拳頭”產(chǎn)品,但由于在市場開發(fā)和宣傳造勢上過于注重“內(nèi)銷”,所以在引流過程中顯示出疲態(tài),直接影響了河南整體形象的優(yōu)化與升級。
如今,“只有河南·戲劇幻城”(以下簡稱“幻城”)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優(yōu)勢,打破由地域構(gòu)成的文化圈層,讓更多的人擁有了接觸河南宏大歷史的可能。從內(nèi)容上看,“幻城”以“尋根”為切口,在繪畫、詩歌、禮樂、建筑、農(nóng)耕等諸多方面宣傳造勢,彰顯了河南作為“中華文明之源”的優(yōu)勢和氣度。無論是傳統(tǒng)穴居“地坑院”,還是傳世名畫《清明上河圖》,抑或是地有確跡的“天子駕六”,都是華夏文明在此誕生的印證。借中原傳統(tǒng)文化這一母題宣傳河南形象,能夠讓受眾切身領(lǐng)悟河南作為中華文明發(fā)源地的文化厚重感,這是一條將文化資源優(yōu)勢轉(zhuǎn)變?yōu)樯虡I(yè)競爭優(yōu)勢的可行之路。
1.2 講好河南故事
“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故事作為一種意符,承載的是一個城市的精神面貌。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社交媒體時代,相較于“冰冷”的理論說教,“有溫度”的情感故事更有利于城市形象的傳播。揚·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指出,每一個文化體系內(nèi)部都存在一種“凝聚性結(jié)構(gòu)”[4],處于共同體中的成員可以借由這一結(jié)構(gòu)所蘊含的共同經(jīng)驗記憶和象征性意義體系,實現(xiàn)對群體身份的認(rèn)同。
“幻城”深度挖掘本土故事資源,通過對具有強(qiáng)烈情感價值的本土故事的精耕細(xì)作,引起受眾個人情感與集體記憶的共鳴。“通天的大路朝西南,路上的白饃吃不完”,這是河南的苦,也是河南的怨。在《李家村劇場》中,演員們用情緒及詩性的演繹將觀眾帶回到1942年的那場浩劫,身臨其境地感受一個村莊的血脈傳承及河南作為糧食大國的使命。在傳播過程中,那些似乎具有更持久意義的元素被固定下來并被賦予了現(xiàn)實意義,從而使被記起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都能在與之相關(guān)的敘事中找到適合它們的位置。正是源于故事所承載的共同的情感價值,才使河南形象的建構(gòu)不僅具有文化傳播的意義,更具有凝聚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時代意義[5]。
2 創(chuàng)新敘事模式,重塑河南文化形象
2.1 平民化的敘事視角
敘事理論有兩個核心,一是故事,二是話語。前者是敘事的內(nèi)容,后者是敘事的視角。聚焦于故事背后的敘事視角,更多是基于平民化的微觀視角進(jìn)行敘事,只有這樣才能使傳播過程變得既有溫度、又接地氣。平民化的視角往往以情感為基調(diào),以生活化的場景為內(nèi)容,同時在傳受關(guān)系和表現(xiàn)形式上更加貼近生活,有助于在吸引受眾視線的同時,讓經(jīng)典借此“飛入尋常百姓家”。
為了契合當(dāng)下受眾的接受語境,“幻城”一改嚴(yán)肅、宏大的敘事風(fēng)格,將視點集中于普通受眾的審美體驗,將中原文化、中原故事、中原精神從原本狹隘的精英體系中剝離出來,激發(fā)受眾全身心參與互動的熱情,由此構(gòu)建起新的“走進(jìn)日常生活、引導(dǎo)生活方式、體現(xiàn)生活價值”的城市文化形象。這種通過匯集大眾個人印跡塑造出來的城市形象,繞開了存在和表現(xiàn)的對立面,創(chuàng)造了一種與現(xiàn)實世界相聯(lián)結(jié)的更接地氣的新型關(guān)系。
2.2 多模態(tài)的敘事文本
隨著數(shù)字媒體的迅速更迭和演進(jìn),新的多模態(tài)敘事興起。多模態(tài)本質(zhì)上是一種跨域映射,具體而言,就是圖像、語言、聲音、動作等多種符號資源共現(xiàn)于同一語境的話語中,共同生成意義的表達(dá)形式[6]。“幻城”以在不同時空條件下講好河南故事為目標(biāo),借助舞臺、文字、音樂、舞蹈、戲劇、詩詞經(jīng)典等多模態(tài)媒介,先訴諸觀眾的視覺、聽覺和觸覺,進(jìn)而延展到無限的意義空間。以《天子駕六遺址坑》為例,在借鑒多模態(tài)話語理論框架的基礎(chǔ)上,該劇場通過古今人物對話、舞臺布置及背景音樂等多個符號系統(tǒng)間交際關(guān)系的營造,使原本在大眾眼里有距離感的經(jīng)典文本得以“發(fā)聲”,從而實現(xiàn)“豈不以命護(hù)書”的價值追求。
2.3 編碼化的符號信息
魯迅先生評價《紅樓夢》時曾說:“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jīng)學(xué)家看見《易》,道學(xué)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7]按照霍爾的編碼理論,編碼即根據(jù)一定的社會秩序,利用符碼生產(chǎn)信息的過程,但在實際的傳播中,由于不同受眾的生活經(jīng)驗和文化背景有所不同,所以在意義結(jié)構(gòu)的解讀中存在多種可能,其結(jié)果不具備統(tǒng)一性[8]。
就“幻城”而言,編碼就是將地方資源轉(zhuǎn)換成可供傳播的藝術(shù)符號的過程。編碼者會基于自身的知識結(jié)構(gòu)、生活經(jīng)驗以及受眾的需求進(jìn)行符碼信息的生產(chǎn)。“幻城”的總導(dǎo)演王潮歌基于時代和市場需要,選取了有代表性的河南資源,通過對其進(jìn)行深刻解讀及藝術(shù)創(chuàng)造,打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優(yōu)秀劇本。在選角上,為了更真實地展現(xiàn)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幻城”大量選擇非專業(yè)的本地人參與演出,他們借助圖像、肢體、聲音等表象符號向受眾傳遞了河南的精神氣質(zhì)與文化內(nèi)涵,實現(xiàn)了以相互關(guān)注和情感連帶為核心的互動儀式鏈。
3 加強(qiáng)話語體系建設(shè),增加傳播可能
法國媒介學(xué)家雷吉斯·德布雷曾說:“如果要傳承的話,首先必須傳播。”[9]近幾年,以“唐宮夜宴”“老家河南”“中國節(jié)日”為代表的系列熱點,激活了沉寂已久的河南文化。在新媒體技術(shù)的加持下,這些抽象且極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一種新的視覺呈現(xiàn)方式,在滿足觀眾審美期待的同時,展現(xiàn)了河南內(nèi)斂且包容的文化性格。由此觀之,河南形象的建構(gòu)與媒介的傳播密切相關(guān)。
3.1 賦權(quán)多元主體,有效傳遞河南聲音
賦權(quán)多元主體意味著“人人都是媒體人”時代的來臨。在詹金斯的參與式文化理論中,當(dāng)受眾主動參與到信息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過程中時,就形成了所謂的“媒體流”,在這個過程中,媒介的議程設(shè)置功能弱化,受眾的情感依附明顯增加,逐漸成為信息傳播與接收的內(nèi)源性動力。因此,當(dāng)普通民眾擁有了控制輿論的能力時,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形象的書寫門檻。
對一個正在建造中的文旅項目而言,“幻城”以受眾為中心,堅持“互聯(lián)網(wǎng)+”的運營理念,聯(lián)合抖音、微信、B站等多個自媒體平臺,創(chuàng)造了更多互動性極強(qiáng)的“場外信息”。例如,B站UP主“破產(chǎn)兄弟”發(fā)布了一個題為《華夏文明為何從未中斷?“只有河南”能給出答案》的視頻,簡略介紹了“幻城”中各劇場的內(nèi)容及表演形式,獲得了大量的觀看、點贊和評論。也就是說,正是基于自媒體的有效傳播,才使這些“場外信息”有了更多探討和參與的可能。
3.2 融合多種媒介,建構(gòu)良好河南形象
麥克盧漢的著名論斷“媒介即訊息”,強(qiáng)調(diào)了媒介技術(shù)對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性。在他看來,真正決定文明形式的不是媒介傳遞的信息,而是媒介本身。技術(shù)的更迭引發(fā)了媒介模式的變革,由原來的口口相傳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影像傳播,傳統(tǒng)主流媒體“一家獨大”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由廣播、電視、報紙、手機(jī)終端、互聯(lián)網(wǎng)等多種媒介有機(jī)互動的全媒體傳播矩陣,繼而實現(xiàn)了從“輿論主場”到“輿論廣場”的轉(zhuǎn)變。
媒介生態(tài)的改變,為河南形象的傳播提供了契機(jī)。“幻城”順應(yīng)了媒介傳播的新態(tài)勢,按照“移動優(yōu)先、內(nèi)容為王”的原則,積極采用融媒體的傳播策略,聯(lián)合線上與線下、省內(nèi)與省外,向多個平臺發(fā)出觀看的“邀請函”。通過聚合多種媒介力量,消除了區(qū)域間信息流通的物理界限,完成了全覆蓋、多渠道、超時空的互動傳播。與此同時,借助這些傳播終端的市場優(yōu)勢及群眾資源優(yōu)勢,將河南的地緣、人緣和文緣有效融入對外傳播過程,大幅增強(qiáng)了河南形象的宣傳效果。
4 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賦能,感受沉浸式體驗
4.1 提煉視覺符號,實現(xiàn)現(xiàn)代性“轉(zhuǎn)譯”
新媒體時代,一種新的視覺文化現(xiàn)象出現(xiàn)并滲透在城市形象的肌理中,成為勾勒社會現(xiàn)實的強(qiáng)大力量。圖像語言相較于文字信息,更能激發(fā)人的帶有強(qiáng)烈情感的意識。技術(shù)保障下的數(shù)字影像憑借突出的涉身性和具象化媒介性質(zhì),被各種終端推崇,成為一種元媒介,并引發(fā)了當(dāng)前審美方式的變革。
基于人的感覺習(xí)慣,“幻城”以地域文化為依托,提煉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并將其影像化,通過調(diào)動人的全部感覺器官,建構(gòu)了一個具有多方位聯(lián)合表意的視覺文化景觀,進(jìn)而延續(xù)了戲劇節(jié)目的視覺生產(chǎn)與空間建構(gòu)。例如,閉園秀的《文明之光》就利用投影技術(shù)將《清明上河圖》和《千里江山圖》這兩幅靜態(tài)的圖像影像化,使整個“幻城”都成了臨時“演出者”,并將觀眾的思維與意識聚焦到眼前的視覺空間內(nèi),歷史與當(dāng)代、虛擬與現(xiàn)實互相交疊,帶給觀眾更為豐富的時空經(jīng)歷。這不僅提升了受眾的認(rèn)知和欣賞能力,還是迎合當(dāng)代審美范式的一種有力方式。
4.2 利用大數(shù)據(jù)技術(shù),實現(xiàn)精準(zhǔn)傳播
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和大數(shù)據(jù)的出現(xiàn),使精準(zhǔn)傳播成為可能。精準(zhǔn)傳播是指在綜合運用信息技術(shù)和先進(jìn)理念的前提下,根據(jù)受眾的不同需求對其進(jìn)行細(xì)分,通過制定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追求傳播效果更好、更高效的傳播方式。精準(zhǔn)傳播通過可量化的定位技術(shù),突破了傳統(tǒng)傳播方式的模糊性,同時借助先進(jìn)的數(shù)據(jù)庫技術(shù)、通信技術(shù)等手段,保證了與目標(biāo)受眾的長期互動,實現(xiàn)了受眾鏈?zhǔn)降姆磻?yīng)增值。
在精準(zhǔn)傳播的理念下,“幻城”從傳播內(nèi)容、傳播渠道及受眾群體三個方面進(jìn)行精準(zhǔn)定位。首先,在傳播內(nèi)容上,以中原傳統(tǒng)文化為導(dǎo)向,結(jié)合社會時事熱點,使內(nèi)容資源盡可能滿足大多數(shù)人的個性化信息需求;其次,在傳播渠道上,通過精確的信息定位和推送技術(shù),建立與受眾的溝通機(jī)制,以提升傳播的有效性;最后,在受眾群體上,基于受眾的個體特征、行為規(guī)律、活動場域及社會關(guān)系等多維信息,對目標(biāo)受眾進(jìn)行“量身定做”的傳播,建構(gòu)圈層化的傳播模式。
4.3 設(shè)置媒介場景,體驗沉浸式互動
人之情感,非言論所能及也;必置身于世,然后能道之。傳播學(xué)家梅羅維茨提出了媒介場景理論,旨在探討媒介如何影響人的行為和心理。在他看來,場景并非實際的地點,而是一種由媒介信息環(huán)境構(gòu)成的行為和心理的感覺區(qū)域。從傳播學(xué)的角度來說,人在接收外部信息的時候,調(diào)用的感官越多,心理上對該事物的形象認(rèn)知就越接近于真實,其傳播效能自然也就越高。我國學(xué)者李沁在《沉浸傳播》一文中指出,人類社會將進(jìn)入以“沉浸傳播”為特質(zhì)的“第三媒介時代”[10],這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傳播”。
得益于“5G+VR/AR”等新興技術(shù)的發(fā)展,“幻城”建構(gòu)起了多種趨近于現(xiàn)實的“擬態(tài)空間”。在這種可感知的環(huán)境氛圍中,受眾通過行進(jìn)式、碎片化的觀影方式,在心理和行為上實現(xiàn)了與環(huán)境信息的交流與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對受眾“身體在場”的召喚。可以說,正是通過場景的營造和知覺體驗,使戲劇與受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最終達(dá)到所謂的“心流”狀態(tài)。以《張家大院》為例,全劇圍繞一場豫商晚宴展開,其舞臺設(shè)在了一個相對開放的空間內(nèi),而觀眾席就散落在舞臺中間,這樣一來,觀者直接進(jìn)入了場景,有效成為表演者,從而沉浸式地感受“有國才能有家”的豫商精神。
5 結(jié)語
“立時代之潮流,發(fā)思想之先聲。”某種意義上,誰擁有媒介,誰就擁有了城市形象的書寫權(quán)。在建設(shè)文化強(qiáng)國的背景下,“只有河南·戲劇幻城”迎合了新媒體的發(fā)展趨勢,通過回顧歷史文本實現(xiàn)了與時代的共鳴,在喚起公眾文脈意識的同時,為河南形象的建構(gòu)與傳播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徑。
參考文獻(xiàn):
[1] 王守仁.傳習(xí)錄[M].北京:開明出版社,2018:77.
[2]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jì)要[M].賀次君,施和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2132.
[3] 劉高杰.國學(xué)經(jīng)典集錦[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137.
[4] 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5:6-7.
[5] 闕雨萱,鄧琰弋.新媒體視域下城市媒介形象建構(gòu)與傳播研究:以河南衛(wèi)視的“中國節(jié)日”系列節(jié)目為例[J].新聞研究導(dǎo)刊,2022,13(23):33-37.
[6] 辛志英.話語分析的新發(fā)展:多模態(tài)話語分析[J].社會科學(xué)輯刊,2008(5):208-211.
[7] 魯迅.魯迅佚文全集[M].北京:解放軍報社,1976:109.
[8] 黃丹,王廷信.旅游演藝傳播的“編碼與解碼”理論研究[J].藝術(shù)百家,2020,36(4):68-74.
[9] 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學(xué)引論[M].劉文玲,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14:5.
[10] 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義媒介概念的內(nèi)涵和外延[J].國際新聞界,2017,39(8):115-139.
作者簡介:楊曉娜(1996—),女,山西長治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藝術(shù)學(xué)理論(藝術(sh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