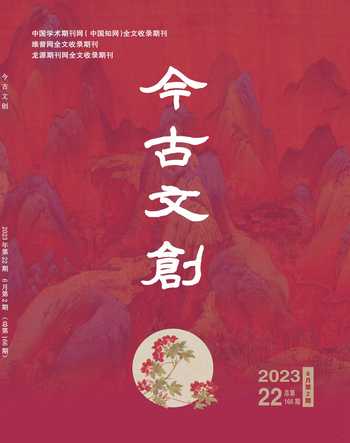《片刻榮耀》中的女性意識解讀
李雪松
【摘要】《片刻榮耀》是恩古吉·瓦·提安哥所著的重要短篇小說。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寫一個在城市酒吧做女招待的鄉下女孩遭受壓迫和自我覺醒的故事,以此展現女性生存困境和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景。女性意識作為現代社會中一種普遍的現象,在該作品中有著生動的展現。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作品從社會現象切入,將父權社會下女性承受的壓迫與自我拯救的努力過程展現出來,具有超越時代的思想藝術價值。
【關鍵詞】恩古吉·瓦·提安哥;《片刻榮耀》;女性意識;壓迫與覺醒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標號】2096-8264(2023)22-001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2.005
一、引言
恩古吉·瓦·提安哥是享譽世界的肯尼亞作家,其短篇小說《片刻榮耀》被收入由哈珀·柯林斯出版的世界文學選集。小說中女主人公比阿特麗斯從事酒吧女招待的工作,作為黑人女性面臨來自種族和性別的雙重壓迫。在困境與陰霾中比阿特麗斯反思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最終反叛傳統父權社會規則,獲得關于自我認知的覺醒。故事以生活中邊緣人物的經歷為線索,反映出恩古吉·瓦·提安哥對于社會特定群體中普遍問題的深切關注與思考。
本文從《片刻榮耀》中的女性意識出發,關注女性真實生存境遇,探索女性的生活走向與心靈救贖之路。
二、種族壓迫之苦
種族壓迫是階級剝削制度的產物。其實質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階級的利益,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對其他種族進行掠奪和奴役。種族壓迫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奴隸社會。古羅馬帝國將法蘭西人和日耳曼人視作“野蠻人”和“劣等種族”,強迫其服從大羅馬帝國。進入資本帝國主義時代后,白人殖民主義者更竭力散布“人種優劣論”,宣揚為殖民侵略、擴張政策而服務的殖民主義,對非洲的黑人、美洲的印第安人及其他有色人種進行殘酷鎮壓和野蠻掠奪。
種族壓迫并不會隨著殖民統治的結束而隨之消亡,往往轉化為一種內在隱秘的形式嵌入民眾內心。在《片刻榮耀》中,女主人公比阿特麗斯一度刻意追隨迎合白人審美標準,對于黑人女性的天然美感嗤之以鼻,迷失在黑白之間進退兩難。比阿特麗斯在酒吧工作卻不得客人眷顧,她將此簡單歸因于自己黑色的皮膚。于是她涂抹一種名為“阿姆比”的亮膚霜,天真地希望“擦去黑皮膚帶來的恥辱”[6]96。“阿姆比”亮膚霜對于比阿特麗斯來說,是十足的奢侈品,她只能少量地涂抹在臉和手臂上,但一些較隱蔽的部位仍然是黑色,這讓她覺得“羞恥且惱怒”[6]96。同時比阿特麗斯意識到包括自己在內,眾多黑人女性存在自我憎惡這一現象。比阿特麗斯的行為及思想體現出在長久以來的強勢殖民之下,黑人女性與本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念漸行漸遠,傾向于以白人的審美觀和價值觀為標尺衡量自己。
比阿特麗斯對于假發的渴求反映出另一重形式的種族壓迫。在非洲,黑人女性審美標準和白人女性審美標準共存,但后者處于強勢地位,影響眾多黑人女性的美與丑審視范疇。非洲女性對頭發造型的改變,或是拉直或是染發,都在很大程度迎合白人女性審美標準,她們的最大愿望就是以頭發為媒介從身體特征上來接近白人女性。她們之所以如此在頭發上下足功夫,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取悅黑人男性。
非洲國家經歷過白人殖民統治時期,白人審美使得黑人男性價值標準發生變化,不自覺地向白人審美文化靠攏接近。學者雪莉·安妮·塔特指出審美的種族屬性,美與丑的種族話語隱藏在各式各樣的美的模式中,“美”是在文化中被演繹的,文化意義上的美就是話語的結果[1]9。比阿特麗斯希望擁有“各種顏色的假發,金色的,深褐色的,紅色的”[6]100,“羨慕頭上戴著歐洲或印度式假發的女孩”[6]95。她作為酒吧服務生,對于假發種類的需求量本不該如此之多。比阿特麗斯每多擁有一頂假發,便是她靠近黑人男性的一步跨越。比阿特麗斯的假發喜好暗示出自己的種族身份和男性審美偏好,此時頭發已經超越生物意義上的身體體征,成為比阿特麗斯獲取男性目光與焦點的有效工具。可悲的是,在此過程中比阿特麗斯不自覺地落入白人審美擁有者——黑人男性的價值取向之中,淪為盲目追逐外在實則深陷種族壓迫泥淖的羔羊。
三、性別壓迫之痛
性別壓迫是種族壓迫的變種與支撐,二者相互獨立又犬牙交錯,形成復雜多變的壓迫系統。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寫就這樣一段帶給眾多女性主義者以啟示的話語:“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于無產階級……在現代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統治的獨特性質,以及確立雙方的真正社會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當雙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時候,才會充分表現出來。”[4]72
恩格斯對女性地位和生存境遇予以深切的關懷和思考,但現實中仍有眾多女性長久地囿于性別壓迫之下難以逃脫。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同時兼具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雙重身份,而以女主人公比阿特麗斯為代表的黑人女性則永遠處于被壓迫者的地位,承受痛苦和磨難。比阿特麗斯的動蕩人生是男性對女性壓迫的真實寫照。比阿特麗斯家境貧困,中途輟學,不擅長打字和速寫,缺乏基本工作技能。向往大城市生活的比阿特麗斯被一個年輕男子騙至酒吧,她透過酒吧看見被霓虹燈點亮的城市,誤以為此處便是夢想開花之所。實際上,涉世未深的比阿特麗斯誤打誤撞跌入性別壓迫的深淵,由此開啟噩夢般的人生軌跡。
“那個黎明的許諾讓她感到快活而飄飄然”[6]103,一覺醒來,帶領她來到酒吧的男人已經不知去處,比阿特麗斯不情愿地擁有新的身份——酒吧女招待。來到酒吧時至一年半,比阿特麗斯從未得到機會回去探望父母。比阿特麗斯“對自己飽受的凌辱和輾轉的經歷記憶猶新”[6]103,不甘心屈居于此卻難以另謀出路。比阿特麗斯的悲慘遭遇正是由男性騙子肇始的性別壓迫所導致。
比阿特麗斯作為酒吧女招待,酒吧老板對她輕蔑克扣是性別壓迫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酒吧老板被尼婭古蒂拒之門外后找到比阿特麗斯,對她又是侮辱又是奉承,“方式有些勉強甚至輕蔑”[6]97。在比阿特麗斯疲于招待過多的顧客而略顯力不從心時,老板在既不預先通知,也不發放工資的前提下就單方面通知她被解雇。這實際上是在強化黑人女性的“騾子式”存在狀態,騾子般的命運規定黑人女性永久忍耐、不停勞作,是性別歧視對女性自我帶來的壓抑與扭曲。在比阿特麗斯的前期認知中,出賣身體、依賴男性客人以期從其身上獲取資源價值是無可厚非的。“她幻想著情人們開著油光锃亮的奔馳雙人跑車來接走她,看到自己和他手牽著手走在內羅畢和蒙巴薩的街道上”[6]99。比阿特麗斯甚至在看到“比她更丑的女孩,在臨近打烊的時候,被一幫顧客爭搶著”[6]94,悵然若失,她渴望自己可以在某一個酒吧中“至少也位居統治者之列”[6]94。這些無一不在言說著比阿特麗斯曾經妄圖成為男性群體中炙手可熱的一員,把自己生活的前景與希望寄托于毫不相關的男性客人之上,也從側面勾畫出她潛移默化中接受“女性依賴男性,處于從屬地位”這一觀念。現實給予她沉重而清醒的認識,比阿特麗斯不過是在接受一鎊錢后,“充當一位傾聽者,一個盛放他滿腹牢騷的器皿,充當接受男人一夜負擔的容器”[6]102。至此不難發現,以男性為中心的話語體系中,女性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帶有性別壓迫的烙印。在父權制性別規范的不斷內化和強制操演下,比阿特麗斯喪失了自我主體意識,質疑自我存在的意義與歸屬。
四、反叛與覺醒之路
福柯指出,“權力無所不在……這不是說它囊括一切, 而是指它來自各處”[5]67。壓迫與反叛相伴相生,父權制社會下男性對女性的剝削與掠奪是造成女性反叛與崛起的重要原因。
比阿特麗斯一方面在男性支配的社會中屢遭欺凌,成為男性尋歡作樂的工具,另一方面在潛意識中追求男性的認可和夸贊,以此作為審美標準與存在價值。正如波伏娃所說,“她們始終依附于男人,男女兩性從未平等地分享世界”[7]16。可見,比阿特麗斯長期處于男性意識形態的禁錮之下,落入根深蒂固的傳統俗套。
那么比阿特麗斯的反叛意識從何時萌生呢?回顧全文,她的反叛具有階段性,并不是一蹴而就。首次拒絕老板的無理請求讓比阿特麗斯初嘗打破既定規矩的可能性。面對老板的侮辱行為,她異乎尋常地對老板身上的一切產生反感。即便老板以送禮物為由,她依舊嚴詞拒絕,違抗“規矩”從窗戶跳出,另尋住處。“她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驚奇” [6]97,由此可見比阿特麗斯不甘愿乖乖順從父權社會,開始萌生探尋自我價值的想法。
在居無定所、漂泊流浪之時,比阿特麗斯想起母親居住的小鎮——世界上最甜蜜的地方也是記憶中遙遠的風景,夢想著“與土地、莊稼、清風、明月同樂;在漆黑的樹籬下竊竊私語;在明亮的月光下跳舞相愛”[6]98。在對反叛的認知過程中,個體往往需要通過他者或外部刺激來喚起自我記憶,進而達成對現存狀態的批判性否定。
更深層次的反叛發生在偷竊客人錢財之時。這位客人與其他眾人概不相同,他身世可憐,生活貧苦。在他自言自語式講述自己辛酸過往之時,比阿特麗斯竟看到他內心深處存在的“一團火,一粒種子,一朵正被慢慢窒息的花”[6]102。比阿特麗斯以同病相憐的受害者視之,準備同樣地將自己的曲折過往與之一吐為快。在動情講述之后,她被一股莫名的空虛感襲擊,感到一陣撕心裂肺的痛苦,因為“那個男人早就蓋著被子睡著了,鼾聲如雷” [6]103。在她看來,自己“內心深處的騷動成為他的催眠曲” [6]104,于是比阿特麗斯帶著冷酷而堅定的眼神帶走他身上五張粉色的新紙鈔。此時的紙鈔對于比阿特麗斯已經失去平日里金錢交易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種對積壓的憤怒與受辱的委屈變相疏解。
偷竊舉動嫻熟自然,仿佛經歷過歷練一般。這說明比阿特麗斯往常不屑于做此種事情,這一次偷竊是以往數不勝數的內心斷裂感集中爆發,是對父權社會加之女性“召喚功能”的否定與抑制。經與尼婭古蒂交談之后,比阿特麗斯的反叛意識徹底得到釋放與肯定。尼婭古蒂勇敢追尋個體解放,為比阿特麗斯擺脫陰霾性的現存狀態提供參考與指引。
尼婭古蒂家境殷實,父母篤信基督教,生活在宗教禮儀的繁文縟節之中。最終尼婭古蒂不堪重重規則制約,選擇逃離令人窒息的家庭環境,走向紛繁復雜卻享有自由的社會,并將此視為暫時逃避現實的避難所。尼婭古蒂的出逃行為揭示出眾多女性悲劇命運之后隱藏的傳統父系社會體制。值得慶幸的是,尼婭古蒂擁有強大的精神與內心作為支撐,跳脫父系社會規則架構,建立自己的價值坐標。二人的交談使這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借助語言的形式得以傳遞給比阿特麗斯,賦予后者新生的希望與憧憬。
比阿特麗斯與尼婭古蒂的促膝交談在房間之中進行,自然而然會使讀者聯想到伍爾夫的經典作品《一間自己的房間》。她認為“一個女人如果想寫小說,就必須有錢,以及一間自己的屋子”[2]4。女性想要從“共有生活”中跳脫出來,必須有一間屬于自己的可以上鎖的房間。上鎖的房間給人以空間,使人獲取思考和表達的自由,是女性得以庇護的安全避難所。在房間中,尼婭古蒂講述自己離家出走的原因,表明對比阿特麗斯的賞識與吸引。長久以來困擾比阿特麗斯的命題“尼婭古蒂恨我,看不起我”不攻自破。比阿特麗斯從尼婭古蒂的經歷認識到身為女性實現自救而非他救的必要性。
黑人女性主義運動初步萌芽于19世紀后期。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60年代黑人運動洗禮后,黑人女性主義運動逐步發展壯大,其理論與實踐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取得突飛猛進的進步。黑人女性覺醒者不斷加入黑人女性解放的事業,從多方面入手明確地對黑人女性主體意識進行探討。比阿特麗斯是黑人女性覺醒者的典型代表,歷經對父權社會反叛,達到自我價值與主體意識的雙重覺醒。比阿特麗斯一改往常刻意取悅男性的心理狀態,開始更多地關注自我的情緒感受。比阿特麗斯在商店給自己購買長襪、新衣服和高跟鞋,走到鏡子前,打量全新的自己。服裝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人內心狀態的外化體現,換裝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比阿特麗斯獲得經濟獨立的開端,也是她理性選擇下與過去軟弱自我的決裂。面對陌生男性的悅色與欲望,比阿特麗斯勇敢地走出酒店,“拋下沒吃完的飯和沒碰過的酒”[6]106。在酒吧里接二連三的邀請向比阿特麗斯遞來,她不為所動,“卻毫不客氣地接過他們為她送來的酒”[6]107。酒在特定場合是建立聯系、溝通情誼的有效工具,此刻比阿特麗斯擁有拒絕或是接受的權力,將選擇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自動唱機旁邊手舞足蹈的比阿特麗斯,“她的身體是自由的,她也是自由的”[6]107。
關于身體的研究,福柯指出現代權力以“更隱蔽的方式實現對身體的控制”[3]251。當父權統治階級的欲望對女性實現征服,女性便失去對自己身體的擁有權與控制權。而比阿特麗斯的身體和自我反抗被動接受書寫的地位,勇敢地直面殘酷冷淡的命運糾葛,對女性悲劇命運進行思考與詰問,顛覆舊有父權制成規,積極進行個人心靈探索與調整,理性思考女性價值和主體地位所在,最終實現自我意識的覺醒。
五、結語
比阿特麗斯是黑人女性意識覺醒的典型代表,打破父權制對女性思想和身體的禁錮。通過對自我價值與主體意識的找尋與堅守,比阿特麗斯勇敢地反抗種族壓迫和性別壓迫,形成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堅定信念。恩古吉·瓦·提安哥關于女性命運的書寫不僅僅局限于肯尼亞,他反抗壓抑人性的傳統制度和觀念,追求普遍意義上的兩性平等和個性解放。恩古吉·瓦·提安哥為女性走出壓迫邁向覺醒提供樂觀的嘗試,為新時代女性追求自由和幸福展示美好的期盼與愿景。
參考文獻:
[1]Tate S A.Black Beauty:Aesthetics,Stylization, Politics[M].Routledge,2016.
[2]弗吉尼亞·伍爾夫.一間自己的房間[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10.
[3]黃華.權力,身體與自我福柯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米歇爾·福柯.性經驗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欽努阿·阿契貝,C·L·英尼斯編.非洲短篇小說選集[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7]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譯本[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