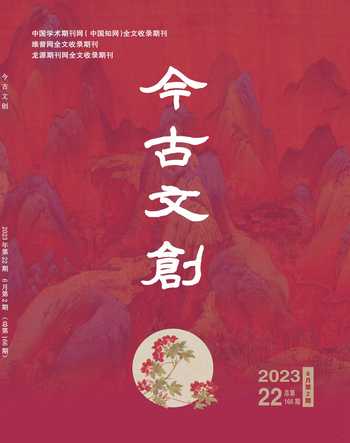淺析孔子與董仲舒關(guān)于正名思想的異同
【摘要】儒家的“正名”思想,是由孔子提出并經(jīng)后人不斷發(fā)展豐富的理論。從孔子的“名實(shí)相應(yīng)”,到荀子的“制名以指實(shí)”,再到董仲舒的“名則圣人所發(fā)天意”“名生于真”。在這之中,“名”的內(nèi)涵意義不斷在發(fā)展變化,但“正名”思想的目的——為政治服務(wù)并無改變。
【關(guān)鍵詞】正名主義;孔子;董仲舒;政治;邏輯
【中圖分類號】B21? ?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 ? ? 【文章標(biāo)號】2096-8264(2023)22-005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2.015
一、“正名”字義辨析
“正名主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要了解“正名”思想,首先我們需要知道什么是“正名”?“正”是什么,“名”又是什么?
《說文·正部》:“正,是也。從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從正。”“一”是古文“上”字,表示在上位者,所以有“會上位者止于正道之意”。同時又有“合于法則”的引申意。《說文·口部》:“名,自命也。從口,從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名”的本義為自己報出名字、起名字。由命名引申用作名詞,表示名字、名稱。同時又引申為名聲、名望。
此外,“正”字又有“政”的意思。《論語·顏淵篇》第十七章有言: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說文·攴部》:“政,正也。從攴,從正,正亦聲。”從正,會采取措施使正確之意。“政”的本義為糾正它使變正確。如《墨子·天志上》:“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
從字義辨析來看,“正名”即可意為辨正名稱、名分,使名實(shí)相符。
二、孔子的正名思想
要探討孔子的正名主義,我們需要回到孔子提到正名的文本當(dāng)中。在《論語·子路篇》,孔子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正名主義思想,其內(nèi)容如下:
子路曰:“衛(wèi)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先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這一段主要是記載了子路向孔子探討治理國家要先做的事是什么,而孔子對他的回答乃是正名。接下來,讓我們對這段話進(jìn)行詳細(xì)的解釋。首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四書章句集注》引楊氏曰:“名不當(dāng)其實(shí),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shí)而事不成”。即是說,名聲如果不能與實(shí)際相符,說起話來就不順當(dāng)合理,話說得不順當(dāng)合理,就難以被考實(shí),這樣一來事情就會做不成了。接著,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那么這里的禮樂指的是什么呢?范氏注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這里的注釋先對禮和樂下了個定義,禮,在范氏看來是事情運(yùn)行的秩序,樂則是事情按照其秩序平穩(wěn)地運(yùn)行。他認(rèn)為,如果事情做不好了,那么禮樂就會失去它們原有的秩序,禮樂一不能運(yùn)作,那么所有施行的政策就會失去基礎(chǔ),那么刑罰就不能發(fā)揮作用了。最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引程氏的話而言即是:“名實(shí)相須,一事茍,則其余相茍也。”這里很好地解釋了名實(shí)相應(yīng)的基礎(chǔ)性作用。只有名實(shí)相應(yīng),禮樂才能順利運(yùn)行,國家才能正常運(yùn)行。
“正名”這一思想的提出,有它的時代背景。孔子提出正名,是回應(yīng)子路的“為政奚先”問題。所以“正名”最開始是指向政治問題的。“政治”一詞,并不同于我們?nèi)缃袼v的“政治”,“政者,正也”,政治的要求,更多的是對統(tǒng)治者的要求,要求執(zhí)政者發(fā)揮其表率作用,從而促進(jìn)整個社會的“正”。從文本內(nèi)部看,“衛(wèi)君待子而為政”,“衛(wèi)君”指衛(wèi)出公衛(wèi)輒。《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夏,衛(wèi)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wèi)出公。六月,趙鞅內(nèi)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偽自衛(wèi)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wèi)圍戚,以衛(wèi)太子蒯聵在故也。
這段話大意是:這年夏天,衛(wèi)靈公死了,他的孫子輒立為國君,這就是衛(wèi)出公。六月間,趙鞅把流亡在外的姨靈公太子蒯聵接納到戚地。陽虎讓太子蒯聵穿上孝服,又讓八個人空麻戴孝,裝扮成是從衛(wèi)國來接太子回去奔喪的樣子,哭著進(jìn)了戚城,就在那里住了下來。冬天,蔡國遷都到州來。這一年是魯哀公三年,孔子已六十歲了。齊國幫助衛(wèi)國包圍了戚城,是因?yàn)樾l(wèi)太子蒯聵在那兒的緣故。《論語注疏》邢昺疏:案《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wèi)。是時,衛(wèi)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shù)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wèi),君欲得孔子為政”。這就是孔子正名之說的政治背景,即衛(wèi)出公輒和他父親蒯聵之間存在君位繼承問題,這可以說明孔子正名之說的提出所解決的首要問題即政治問題。
不僅在此,孔子在別處也強(qiáng)調(diào)了正名主義的思想。如在《雍也·第六》中,孔子言: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在《朱子全書》中認(rèn)為: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我們可以將觚理解為一種有棱的器具。這句話表達(dá)的意思也就是說,觚,作為一種有棱的器具,卻沒有棱,還能稱為觚嗎?這里也隱含了孔子的正名主義思想,觚,按照其定義而言,就是要有棱的事物,而現(xiàn)在如果對于一件沒有棱的事物卻稱之為觚,那么就是名稱與事物不相符。宋代的程頤和程顥在對觚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將正名主義延伸到了政治領(lǐng)域,在對該段進(jìn)行注解時,其言:
觚而施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識,則為虛位。
上述話也就是將正名主義運(yùn)用到了政治領(lǐng)域。即就是說,正名主義應(yīng)該不僅僅是使觚成為觚,使器具成為與之名稱相符的器具,更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的觀念,使君為君,臣為臣,各司其職,不越界。
胡適在其《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曾這樣評價孔子的正名主義:“建立公認(rèn)的是非真?zhèn)螛?biāo)準(zhǔn),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問題。” ①儒家的重點(diǎn)不像道家般置于形而上學(xué),也不像名家置于邏輯,也不像法家特重功利,它所重的乃在倫理層面。其意不僅認(rèn)定名實(shí)必須符合,而且主張職位、職務(wù)、職能等,也須詳加規(guī)定,切實(shí)執(zhí)行,唯有如此,才能說符合正名。
正名主義,是孔子提出的行為標(biāo)準(zhǔn)之一,即君子要對自己的言行負(fù)責(zé)。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并沒有從理論上來論證正名主義的合理性,相反,他更多是在道德層面強(qiáng)調(diào)正名主義的應(yīng)然性。追究其哲學(xué)基礎(chǔ),我們可以從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guān)系來進(jìn)行解釋。名,是事物的概念,而事物的概念往往表達(dá)的是事物的本質(zhì),而實(shí)往往就是事物的內(nèi)容,而名表達(dá)的事物的概念,往往實(shí)一種形式,所以名實(shí)相應(yīng),則是強(qiáng)調(diào)形式要與內(nèi)容相對應(yīng)。
三、董仲舒的正名思想
要了解董仲舒時期的正名思想,就得對董仲舒所處的歷史時代有一個了解。董仲舒身處漢初,劉邦剛建立漢朝時,經(jīng)濟(jì)凋敝,百姓痛苦,所以漢初實(shí)行了黃老之學(xué)以休養(yǎng)生息。這里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稷下黃老之學(xué)也尤為強(qiáng)調(diào)正名主義,《管子·白心》 ②中的核心命題便是——“名正法備,則圣人無事”,其意即當(dāng)名實(shí)相符再輔之以法律,那么圣人就不用操心國家之事了。黃帝四經(jīng)中的《經(jīng)法·道法》也曾言:“是故天下有事,無不自為刑( 形) 名聲號矣。刑( 形) 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跡匿正矣。” ③盡管這里的正名主義是與刑罰相結(jié)合,但是不可否認(rèn)的是黃老之學(xué)重視正名主義,并將正名主義的范圍擴(kuò)大到了刑法領(lǐng)域,所以,在漢初推崇黃老之學(xué)的環(huán)境下,董仲舒的正名主義多少受到了黃老之學(xué)的影響。
在經(jīng)濟(jì)恢復(fù)、百姓生活改善、政權(quán)鞏固之后,漢武帝任用董仲舒,實(shí)行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圍繞“封建大一統(tǒng)”的主題來展開,它提出的“以民隨君,以君隨天”是春秋之法的根本準(zhǔn)則。董仲舒的正名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其著作《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第三十五中,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開篇董仲舒就強(qiáng)調(diào)了名號的重要性以及名的來源:
治天下之端在于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之逆順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
在這一段話中,“審辨大”一詞,蘇輿注:辨,別也。審事物之所以別異于大綱,故曰“辨大”。其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春秋繁露》中,被解釋為審查清楚事物的類別和大綱。“名者大理之首章也”一句,據(jù)《春秋繁露義證》言:“理者,分也。分者,必有以括之。首章所以括其大分也。古人著書,當(dāng)有綱領(lǐng),列之首章,故此言事物有名,猶大理之首章也,后人議事,亦以首章為綱要。”這里強(qiáng)調(diào)的是道理,是可以分開來講的,可以分開的事物,必然需要有一個總的類來概括。一本書的綱要便可以概括其大分。名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本書的綱要,當(dāng)我們談?wù)摰揭粋€事物時,往往是先從名入手的,從名來了解事物的內(nèi)容。后面的“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之逆順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這一句是承接上一句來講的,上一句中將名的作用比作書的綱要,列于首章,當(dāng)我們讀懂首章的意思之后,并深入了解其主要內(nèi)容之后,那么就可以知道是非,明白逆順,它的微妙所在就和天地相通了。后面一句則是用來解釋前面為什么“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后能達(dá)到“是非之逆順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其原因主要是“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對于該句,在《春秋繁露義證》中,蘇輿案:“崇效天,卑法地,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本于此。聞其名則喻其實(shí)。逆夫人心之所受,則禮法可以為禁。故分曰名分,教曰名教,分與教皆生于名,俾天下不敢懍然而不敢犯,此治世之要樞也。”在蘇輿看來,君臣、父子、夫婦這些詞,只要聽到其名字就知道其代表的是什么,即其名稱已經(jīng)暗喻了其背后的內(nèi)容,正所謂“聞其名則喻其實(shí)”,治理國家的關(guān)鍵就在于“名”,并且該“名”是“取之天地”的,只有這樣,世人就不敢隨意地更改名以及做與其“名”所規(guī)定的不符的事。所以說,是非的辯證,取決于逆順;逆順的辯證,取決于名號;名號的辯證,取決于天地,天地是名號的大義。
名來源于天,那么名的特點(diǎn)是什么呢?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第三十五中對于名的特點(diǎn),其記載道: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
在這里,董仲舒強(qiáng)調(diào)了名生于真,而這種真并不是判斷真假的真,而是一種天意之真。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即是說圣人所傳達(dá)的是天的旨意,天所傳達(dá)的名號才是真的。可以認(rèn)為,在董仲舒那里,名的來源是天。
董仲舒在這里巧妙地構(gòu)建了天、圣人和名的關(guān)系。即是說,名是來自于天意的,而天意即是真的,那么如何表達(dá)這種名號呢?則需要圣人作為二者的媒介,圣人所說的即是真的,通過圣人來使天意傳達(dá)下來。在這里可以將其轉(zhuǎn)化為“天”與“人”的關(guān)系,即是人要遵從天的旨意。從這兩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名”與“真”都覆蓋上了神秘色彩,與其所倡導(dǎo)的天人感應(yīng)的理念相對應(yīng)。除此之外,董仲舒的名實(shí)相符概念也體現(xiàn)了一定的邏輯框架,他不再像孔子強(qiáng)調(diào)正名的應(yīng)然性,而是強(qiáng)調(diào)了正名主義的前提和理論基礎(chǔ),即天人合一和名從天來。
四、孔子與董仲舒正名之異同
孔子作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的正名思想,更多的是從道德層面上對人們的思想行為形成一種規(guī)范制約性的作用,強(qiáng)調(diào)的是人內(nèi)心的自我修養(yǎng),這里更多體現(xiàn)的是一種可選擇性,因?yàn)榇嬖谶x擇,才能突出一個人的內(nèi)心道德修養(yǎng),如“君君,臣臣,夫夫,子子”。正名強(qiáng)調(diào)的名實(shí)相符對應(yīng)人的修養(yǎng)層面,一個人只有名與實(shí)相符了,即是言行一致,或者說人們所在的職務(wù)要與其職責(zé)相一致,才能更好地促進(jìn)國家的運(yùn)行與運(yùn)作。可以說,孔子的正名主義并不具備有很強(qiáng)的邏輯性,孔子是依靠一整套倫理綱常以及人們內(nèi)心的自覺來為強(qiáng)調(diào)證明的合法性。
而董仲舒作為漢代儒家的發(fā)揚(yáng)者,其繼承了先秦時期儒家的“正名”思想,但其并沒有一味照搬,而是將儒家的正名思想與漢代當(dāng)下的社會條件相結(jié)合,董仲舒主要是將“正名”思想與天意相結(jié)合,利用正名思想,在人、天的關(guān)系中鞏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董仲舒提出的正名思想是為政治服務(wù)的,即是說,要想達(dá)到名號為真,即名實(shí)相應(yīng)的境界,那么就必須借助圣人,來傳達(dá)天意所指示的名號,這樣就必須遵從圣人,遵從天意。這里與儒家強(qiáng)調(diào)的正名主義具有很大的差異,這里的名來自天,更多強(qiáng)調(diào)的是一種必然性的結(jié)果。其次,董仲舒不再延用孔子對正名主義來源的非合邏輯性解釋,而是在此基礎(chǔ)上增添了邏輯性。董仲舒強(qiáng)調(diào)天人合一的觀念以及強(qiáng)調(diào)天是最高統(tǒng)治者的思想,可以說,前兩者是董仲舒正名主義的邏輯前提和基礎(chǔ)。
盡管儒家的正名思想更多是從人的道德修養(yǎng)的層面出發(fā),而董仲舒的正名思想更多的是從為現(xiàn)實(shí)政治服務(wù)的需要出發(fā),但無可否認(rèn),二者的正名思想仍然存在著相同之處。孔子周游各國,倡導(dǎo)儒學(xué),試圖恢復(fù)周禮,所以在其正名思想中無可避免地為隱藏了為政治服務(wù)的目的。孔子將言行相應(yīng)與禮樂的興衰結(jié)合在一起,仍然強(qiáng)調(diào)了正名思想需要為當(dāng)時的政治服務(wù)。俞榮根先生認(rèn)為:儒家的正名主義實(shí)質(zhì)上是為了構(gòu)造“法自君出的立法觀” ④,深刻強(qiáng)調(diào)了正名主義對于統(tǒng)治者的重要性。而董仲舒,雖然從其所強(qiáng)調(diào)的正名主義來看,盡管更多地體現(xiàn)了其政治性,但是,其對名號的定義,認(rèn)為其來自天意,還進(jìn)一步區(qū)分了“名號”,認(rèn)為不同的等級遵循不同的“名號”,這樣國家才能正常運(yùn)行,這里的思想與儒家相比便具有較強(qiáng)的邏輯性和規(guī)范性。董仲舒對名號的強(qiáng)調(diào),同時也促成了漢代時期“以名為教”的教化方式的確立,促進(jìn)了漢代大一統(tǒng)政教合一局面的生成。所以,董仲舒的正名思想也與孔子所倡導(dǎo)的正名思想一樣,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
注釋:
①胡適:《中國哲學(xué)史大綱》,崇文書局2015年版。
②郭沫若認(rèn)為《白心》出于尹文,仍屬稷下黃老的思想。參見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八卷《青銅時代·宋钘尹文遺著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7—572頁。
③《經(jīng)法·論約》:“故執(zhí)道者之觀于天下也,必審觀萬物之灰始起,審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存亡興壞有處,然后參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經(jīng)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2頁,第39頁。
④俞榮根:《儒家法思想通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頁。
參考文獻(xiàn):
[1]許慎.說文解字[M].沈陽:遼海出版社,2014.
[2](南宋)朱熹注.論語·子路篇[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
[3]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
[4]朱熹.朱子全書·雍也·第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朱熹注.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6]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華書局,1975.
[7]汪奠基.中國邏輯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簡介:
黃海燕,女,漢族,廣東汕頭人,華南師范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哲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