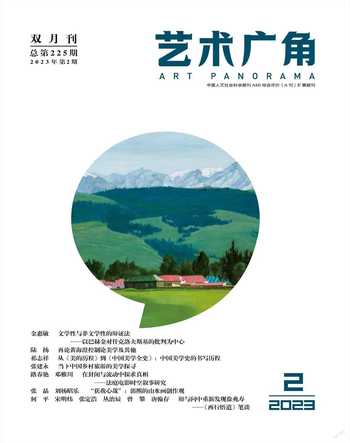身體:解構思想的武器
李帥
摘 要 伊格爾頓從兩個向度上論及身體:理論上,身體是其解構思想的武器;批評上,建構了身體政治批評話語。從元身體學的角度看,伊格爾頓對于身體的創造性特質的論述乃在于對人的本性的論述,強調身體的主體性地位。在美學與政治的關系上,伊格爾頓的目的是解構西方存在300多年的經典美學;解構實則是為了重構,即重建一種唯物主義美學。在文化與自然的關系上,伊格爾頓對馬克思的身體觀的解讀是建構其身體理論的基石;從文學與人類命運的關聯上看,身體詩學是介于現實物質世界與形而上學之間的批評理論形態。
關鍵詞 特里·伊格爾頓;身體詩學;解構思想;西方馬克思主義
一種理論的誕生,源自對實踐的思考、總結、歸納和概括,并經過理性的分析和邏輯的演繹將其構建成一個體系,這是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對身體問題的關注,源自人類對自身的反思,也是思維方式不斷發生改變的結果。從本體論、認識論到生存實踐論等思維方式的不斷轉換,人類如何看待身體的視角也隨之轉換。西方身體文化理論經由蘇格拉底到尼采的起源和流變,在20世紀以及21世紀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影響較大的有弗洛伊德的潛意識操控的身體、巴赫金的身體修辭學、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福柯的身體政治、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舒斯特曼的實用主義身體美學、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別身體以及唐娜·哈拉維的賽博格身體思想等。在這精彩紛呈的西方身體文化理論當中,英國文論家特里·伊格爾頓可以說是獨特的。他并沒有構建一種新的身體理論,但是在他的學術思想中,身體確實有一種獨特的地位,在細讀和耙梳他的思想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身體是他解構思想的武器。
一、元身體學:哲學與宗教
身體既然作為他解構思想的武器,這里面實際上有兩個論斷:一是伊格爾頓有解構思想,二是伊格爾頓解構思想的解構所運用的工具是身體。那么,這兩個合二為一的論斷是否真的站得住腳,有其現實的理論依據呢?身體是工具還是目的本身呢?帶著這樣的思考,我們來看看關于我們“是一個身體”還是“有一個身體”的爭論。這有點兒類似于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還是“我在故我思”的抉擇和判斷。“我有一個身體”也確實是出自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集》。[1]如果說“我有一個身體”,那么意味著身體是客體、是對象,可以被任意處置,身體成為達到目的的工具,是使用性的、實用性的;如果說“我是一個身體”,那么意味著我就是身體本身,身體就是我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前者代表的是西方傳統身體觀即主客二分的作為客體的身體,后者代表的是以尼采為發端、梅洛-龐蒂首創的一切從身體出發的身體現象學,強調身體的主體性地位。
伊格爾頓無疑是非常推崇梅洛-龐蒂的。他說:“我們這個時代有關身體的最佳著作肯定是莫里斯·梅隆-龐蒂的《感覺現象學》一書,但是這本書帶有把身體視為實踐和構想的人本主義意義,因此對于某些思想家是完全過時的,從梅隆-龐蒂向福柯的轉移,是作為主體的身體向作為客體的身體的轉移。” [2]由此,伊格爾頓引出關于身體問題的核心觀點是身體的創造性特質,“人體的特殊之處就在于它的在改造它周圍物質客體的過程中改造它自己的能力”[3]。伊格爾頓對后現代主義文化的批判正是借助于身體的主體性地位,而身體的創造性特質正是人性的核心,卡西爾將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將人性定義為“人的無限的創造性活動”。[4]伊格爾頓的主要研究領域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意識形態、政治批評等文學的文化研究和外部研究,雖然他承認身體相對于意識而言或者說物質相對于意識而言的優先性地位,畢竟他繼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第一性、生存實踐論思維方式等,但是,他所意在建構的思想體系卻不是身體本身,正如在《作為語言的身體》中,他通過身體將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和形而上的天主教神學之間的斷裂加以彌合;在《美學意識形態》中,他通過身體的中介鏈接起審美和意識形態,試圖以美學的中介通向更廣大的政治、社會、倫理等問題;在《后現代主義的幻象》中,闡發了身體本身的創造性特質,批判了后現代主義身體學;在《文化的觀念》中,提出身體是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一個鉸接與黏合劑;在《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中,提出了正是人類所共享的物種身體成為理解、同情、愛的基礎和前提,并能使我們彼此感同身受。身體的中介屬性、工具屬性在伊格爾頓的文論思想中一覽無遺,而身體之所以能夠成為伊格爾頓解構思想的武器的原因是身體本身的創造性特質及身體的主體性地位。
那么,伊格爾頓如何切入對身體問題的研究和思考?這直接涉及到語言與身體的問題、身體與主體的問題。“身體”“主體”同時是“自我指涉的問題也就是語言問題,因為只有經過語言的中介,身體才能呈現為具有意指內涵的形象、概念或符號” [5]。在《作為語言的身體》中,“伊格爾頓以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中的陳述作為論述的起點:狗不是語言動物,狗不可能是虛偽的也不可能是真誠的” [6]。這個譬喻表明了人類社會的獨特性,“人類社會既是生物聯合體又是語言聯合體。人類社會起源于我們共同的身體特征以及我們共享的交流能力”[7]。伊格爾頓認為,語言世界的入口向人類敞開,等于同時向人類敞開了語言的創造潛能和語言的破壞潛能。伊格爾頓說:“語言的創造潛能和破壞潛能的分裂導致某些人出于個人獲利的目的,將其他人的身體看作是能被剝削和利用的商品,從而導致精神和政治的雙重‘墮落:‘當人類……出于個人自我提升的目的把其他人用作客體……人就犯了基督教所言之罪和社會主義所稱的資本主義。(BL52)”[1]伊格爾頓寫作《作為語言的身體:新左派神學綱領》的目的是通過語言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重新思考基督教墮落和拯救的問題,而身體與語言的辯證關系在其中起到中介的作用。
由此可見,特里·伊格爾頓從元身體學的角度把人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言說。關于人的論述,馬克思從“類”“類本質”“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逐層推進以區分于異化的人;馬爾庫塞則將資本主義社會中被資本異化的人稱為“單向度的人”;海德格爾從時間維度指出“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于天地人神構架中的“在”;梅洛-龐蒂則從空間維度將人還原為身體性存在,由此引出關于主體性的主題。而伊格爾頓對身體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重建有關。伊格爾頓對海德格爾頗有微詞,認為他的“此在”不吃不喝。海德格爾的“此在”只是針對“他在”和“存在”而言,此在是個體的和現象的,此在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一個空間范圍內時間性存在的物質實存,這個物質實存就是身體。《美學意識形態》運用身體的目的是追溯到作為整體的人或人的本性,以解構西方傳統美學。
解構主義消解一切,當一切都被打破之后,必然要求重構,如何重構?重構什么?特里·伊格爾頓發現了身體。“身體是我們所有的人類存在既有事實最明顯標記”[2],“身體重要性的一部分是它的匿名性”;“身體是我現身在別人面前的多種方式之一”。[3]我們可以在某種意義上理解為身體就是海德格爾的此在在后現代時期的瞬間在場、當下聚集的物質性實存。后現代思想家要追問的不是“為什么有存在而無卻不存在”,他們要追問的是怎么證明有的存在?有以什么樣的形態存在?于是,追問到身體。此在以身體性的方式存在。身體在空間中存在,身體在時間中留存、也消逝。也就是說,哲學上某些古老的問題,需要從此在出發,從身體出發重新去追溯。特里·伊格爾頓追溯的目的是出于后理論時代解構之后重構的需要。
二、身體話語:美學與政治
伊格爾頓從兩個向度上論及身體:理論上,身體是伊格爾頓解構思想的武器;批評上,他建構了身體政治批評話語,這套話語的核心關鍵詞是審美與感性、物種身體與情感結構、性別身體和女性身體。伊格爾頓的第一個目的是解構西方存在300多年的經典美學,即鮑姆加通的感性學(Aesthetics)。從鮑姆加通為美學命名的缺憾談起,指出身體的缺失導致美學并沒有沿著感性學的道路發展下去,而是開啟了理性對感性的殖民化,其根本原因在于鮑姆加通是從認識論的思維方式命名美學,這是他的失誤之處。“按說人類的‘感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感知、表象、想象、聯想為要素的感性認識,這是與認識活動相關的;一是以生理欲望、原始沖動、感官快適、自然本能等為表現形式的感性生活,這是與肉體和官能直接相關的。”[4]而美學應是二者齊備。但顯然,鮑姆加通所開創的經典美學只是指向了感性認識,而沒有囊括進感性生活,由此伊格爾頓在《美學意識形態》中直接指出:“美學是作為有關肉體的話語而誕生的。”突出了身體的優先性地位,同時展開對經典美學的解構,既然從一開始美學就走上歧路,是時候回歸起點,重新開辟一條新路。
這個身體有豐富的內涵和所指,所代表的是人類的感性生活,即“與肉體和官能直接相關的生存狀態,包括情感欲望、生理需要、本能沖動、感官快適等”審美活動的重要方面,是身體話語。但由于伊格爾頓在范疇使用上的松散和寬泛,“因此他所謂‘肉體,并非僅僅指人自然的、原始的動物性方面,而且是指那些經過文化陶鑄的生理性、遺傳性因素,包括性別、性、身體、種族、民族、族裔、年齡等,它們之間的懸殊與抗衡事關文化,又無不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從而成為一種‘文化政治”[1]。而身體話語和文化政治,正是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的兩個關鍵詞,是理解其解構經典美學和重構后現代美學的核心。由此確立了美學的后現代轉向,其中身體話語是宣布經典美學終結的邏輯起點,也是重構一種唯物主義美學的出發點。
由此引出伊格爾頓的第二個目的:重建一種唯物主義美學。重建一種唯物主義美學,其根基非常重要,具體而言就是“審美意識形態的物質基礎是什么?”伊格爾頓的審美意識形態理論正是沿襲了葛蘭西的思想研究路徑,不僅強調在后現代社會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種實踐行為,還為審美意識形態找到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身體。
伊格爾頓擅長在兩種看似毫不相干的范疇中找出關聯,比如在審美與意識形態之間,找到了身體作為二者的關聯;在馬克思主義與神學之間找到了語言作為二者的關聯,但鑒于語言是人的身體在勞動過程中的創造性產物,也就將馬克思主義與神學之間的關聯下移到身體。伊格爾頓最推崇的身體研究著作是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其中有句名言:“世界的問題,可以從身體的問題開始”。現象學最經典的方法是現象學還原,還原事物的本來面貌。這實際上是一種元哲學的思維方式。當世界發展變化日益復雜,當所有的爭論越來越濃烈不可開交,有必要回到源頭反思。因為西方思想的誕生是基于邏輯學的辯證推理,但當“美學事件”“文學事件”發生時,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而反思的過程就是從起點出發。伊格爾頓的思想是建立在他不斷學習、不斷汲取前輩的思想營養的基礎之上的。比如早期20世紀60年代,他深受威廉斯和麥凱布的影響,是在細讀、消化、吸收之后的突破和發展。審美意識形態理論也是如此。正是在《美學意識形態》中,身體的重要作用得以凸顯。
三、身體符號:文化與自然
伊格爾頓對馬克思的身體觀的解讀是建構其身體理論的基石,從早期文本《作為語言的身體》到最近的《論幽默》,伊格爾頓立足于西方文化神學背景之下所展開的文學理論研究,確實可以歸結到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與立場。這是因為立足于自身文化語境進行的對自身的批判唯有借助于“他者”的視角才可以展開。作為世界上對資本主義制度批判得最徹底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對于伊格爾頓而言,顯然是一個可以借助的切入點。
1.身體話語-文化符號
身體話語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含義是宏大的兼容并蓄的,將不同形態的多元文化歸結到一種具有普泛式的物質基礎根基。話語從學理上說是成系統的表達方式,有其特定的內在邏輯,它不同于言語與語言,話語是有一套方法論支撐的文學理論表述體系。身體話語源自尼采與福柯的系譜學,但伊格爾頓的身體話語吸收與借鑒了他們的起源與系譜學式追溯方法卻又有其獨特之處;也不同于莫里斯·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后者在哲學內部將笛卡爾的“意識”起點轉換為“身體-知覺”起點;伊格爾頓從思維方式的角度指出馬克思是“反哲學”的,實踐的,有力量的,而并非只是思想家,是人在思考而非“意識”,此“人”是有身體的,這構成人的思想的前提預設。身體不是對象而是前提,在此基礎上歷史、政治、美學、思想得以展開,而展開的目的在于實踐和變革。伊格爾頓認為馬克思在早期作品中提出的“所謂的人類‘物種存在性”[1]的辯證之處在于:人類的物質機體和生物學事實是超越個性差異的共性。以物種身體為立論的基礎,伊格爾頓將馬克思的歷史、政治的宏大敘事及象征這些秩序的文化符號歸因于身體話語。他的身體理論深受馬克思的影響。
伊格爾頓早期文本《作為語言的身體》顯然是在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尋找一個更為現實與貼切的契合點[2],即人的神性與獸性之間的中間地帶,從倫理—道德角度看是善與惡的分界線,從人的現實性的角度看是身體,而從文化的角度看則是語言。宗教是西方文化的背景,在伊格爾頓的著作《如何讀詩》《如何閱讀文學》《文學事件》《批評家的任務》《陌生人的麻煩:倫理學研究》中將西方社會種種社會問題以“神學-文學符號學”“神學-政治符號學”的形式加以表達,即在西方學界語言學轉向的基礎上對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能指-所指”框架轉換為“身體-語言”。[3]然而,這只是伊格爾頓思想的學理性表達在文學與文化理論的學科范式內所作的探索,但從“政治批評”到“美學意識形態”,伊格爾頓的關注點自始至終都在“文學之外”,且把身體話語作為言說的起點與前提預設。“類”“類本質”“人的本質力量”是馬克思主義探討人類社會問題的人類學根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的身體也一直是人類的沉重的肉身,伊格爾頓將自己的思想寄身于天主教神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之中。
2.身體-語言
若宗教是西方思想家不可脫離的語境的話,那么馬克思主義則是伊格爾頓的主動選擇。在此意義上,伊格爾頓的“身體-語言”不僅指向文學理論也指向了文化理論,既有西方宗教文化的背景,也是伊格爾頓從馬克思身上所發現的哲學人類學,所借鑒的關于人性的唯物主義認識。整體而言,伊格爾頓所追求的是一種更為“基礎存在論”式的現象學還原。他所嘗試的工作是一種更為基礎、更為本質的“還原論”,將宏觀的馬克思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社會理論、微觀的身體-語言的學理性表達通過身體話語-文化符號的中介進行類比,所強調的是文化的唯物主義根基。
伊格爾頓認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不同于啟蒙運動時期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對于馬克思而言,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應該是人類的真實屬性”,“我們首先是一種客觀的、物質的,并且具有形體的存在”。[4]伊格爾頓認為馬克思強調了人類的自主能動性,是能夠創造自身歷史的生物,而馬克思的某些唯物主義觀點源自費爾巴哈。笛卡爾強調“我思故我在”,費爾巴哈卻指出,“是人在思考,而不是自我或者理性”[1]。由此,伊格爾頓提出哲學思考的前提預設:人首先是人,是有身體的物質存在,“我們思考的方式源于我們的動物屬性。我們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延續性,也是因為我們的身體構成和感知這個世界的方式” [2]。意識、精神、頭腦、思想屬于人自身的本質力量,借助語言加以表達與交流,而語言是一種身體活動,身體作為思考的起點,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有身體的參與,在此意義上,實踐變得重要,經濟、生產、勞動最初也不過源于滿足身體的需求。
3.經濟基礎—上層建筑
身體-語言模式將人類歸結于社會主體實踐者,若意識是內在的,語言則是它的外化,而伊格爾頓將身體與語言看成是同一的,且為物質生活形態的“社會存在”,“社會存在決定意識”,“我們的語言植根于我們的行為”。此種還原論得出的結論是:“馬克思聲稱,在人類發展的后期階段,思想逐漸變得愈發獨立于身體的需求,而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文化產生之后,我們才可以因為思想本身的價值而熱愛思想,而不是因為它們可以幫助我們維持生命。”[3]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物質現實高于思想,實則指的是馬克思的基礎與上層建筑學說。伊格爾頓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模型的垂直方向與水平層面兩個維度來思考社會構成,申辯馬克思宏大的社會理論的人性基礎之維正在于身體-語言的微觀類比,也將西方傳統形而上學與美學微縮到身體話語-文化符號的內部肌理,充滿了文化唯物主義色彩。在西方現代性的理性的破碎之后重構一種“整體性”根基,與其說是一種范式,不然說是地基,將理性大廈的海市蜃樓重新接續上人的氣息。那是始源、大道與根基。所以,“在馬克思看來,我們的思想是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形成的,這是由我們的身體需要所決定的物質必需” [4]。
在某種意義上說,伊格爾頓不是一位書齋里的學者,他立身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中剖析西方社會,借用的是馬克思的視角與方法。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世界上對資本主義制度批判得最徹底、最深刻的,這是置身資本主義制度之中批判資本主義的伊格爾頓的獨特視角。西方文化的批判式思維與自省特點,讓西方形而上學從人(古希臘)—神(中世紀)—人(文藝復興)以及感性—理性—知性—感性的循環往復中構建著自己的知識體系與學術話語,既產生了燦若星河的人類文明,也醞釀出兩次世界大戰。2001年“9·11”事件爆發后,伊格爾頓先后出版了《論邪惡》《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2008年華爾街金融風暴之后,伊格爾頓創作了《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此時,與資本主義制度迥異的社會主義制度成為伊格爾頓目光的聚焦點。我們很難說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伊格爾頓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否相同,畢竟,目的、手段、方法、路徑、語境都有差異,但毫無疑問的是,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伊格爾頓對馬克思的守衛與辯護,甚至推崇與贊美是對人類社會共同的關切,對人類自身境遇與命運的關切,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作為文化符號的身體話語。
四、身體詩學:文學與人類命運
身體詩學是介于現實物質世界與形而上學之間的批評理論形態。以身體詩學闡釋伊格爾頓的批評理論思想意在涵蓋他在馬克思主義文論與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之間所做的理論探索、批評實踐和文本創作。筑基于這樣幾個基本觀點:文學的物質性在于文學的語言與形式;文學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文化唯物主義文學學派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為基本原則;革命批評、政治批評、美學意識形態屬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范疇;文學理論廣泛涉及宗教、哲學、美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等范疇,具有文化詩學屬性。承續劍橋大學神學與政治辯論傳統,古希臘雄辯術、修辭學與西方釋經學傳統,伊格爾頓廣泛吸納英國經驗主義思想、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思想、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莫里斯·梅洛-龐蒂身體現象學思想融入其批評理論當中,使其具有審美詩學屬性。但是伊格爾頓的批評理論不是哲學、美學、倫理學、政治學,而是身體詩學,即在西方宗教背景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論的審美詩學與文化詩學的合一。
伊格爾頓的批評理論是隨著時代發展演進的。從馬克思主義形式、后現代主義風格、類比與寓言意蘊、意識形態思想、政治和倫理話語到伊格爾頓批評理論中的“歷史”(美學史、悲劇史、文化史)詩學,可知伊格爾頓的批評理論既囊括審美詩學范疇,又有文化詩學范疇。區別于日常生活話語中的身體,身體詩學中的身體指代人—此在—類—有身體的存在,身體是詩意的不是性別的。身體詩學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統攝下以經濟為基礎的上層建筑文化符號,同史學研究視角的下移一樣,文學研究視角的下移是伊格爾頓批評理論具有身體詩學特征的原因,體現為從宏大敘事到微觀話語,從意識形態的內化作用到日常生活話語實踐,從文學的普遍價值到文化的感性經驗和物質實體。科學、哲學、宗教之間的某個位置屬于詩學。伊格爾頓的身體詩學處于宗教構成的西方歷史文化背景之下,耶穌受難的身體是悲劇的隱喻,是強調耶穌的人性一維的詩意類比。身體詩學因而符合伊格爾頓批評理論中對人的物質性與神性的寓言性質,又包含著他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思考和關切。
五、結語
身體詩學具有存在主義修辭風格,吸納感性經驗現象學的某些因素,加上伊格爾頓散文體論述語言的靈動變幻,都為其批評理論涂抹上詩意棲居的“獨立姿態”。與一般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不同,伊格爾頓縱橫捭闔于文學文本、批評文本與理論文本之間又有其解決現實問題指向,具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的實踐品格又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獨樹一幟的“身體詩學”。既是文化詩學與審美詩學的合一,又是獨創的批評理論形態—散文體批評、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政論文體裁的歷史詩學。如果這個概括還不太準確的話,那是因為特里·伊格爾頓批評理論像一塊“飛地”,自身并沒有成型的理論形態,只有大致的理論框架和研究領地,并且仍然處于變化形成的過程當中。
〔本文系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伊格爾頓身體理論反思研究”(L15BWW013)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李 帥:遼寧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 任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