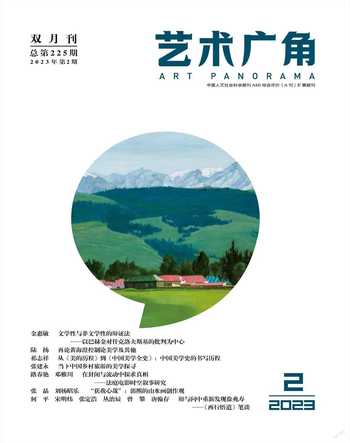《西行悟道》奠定了徐兆壽文化學者的地位
我和徐老師一樣都是西北人,多年在西北。他在蘭州,我也在蘭州,所以我們的聲音里面帶著西北的味道。因為距離比較近,關于徐老師的創作、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一些曲折歷程,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影響,我都是一個見證者。
這本《西行悟道》是徐老師“吾道一以貫之”的新作品。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徐老師的作品,從他青年時代的詩歌,如《那古老大海的浪花》《麥穗之歌》,到一系列小說,包括青春題材的小說,再到后面的文化研究、文化隨筆,乃至今天這本《西行悟道》,里面很多東西在變,徐老師的追思不斷往深處、高處延伸,關注的問題也不斷轉向,但是有的東西沒有變,那就是他對“道”這一終極命題的驚人的持守與探尋。徐老師不同題材的作品或文本,透過對肉身或日常生活的描述,都體現出作者執著的人文關懷和浪漫主義的追思、形而上的追求,有一種巨大的文學與文化的抱負。我記得他曾在一本書的扉頁上寫過一句話“我要重新解釋這個世界”,那時候他年輕敢于這樣說,多少年來他也是這樣做的。這本《西行悟道》又為他的這一句話加上了一個有力的注腳。
《西行悟道》是一本有野心的書。作者西行,是要藉著對昆侖文化與草原文明的重新打量與敘事,擺脫中華文明的中原中心主義,從而尋求建立某種意義上的西部正宗;他念念不舍的“悟道”則是厚古,重溫有功有德的天下道統,并藉西部故事而彰顯天下正主的理想。很明顯,徐老師讀了不少古代典籍,他熟悉西部的上古神話,尊崇孔子所謂的“三代之治”,對《史記》中記載的有關天道隱匿、人道勝出的文字很是上心,對《易經》也頗有研究心得。“天下擁護之圣王,必須要有大功鑄其陽,又要用大德養其陰,失其一,則不能恒久。”“天下的正主絕非血統的繼承,而是道統的承續。”諸如這些觀點,連同作者所贊賞的堯、舜、禹等敬虔時代“真正的民主”,都是作為讀者的我所深以為然的。而孔甲、夏桀、商紂、周幽王的時代,反映的恰好是人的失道與僭越,是人道大于天道、血統大于道統,其結果,必然導致序倫混亂、禮樂崩壞,開啟了后世以陰謀為智慧、以暴力為美學、以斗爭為光榮的歷史周期律。
因此,追尋上古先人們的歷史,尤其是圣王時代的敬虔史,或許就成為后世學者尋脈的依據。中華文明五千年,或許前二千五百年與后二千五百年是完全不一樣的,人們更了解后面的歷史,而對前史相對陌生。《西行悟道》所要揭示的一個隱秘點正在于此。不僅如此,書中也對以中原文明為中心的歷史以及歷史敘事,采取了質疑和補正的態度。“從遠古神話來看,中國最早的文明中心不在中原,而在一個叫昆侖的地方。”昆侖文化作為上古敘事的一個中心,開啟了一個民族地理史、尋根史,與此后的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等一起,形成了早期西部文明的景觀。中原文明是后來的事。中原文明在形成和大一統過程中,逐漸屏蔽了周圍的文明,尤其借助儒家學說和司馬遷的歷史敘述,完成了其正統性與“歷史正義”,從而將周邊的文明敘事邊緣化,“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些邊緣的存在者,在漢語里,就已經被剝奪了某種正當性,失去了某種力量,被迫披上了獸衣樹皮”。書中的這些觀點,通過一個個史料故事,讀來讓人相信,也覺得新奇。在我看來,最引人入勝的是書中的第二輯“草原往事”,作者借題發揮,在《山海經》《史記》等古籍中索隱,展開了草原民族特別是匈奴人的來龍去脈,讀來十分精彩,發人深省。匈奴的祖先叫淳維,本為夏桀之子,夏滅亡,夏桀流放鳴條,他的兒子淳維則帶著夏王朝的遺民逃到了北方草原野地,被后世稱為匈奴。這些“德衰者的后代”與怒觸不周山的共工的后裔共同生活于草原上,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仇敵:中原共主。千年來他們對中原王朝的襲擾、掠奪、占領,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可以看作是復仇之舉,也可以看作是祖先血液中返鄉意識的部落化、民族化的激烈發作,因為他們與三皇五帝建立起來的王朝與文明版圖,本屬一宗。然而,“書寫歷史的人在中原。他是孔子,是司馬遷。他們聽不到那些風中的野蠻詩史。他們只聽到漢字的風聲。”于是乎,在中原文明與漢語歷史之外,邊緣者被遮蔽,邊緣者永遠成為邊緣,無法書寫自己的“歷史正義”。
《西行悟道》給我們的上述讀感,確實是具有震撼力的。盡管從書中很難發現,哪些史料是作者的獨到發現,哪些觀點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作者通過深厚磅礴的敘述,將隱藏多年且閃閃爍爍的歷史事相空前地揭開了,并且駕馭自如,這本身是了不起的。而且,面對歷史,面對文化,徐老師有自己的眼界、胸懷,更有自己的見解與見識。他自己不被遮蔽,反而透露出難能可貴的史識。有史識,方為大氣。一個文化學者的底蘊和眼光,也就由此奠定了。
徐老師以西部為中心,試圖動搖中華文明中原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這一點令人深為贊嘆,沒有相當的文化抱負是不敢談的。本書以西部為支點談中國歷史文化,談道統,談信仰,體現了作者的深層用意。他不僅是要清談,而且是要構建,借助于歷史事相的還原與重組,建構一個認識論的世界。這種建構不僅對于中原中心主義的敘事有補正作用,而且對于歐洲中心主義、科學中心主義的歷史與現實有糾偏作用。實際上,道的終極只有一個,不分東西方,也不天然地導致科學與宗教的對立、天道與人道的對立,然而歷史事實的演變,卻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對立,我相信徐老師在他的書中,藉著談論各種問題,不是要制造新的對立,甚至也不是要制造什么新的中心,他或許是要消弭各種對立,統合各種中心,達于終極意義上的和諧歸一。
徐老師對西部這個地域性的對象做開闊高深的文化探尋,與他自己身在西部、對西部懷有深厚的情感有關,同時也可能與這些無關,只與西部本身的文化密碼有關,只與西部的重要性有關。這種密碼與重要性,可能不僅僅指自然地理,不僅僅指歷史、文化,可能指向根本性的所在,因此才有人說,他是要藉著此書,為民族文化尋找一個“托命之地”。
西部需要被重塑,并且需要進一步重塑。我們都知道新時期以來,或者再往前推移,有“西北文學”“西部文學”的說法,這種說法與西部被重新塑造、被重新發現、被重新標識有關。近代以來西部的那些探險家、學者、文人、考古學家、新聞記者等從亞洲的中部、西部,乃至到中國的西部進行探險考察產生的那么多文獻,很多已經發表,結集成書出版,都是對西部的一次次重塑。在21世紀,認知和思考西部需要一個新的起點。徐老師的這本文化隨筆就是一個新的典范,是新時代重新思考西部文化的新起點。這本書在他的創作和學術生涯中,或許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最后,引用一句阿多尼斯的話,談到中心和邊緣的問題,他說:“什么是中心?中心就是一切邊緣的邊緣。”我本人在一次節目中說:“地球是圓的,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作者簡介】
何 平: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宋明煒:美國韋爾斯利學院東亞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定浩:詩人,評論家,《上海文化》副主編。
叢治辰: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三屆客座研究員、特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
曾 攀:《南方文壇》雜志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
唐翰存:蘭州交通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
(責任編輯 牛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