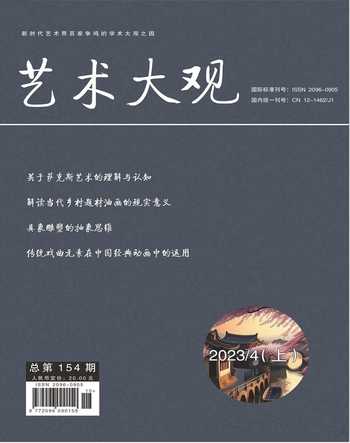《峨眉山月歌》的音樂特征與演唱探究
摘 要:《峨眉山月歌》是眾多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中的經典之作。歌曲打破傳統,采用非方整性曲式結構,通過在鋼琴伴奏中植入固定音型結構,借鑒節奏序列技法,依詩寫曲、依詞行曲,詞曲交融、相得益彰,既融入個人寫作特色又保護了古典詩詞應有的韻味。演唱這類音樂與內容皆有一定深度的作品,需要演唱者了解詩詞的內涵,了解詩詞的平仄、轍韻、節奏、聲調,配合靈活的呼吸支撐,才能做到詩樂一體,完成對音樂形象的準確塑造。
關鍵詞:古詩詞藝術歌曲;《峨眉山月歌》;音樂特征
中圖分類號:J6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10-00-03
一、《峨眉山月歌》作品概述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時期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有著“詩仙”的盛譽。李白長于蜀地,少時廣學博覽,詩賦多首。他一生輾轉,閑時吟詩飲酒、習劍修道,又四處求索、建功若渴,放蕩不羈的外像下又希望成為一代賢臣,為官獻世。
《峨眉山月歌》約作于公元724年秋(開元十二年),于逾弱冠之年自水路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游”(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此詩清雅婉轉,神韻十足,被稱為“千秋絕調”[1],蜀江秋色被描繪得靈動至極。
全詩釋義為:秋夜里,幽靜的峨眉山高聳入云,隱隱地探出一彎弦月;月影映入了平羌江的水流中,在滾滾漣漪中波光浮影。半夜時,順著水路乘船從清溪驛直奔三峽;在去往渝州的路途中抑不住心中的思念。詩中抒發了詩人離鄉的愁緒,又將行船之途寫得輕快昂然,可以看出詩人此時是愁情與激情相融的。
二、《峨眉山月歌》的音樂特征分析
(一)曲式與和聲結構
《峨眉山月歌》為單一部曲式,采用非方整性曲式結構,速度標記為慢板(Lento)。引子部分(第1-5小節)調性為d小調,伴奏部分創新性地使用興德米特作曲理論的和聲連接方法,并與中國民族調式相融合。引子部分開始,左手的伴奏從F宮系統的D羽音切入固定音型,右手出現了興德米特和聲理論A類和弦中的Ⅲ組和弦和Ⅴ組和弦。興德米特把全部和弦分為不包含有三全音的A類與包含有三全音的B類之后,又根據其他因素再將全部和弦分為六個組[2]。
A樂段(第6-20小節)共分為了三個樂句。a樂句(第6-12小節)在第10小節處出現了調性的轉換,進入了G大調,又在b樂句(第13-16小節)的開頭回歸到d小調,但旋律走向則不大相同,最后又在a樂句(第17-20小節)出現了轉調傾向。
尾聲部分(第21-25小節)調性為?B調,左手和弦在A類和弦中的Ⅰ1、Ⅰ2、Ⅲ2三組和弦上交替使用,結束在了Ⅰ2和弦上,最后的旋律高音和伴奏高音都落在了?B音上。
(二)詞曲交融的旋律
筆者建議演唱者從詩詞格律和平仄關系入手,以現代標準漢語的讀音對全詩進行吟誦,切實地感受《峨眉山月歌》的格律、節奏、聲調等,再代入旋律演唱。長短相間的句式和字音的平仄韻律與音樂的旋律、節奏相呼應,這些都是古詩詞藝術歌曲音樂創作的依據[3]。
峨眉/山月/半輪秋,(平平平仄仄平平)
影入/平羌/江水流。(仄仄平平平仄平)
夜發/清溪/向三峽,(仄仄平平仄平仄)
思君/不見/下渝州。(平平平仄仄平平)
全曲的小三度音程使用較多,如“峨眉”“山月”“江水”“渝州”,其音響黯淡柔和,略帶憂傷,把握住音準,也就能把握住《峨眉山月歌》中的點點鄉愁。“峨眉”“清溪”“思君”等平聲詞,在旋律上都用了簡潔的音程變化和節奏來表達,避免復雜的裝飾音和音程變化讓平聲字的聲調改變,產生聽覺誤差。
旋律的波動起伏也與歌詞相關聯。“峨眉山月”高聳入云,此句的音高也逐步上行,以弱貼合夜的幽靜,為了突出山的巍峨,力度也從弱逐漸推起。月影潛入江流,“影入平羌”級進的音程仿佛影面拉長。“江水流”的旋律最具韻味,十六分音符和三連音相配合,如舟行泛起的水波。一路浩氣“向三峽”,勁拋群山,三峽的險峻激起了詩人想探遍祖國大好山河的萬丈豪情。“思君不見”是詩人的核心情感所在,也是全曲力度最強之處,思鄉、思人亦思前途。力度減弱、旋律下行,漸漸又回到“下渝州”的現實中。
全曲旋律線條清晰,中國傳統風格依字行曲被體現得淋漓盡致。羅忠镕通過此方法有機地把旋律與唱詞結合,從而更生動形象地刻畫歌曲中的景象與情感,也使得詞曲高度融合[4]。
(三)鋼琴伴奏分析
鋼琴伴奏有著羅忠镕開拓創新的巧思,羅先生在鋼琴伴奏中植入了固定音型結構,從左手開始又在尾聲處漸漸移到右手。這樣的固定音型通過連線(Legato)的承接一共組合了十九次,F宮系統內的D羽音(五次)、G商音(四次)、C徵音(兩次)、F宮音(兩次)、A角音(兩次),?B宮系統的F徵音(三次)、C商(一次),最后落到?B宮系統的主音上。這樣的固定音型從各個主音切入,十個十六分音符為一組,以這樣的模式發展并貫穿全曲,好似“向三峽”“下渝州”的渺渺水路。
從右手和弦來看,羅先生借鑒了阿爾班·貝爾格的弦樂四重奏作品《抒情組曲》中的節奏序列技法,以每四個和弦為一組序列,全曲共出現十次[5]。這種和弦組的特點是節奏依次遞減/遞增后延長(該譜例為遞減后延長),表現為四分附點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二分音符的拼接組合。它們相互呼應,固定音型似滾滾向前的平羌江水,變化的和弦仿佛舟下的漣漪散開,又似夜半的鐘聲、鳥鳴、弦月。鋼琴鋪墊著李白月影江舟的行路遠景,人聲旋律則表達了李白離鄉求志,思鄉滿懷的心情。
三、《峨眉山月歌》的演唱分析
(一)氣息強弱的控制
唐代音樂家段安節在其所著的《樂府雜錄》中留下一段傳用千年之語,其載:“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云響谷之妙也。”[6]中國聲樂演唱通常采用胸腹式聯合呼吸法,胸腹式呼吸能讓聲音更加飽滿、立體,它不僅要求氣息進入胸腔,內化用于“臍間”,還要求腹肌和橫膈肌力量的協調使用,一些字詞、句讀的處理也依靠氣息的支持。
首聯“峨眉”兩字應作輕聲高位,緩緩漸強;在“山”字上送氣;“半”字可用氣息強調雙唇音“b”,形成一個爆破音的效果,加強氣韻并貼合漸強的力度記號;“輪”的拼讀由邊音到鼻韻母,切莫全部歸于鼻腔之中。頷聯的“影入平羌”應注意胸腔位置,起音飽滿不虛,氣息下嘆,尋找兩肋擴張感覺,“水”和“流”這兩個字的韻母要用氣息包裹住,仿佛氣息是一條小舟,而兩肋、橫膈肌和腰背肌肉是寬廣的平羌江面,氣息穩穩地在江中緩行。
在弱起節奏后,頸聯需要用到兩次“快吸慢用”,即快且深地吸氣并均勻地使用。第一次,“夜發清溪”的“夜”字要在快吸氣后發得不突兀,保持小腹的緊張。第二次在“向三峽”前,為保證高音的完美,可設計一個氣口。此三字應注意氣息的飽滿度和力度控制,都要緊密地與橫膈肌推動做好配合。尾聯是氣息使用的高潮,“思君”二字要保持氣息支撐,腰背肌肉將橫膈膜和兩肋擴張,以保證兩字不扁不擠卡;“不見”到“下渝州”有一個氣息下嘆的過程,送氣中要哼住高位置并過渡到較弱的音量,營造出半夜水路行舟的幽靜。
(二)咬字中的轍與韻
中國聲樂傳承著我國傳統的聲樂美學,其中有一精妙之點,即“字正腔圓”,它也廣泛地運用在中國聲樂演唱的咬字當中,談及漢字的咬字、吐字,便不得不提到“十三轍”。“十三轍”講求的是字的拼合,在不同的速度、力度要求下,字的拼合速度有著細微的差別。這無處不在的細微差別,決定了民族聲樂演唱韻味的有無[7]。
全詩二十八個字,有言前轍四,由求轍、中東轍、姑蘇轍、江陽轍、發花轍各三,梭波轍、灰堆轍、人辰轍、衣齊轍各二,乜斜轍一。《峨眉山月歌》的韻腳為下平聲十一尤韻,此韻以悠長之感為其特點,表現出悠遠、婉柔、幽雋之意。全曲節奏比較簡單,所以在咬字歸韻時不能緩慢拖沓,先要做到“字正腔圓”才能實現“聲情并茂”。
首聯,應注意“山”字的舌尖后音強調,軟腭的力量要將韻母立住;撮口“月”為入聲字,可適當添加一個裝飾音的潤腔。頷聯中的“羌”“江”都是三拼音節的江陽轍,“羌”的時值較短要注意歸韻速度,“江”字可在附點節奏中有較清晰的歸韻;“水”字的處理是作曲家以旋律表達詩人在水路上行駛的妙筆,演唱者需在前十六分音符中完成拼讀,并在三連音中咬住韻母“ui”行腔。
頸聯中的“向”在韻母上打開通道;“三”的舌尖前音“s”應有清晰的字頭;“峽”字需注意聲母、介母、韻母的拼合速度,強調字頭后快速行腔到韻母“a”,將力度和情緒推起。尾聯“思君”的韻母“i”和“un”用高位置哼住,且二字皆為陰平聲調要避免滑音。
全曲意韻之重是“秋”“流”“州”三字,它們都是下平聲十一尤韻的代表字,都在復韻母“ou”上完成歸韻,雖都有著弱或減弱的表情標記,但需大膽咬字,仿古琴“吟”“猱”之技寓于演唱之中,在長音上做出音腔的“搖聲”,塑造秋月之高、江流緩緩、輕舟行遠的形象,將意境表達完整。
(三)音樂形象定位與情感把握
《峨眉山月歌》是一首具有流動、遷移,又因著“不見”所思,而有生命缺憾內涵的佳作[8]。從詩詞與音樂中我們能感受到:前兩句交代了時間、地點和環境,旋律平緩,意境清遠,含蓄地訴說著蜀地的秋夜江景,為全詩的氛圍作渲染;后兩句漸漸托出了“人”的身影,在昂揚的高音上把“思念”傾吐無遺,情感是傾瀉的、激昂的,又在爆發后漸漸收回,略帶悠揚、輕巧之意。
從音樂形象上講,它塑造了一個意氣風發的離鄉青年形象,在鄉愁與仕情間矛盾,懷天下之志而離家遠游。不少聲樂演唱者在歌唱中著力表現“懷愁者”的形象,其實不然,李白此時年少英姿、壯志凌云,他對此行心生愉快,對實現理想抱負充滿信心。
李白在開元十五年初游湖北安陸時,曾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寫下:“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正如他自稱為“青蓮居士”一樣,李白有著一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優秀品質[9]。由此可見,《峨眉山月歌》的情緒是向上的,輕狂驕逸的少年李白懷揣著宏圖大志,他的志向如大鵬一般“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李白《大鵬賦》),并非滿懷愁緒。若論愁,筆者認為有兩種:鄉愁和仕愁,鄉愁源于他年少離家、不知前路又難見歸途;仕愁源于他一生都在“干謁求途”,他因身份而無法參與科舉,唯有求人引薦,但這些都未曾消磨他的愛國情懷和政治熱情。
所以演唱者在塑造音樂形象和把握情感時,是略帶愁思但鵬志不衰的。應化為詩人,擬態一位思念故鄉,但卻渴望得到賞識,能夠從政濟世的游子,對施展才干以安定社稷充滿憧憬,體會“酒入豪腸,釀月嘯劍”的氣概。
四、結束語
古詩詞是中華古典文化的瑰寶,是“取之有韻,用之有味”的寶庫,羅忠镕先生結合中國與西方的作曲技法,精妙地使用在古詩詞歌曲當中,《峨眉山月歌》音區不寬,如此精悍短小的一首歌曲,蘊含了極高的藝術內涵和理論價值。
在創作古詩詞藝術歌曲前,需結合古人的詩興詩意進行分析,其古典意韻和轍韻聲腔需要一字一字地推敲。如今的古詩詞創作歌曲泉涌而出,依詞譜曲的同時,需辨析旋律、節奏是否貼合詩文本身的情感與格律,演唱者不僅要尊重現代作曲家的理論技法,也需注意對原詩的理解和音樂塑造。中華詩與樂同宗同源,詩樂本為一體,切不可重樂而輕詩,為體現樂與聲的境界而忽視了詩詞的寫意,既要演繹專業的聲樂演唱,也要竭力實現古詩詞歌曲的藝術追求。
參考文獻:
[1][明]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M].
[2]于蘇賢.論興德米特的作曲理論體系(上)[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1(02):17-27.
[3]彭芳.古詩詞藝術歌曲吟誦風格探究[D].湖南師范大學,2017.
[4]王帥.羅忠镕《峨眉山月歌》的音樂特征與演唱技巧[D].湖南科技大學,2020.
[5]王丹.羅忠镕《峨眉山月歌》的分析與研究[J].中國音樂,2010(03):94-100.
[6]唐·段安節.樂府雜錄[M].
[7]楊麗.論中國民族聲樂演唱中的“十三轍”[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7(03):146-153.
[8]王隆升.論李白渝州詩《峨眉山月歌》的生命情調[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4,28(12):27-32+47.
[9]曹化根.李白的明月世界[C]//.中國李白研究(2001-2002年集)——紀念李白誕生13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315-327.
作者簡介:陳繼陽(2002-),男,重慶人,本科,從事古詩詞藝術歌曲演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