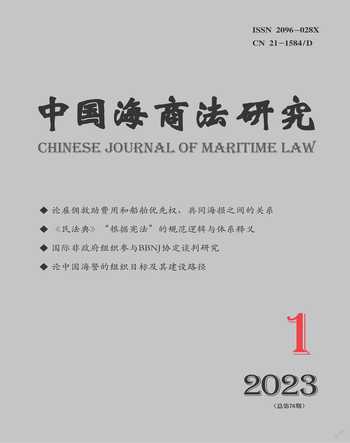論對外資企業約定境外機構仲裁的司法監督
孔金萍
摘要:中國司法實務通常以授權性條款為由限制外資企業將境內爭議提交境外機構仲裁,除非雙方都是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上述限制存在如下問題:首先,不能徹底落實,反而導致仲裁協議效力不可預見,而且,即使適用上述限制,保護的也是違反仲裁協議的當事人。其次,仲裁協議是私法協議,中國卻對其錯誤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再次,外資企業約定提交境外機構仲裁的仲裁協議是否具有涉外性的認定結果與適用程序之間存在矛盾,比如個案中雖然認定不具有涉外因素,但程序上卻適用當時只有涉外案件才能適用的內部申報程序。考慮到法理上仲裁協議是私法協議,且當事人對可以仲裁的事項享有處分權,而《民法典》已經確立了“法無禁止即自由”原則,以及世界范圍內盡量認可仲裁協議效力的國際商事仲裁趨勢,應當認可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也可借鑒《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及新加坡等國做法,明確認可約定提交境外機構仲裁的情形構成涉外因素。
關鍵詞:仲裁協議;法無禁止即自由;外資;境外仲裁機構仲裁;涉外因素
中圖分類號:D925.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23)01-0092-10
A Study on the Judicial Supervision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rbitration
Agreement to Arbitrate by Foreign Institutions
KONG Jinping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Judicial practice in China usually restricts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from submitting domestic disputes to overseas institutions for arbitration on the grounds of authorization clauses, unless both parties are wholly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in pilot free trade zones. The above-mentioned restrictions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irstly, not only do they fail to be fully implemented, but on the contrary, the validity of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unpredictable. And even if the above restrictions are applied, the parties who violate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are protected. Secondly, the principle of “absence of legal authorization is prohibited” is applied incorrectly,although arbitration agreements are private agreements. Thirdly,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such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foreign-related and the applicable procedures. For example, although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re is no foreign-related factor in a case, the internal declaration procedure that is only applicable to foreign-related cases at that time was applied procedurally. In view of the legal principle that the parties have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the matters that can be arbitrated, and the principle of “absence of? legal prohibition means freedom”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Civil Code, as well as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which the effectiveness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s is recognized as much as possible in the world,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arbitration agreements should be recognized. We can also learn from th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Singapore etc., clearly recognize that the situation of agreeing arbitration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by overseas institutions constitutes a foreign-related factor.
Key words:arbitration agreement; absence of? legal prohibition means freedom; foreign investment; arbitrated by overseas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foreign-related factors
司法對仲裁的監督一般包括對仲裁協議的監督和對仲裁裁決的監督。中國對境內仲裁與涉外仲裁適用不同的監督制度:一是仲裁機構方面,境內爭議不能選擇境外仲裁機構,只能選擇中國的仲裁機構;而涉外爭議則可以選擇境外仲裁機構。二是仲裁地方面,境內爭議的仲裁地必須在境內,不能在境外;而涉外爭議的仲裁地則可以在境外。三是法律適用方面,境內爭議不能適用境外法律,只能適用中國法律;而涉外爭議則可以選擇適用境外法律。此外,涉外爭議未約定仲裁協議的準據法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仲裁司法審查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4條,應盡可能適用讓仲裁協議有效的仲裁機構所在地或仲裁地的法律。僅在沒有約定仲裁機構和仲裁地時,作為最后的選擇才適用中國法律。而境內爭議則只能適用中國仲裁法。總體而言,相較于境內爭議,中國法律賦予涉外爭議以更多的選擇權,更傾向于認可其仲裁協議的效力;而境內爭議仲裁協議的有效要件則較為嚴苛。
近年來,隨著仲裁的不斷推廣以及對中國司法環境的擔憂,外資企業約定境外仲裁機構仲裁的案件越來越多,其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4年公布的參閱案例——“北京朝來新生體育休閑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簡稱“朝來新生案”)中,雙方當事人均為在中國成立的公司,且其中一方是外商獨資公司,本案中當事人約定發生糾紛時提交大韓商事仲裁院仲裁。糾紛發生后,雙方如約仲裁并取得仲裁裁決,然后向中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最終被中國法院以仲裁協議無效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參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特字第10670號民事裁定書,該案為2014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選出的第14號參閱案例。】本案引發了法律界對外資企業可否約定境外仲裁機構仲裁這一問題的熱議。
那么對于“朝來新生案”式的案件,即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是依據中國法律在中國注冊成立的外資企業,且主體之外不存在涉外因素,雙方當事人約定發生糾紛時提交境外仲裁機構在中國境內或境外仲裁時,應當如何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
實務中,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時,中國法院首先會審查爭議是否具有涉外因素,然后再根據爭議是境內爭議還是涉外爭議適用不同的準據法審理。對于依據中國法律在中國成立的外資企業,法院認為外資本身不構成涉外因素,除非雙方當事人都是在自由貿易區內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見》(簡稱《自貿區司法保障意見》)第9條第1款,雙方企業均是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注冊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構成涉外因素,可將其間的商事爭議提交境外機構仲裁。
中國對該類仲裁協議的司法監督存在的三大問題如下。
一、仲裁協議的效力不可預見
即使對于同一仲裁協議,因當事人的態度以及申請確認協議效力的階段不同而適用不同的準據法,導致最終效力可能不同,也即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不可預見。
第一種情形:當事人自覺履行仲裁協議和仲裁裁決,仲裁協議最終有效。當事人簽署該類仲裁協議后,本著誠實信用原則,自覺履行仲裁協議和仲裁裁決。這種情況下,法律沒有機會干預,相當于該類仲裁協議有效。
第二種情形:仲裁程序啟動前,一方當事人申請中國法院確認該類仲裁協議效力的,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簡稱《仲裁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簡稱《民法典》)等法律及司法解釋都未明確禁止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但中國法院卻一貫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無效。200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發布的《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實務問題解答(一)》第83條規范的重點也是不允許將境內爭議提交境外機構仲裁。在“江蘇航天萬源風電設備制造有限公司訴艾爾姆風能葉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案”(簡稱“江蘇萬源案”)中,當事人雙方均為在中國成立的企業,其中一方具有外資背景。當事人約定發生糾紛時提交國際商會在北京進行仲裁,2011年當事人向法院提交申請要求確認本案仲裁協議無效,受案法院以爭議不具有涉外因素、中國法律沒有授權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為由,認定本案仲裁協議無效。【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江蘇航天萬源風電設備制造有限公司與艾爾姆風能葉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糾紛一案的請示的復函》(簡稱《“江蘇萬源案”復函》)。】2017年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以及2020年《民法典》頒布以后,司法實務中的慣例仍然是以中國法律并未規定當事人可以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為由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無效。【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1)滬01民終5762號民事裁定書、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1)津01民特11號民事裁定書、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蘇05民轄終797號民事裁定書、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9)滬民轄終199號民事裁定書、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8)滬民申921號民事裁定書。這些案例均是在仲裁裁決作出前申請確認仲裁協議的效力,且其中僅有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1)滬01民終5762號民事裁定書顯示一審法院認定該類仲裁協議有效,但被二審法院推翻,其余案例中一、二審法院均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無效。在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3民特54號民事裁定書中,兩個中國法人約定發生爭議時提交給新加坡調解中心和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以待調解仲裁。這個仲裁協議歷經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均被認定為有效,理由是申請人未能證明本案不具有涉外因素。】2021年,在“宜昌天美國際化妝品有限公司與梧鈞機械(上海)有限公司承攬合同糾紛案”中,雙方當事人均為在中國成立的企業,約定發生糾紛時,按照《國際商會調解與仲裁規則》在巴黎仲裁。一、二審法院均認為,根據該約定能夠確定因涉案合同履行產生的爭議應由位于巴黎的國際商會仲裁院進行仲裁,但一審法院認定該仲裁協議有效,二審法院則認為該仲裁協議無效,理由是“雙方當事人均為中國法人,本案亦無其他涉外因素,本案所涉合同不屬于涉外合同。由于仲裁管轄權系法律授予的權力,而中國法律沒有規定當事人可以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交由境外仲裁機構仲裁”。【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1)滬01民終5762號民事裁定書。】同年,在“天津市垃圾分類處理中心、天津大馬南方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案”中,被申請人天津大馬南方環保有限公司系在中國成立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雙方在合同中約定“雙方無法通過協商解決該爭議,則任何另一方均可將該爭議提交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仲裁”。本案仲裁協議也被中國法院認定無效。【參見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1)津01民特11號民事裁定書。】易言之,時至今日,中國的司法慣例依然是仲裁程序前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無效。【需要注意的是,在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終3818號民事裁定書中,雙方當事人并未就仲裁協議效力產生分歧,中國法院認為雙方當事人約定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交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仲裁協議有效。】
第三種情形,同時啟動仲裁程序和訴訟程序。中國法院認定仲裁協議無效后作出判決,境外仲裁機構認定仲裁協議有效并作出仲裁裁決。一方當事人到中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另一方當事人到外國去申請承認和執行中國判決。雖然未能搜集到此種情形下有關該類仲裁協議的案件,但以下兩個案件可資借鑒:第一個案件是“海慕法姆公司、瑪格國際貿易公司、蘇拉么媒體有限公司申請承認與執行國際商會仲裁院作出的仲裁裁決案”。該案中,對于仲裁協議的效力,國際商會仲裁院和中國法院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斷,并分別作出了仲裁裁決和訴訟判決。當事人申請中國法院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中國法院以仲裁范圍超出仲裁協議、裁決事項不可仲裁、承認和執行該裁決違反公共政策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不予承認和執行國際商會仲裁院仲裁裁決的請示的復函》。本案中,三家外國公司與一家中國公司簽訂合資合同,約定成立一家合資公司,并約定爭議提交巴黎國際商會仲裁委員會仲裁解決。后來中國公司多次起訴合資公司支付租金等,三家外國公司提出管轄異議,中國法院以仲裁協議對合資公司不具有約束力為由駁回管轄異議并多次作出判決。在訴訟過程中,三家外國公司申請仲裁,請求認定中國公司違反合同義務等。仲裁庭最終支持了申請人的大部分仲裁請求。】第二個案例是國際海上運輸案件——The “Joanna V”案。【(2003)2 Lloyds Rep 617.】該案為國際海上運輸合同糾紛,中國法院認定本案仲裁協議無效并作出判決,而巴黎國際商會仲裁委員會認定本案仲裁協議有效并作出仲裁裁決。仲裁裁決早于中國法院判決作出且結果不同,最終英國法院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后以“一事不再理”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中國法院判決。【參見楊良宜、莫世杰、楊大明:《仲裁法:從開庭審理到裁決書的作出與執行》,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54-655頁。】
中國與同屬《紐約公約》成員國的其他國家對同一仲裁協議效力認定結果的不同會導致仲裁協議的效力不可預見,不僅會引誘當事人啟動兩個程序解決同一糾紛,而且容易產生矛盾判決,因仲裁裁決一般會先于法院判決作出,最終中國法院判決很難在境外獲得承認與執行。而因為經常被選為仲裁地的國家一般認可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所以該仲裁裁決即使不能在中國獲得承認和執行,也可以在其他國家獲得承認和執行。
第四種情形:仲裁裁決在境外作出后,一方當事人到中國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時,另一方當事人以仲裁協議無效為由請求不予執行的,應當根據《紐約公約》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但在2018年以前的多起案例中,中國法院卻適用中國法律認定仲裁協議無效。例如,在“朝來新生案”中,大韓商事仲裁院作出仲裁裁決后,一方當事人申請中國法院承認和執行,該案經內部上報程序上報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終被拒絕承認和執行,理由主要為以下兩點:第一,本案無論當事人是否作出明示約定,該合同以及所包含的仲裁條款所適用的法律均為中國法律。第二,因中國法律沒有授權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交由境外仲裁機構仲裁,【2021年以前,司法實務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無效的依據主要是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簡稱《合同法》)第128條第2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簡稱《民事訴訟法》)(2012年)第271條,即《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78條。因為原《合同法》已經被廢止,且《民法典》刪除了原《合同法》第128條第2款,所以下面討論該類仲裁協議無效的法律依據時僅提及《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78條。】且本案不具有涉外因素,因此本案仲裁協議無效。【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北京朝來新生體育休閑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大韓商事仲裁院作出的第12113-0011號、第12112-0012號仲裁裁決案件請示的復函》(簡稱《“朝來新生案”復函》)。】同樣,在“西門子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與上海黃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請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簡稱“西門子案”)【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一中民認(外仲)字第2號民事裁定書。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均為在中國上海自貿區內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2005年雙方簽訂了有關高(低)壓配電系統供應工程的合同,合同中約定:合同爭議須提交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進行仲裁解決;實體爭議應適用中國法律。后來履約過程中發生爭議,黃金置地公司申請仲裁,西門子公司提出管轄異議,被駁回后提出了反請求。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作出仲裁裁決,駁回了黃金置地公司的各項請求,支持了西門子公司的各項反請求。在仲裁裁決作出后到中國申請承認和執行時,黃金置地公司以本案不具有涉外因素因而仲裁協議無效為由主張應當拒絕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中,也是在執行階段適用中國法律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
“朝來新生案”和“西門子案”判斷仲裁協議適用的準據法是錯誤的:因為中國是《紐約公約》成員國,且《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67條已經明確規定國際條約高于國內法的原則,所以在申請承認和執行境外仲裁裁決階段,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應當依據《紐約公約》而非中國法律。根據《紐約公約》第5條,如果當事人沒有明確約定仲裁協議的準據法,則應依據裁決地所在國法律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而依據韓國法,“朝來新生案”中的仲裁協議有效;依據新加坡法,“西門子案”中的仲裁協議亦有效。此外,根據《紐約公約》第5條第2款,以被申請執行地國法律規定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存在一個通道,即依據該國法律爭議不可仲裁或者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違反該國公共政策。對此,《“朝來新生案”復函》認為承認和執行該案仲裁裁決不違反公共政策。因而中國法院本應認定“朝來新生案”中的仲裁協議有效,但實際上卻錯誤適用中國法律認定仲裁協議無效。但這一錯誤已經在2018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仲裁司法審查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獲得糾正,其第16條明確規定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階段應當依據《紐約公約》第5條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但是實務中在仲裁程序啟動前確認該類仲裁協議效力的,依然被認定為無效。
綜上所述,中國限制將境內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的做法導致仲裁協議的效力不可預見,亦即,即使對于同一仲裁協議,不同階段申請確認協議效力,結果也可能不同。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中國法律對仲裁協議效力的監督與《紐約公約》不一致。而且,這種限制僅能在上述第二種情形下適用,適用的結果也是保護了違約方。另外,這一限制導致仲裁協議不可預見可能會引誘當事人對同一爭議啟動訴訟和仲裁兩種程序,這樣不僅浪費司法資源,而且容易導致矛盾判決。
二、對屬于私法協議的仲裁協議錯誤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
(一)仲裁協議是私法協議
對于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仲裁法》沒有明確規定,如何判斷關系到仲裁協議的性質。有關仲裁協議的性質,有程序法契約說、實體法契約說、混合型契約說與獨立型契約說四種學說。部分學者認為仲裁協議是實體法契約,理由是仲裁協議更多地受制于民商事實體法,而非程序法;契約的法律性質不應取決于契約的內容,而應取決于契約的形成條件和約束效力。【參見譚兵主編:《中國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頁。】多數學者認為仲裁協議是程序法契約,理由是其調整的不是當事人之間的實體權利義務關系,而是是否排除訴訟管轄權這一程序問題。【參見侯登華:《仲裁協議法律制度研究——意思自治視野下當事人權利程序保障》,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第69、74-75頁;江偉主編:《仲裁法》(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頁。】而傳統觀點多認為程序法是公法,因而作為程序法協議的仲裁協議是公法協議。【參見陳桂明:《程序理念與程序規則》,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3頁;張凌、李嬋媛:《公法契約觀視野下的刑事和解協議》,載《政法論壇》2008年第6期,第34頁。】混合型契約說是一種折中的觀點,認為仲裁協議同時兼具實體法契約和程序法契約的性質,在有些方面受實體法規范,例如,協議的成立、效力等;在另一些方面則受程序法的約束,例如,仲裁協議排除法院對仲裁事項的管轄權問題等。獨立類型契約說從仲裁自治理論出發,認為仲裁協議既不同于實體法契約,也不同于程序法契約,而是在實踐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的特殊類型契約,它兼具實體法契約和程序法契約的性質。【參見江偉主編:《仲裁法》(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頁。】
需要注意的是,實體法契約說認為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應當依據實體法;混合型契約說也認為仲裁協議的成立和效力應當受實體法規范。學界多主張仲裁協議是程序法契約,而傳統上又習慣將某一部門法整體定性為公法或私法,比如認定程序法是公法,因而程序法協議也是公法協議。但這種認定存在邏輯上的問題,因為一個法律部門所規范的法律關系性質可能并不單一,有的既涉及公法關系,也涉及私法關系。有鑒于此,不宜將某一法律部門整體定性為公法或私法,只宜將其中的具體條文所規范的法律關系定性為公法關系或私法關系。【參見王涌:《私權的分析與建構:民法的分析法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53頁。】
公法與私法區分學說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說是主體說、服從說、強行法說和利益說。主體說認為劃分的標準是是否有代表國家或某種公共權力的主體存在,如果有,則是公法關系;如果沒有,則是私法關系。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即持有主體說的觀點。【參見[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4頁。】服從說也稱實質說,其認為劃分的標準在于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如果處于對等關系則屬于私法,如果處于上下服從關系則屬于公法。強行法說則認為區分的標準在于法律是否允許當事人協議改變,如果不允許則是公法;如果允許,則是私法。利益說也稱目的說,其認為劃分的標準是法律的實質內容或目的。現代利益說則認為,旨在維護公共利益的法律屬于公法,旨在維護私人利益的法律屬于私法,而且這兩種不同目的可以從法律規則的內容中加以識別。【參見沈宗靈:《比較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頁。】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公法契約也并非法律無明文規定就不得有效成立,【參見[日]田中二郎:《公法契約的可能性》,肖軍譯,載《行政法學研究》2002年第1期,第81頁。】比如,涉及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行政契約,一般認為對于其合法要件、瑕疵形態、履行終止的判斷,除了有行政法上的特別規定和法律原則須遵守之外,可以準用民法上關于契約行為的一般規定。【參見陳新民:《中國行政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186頁。】考慮到仲裁協議的主體一般是企業,且雙方當事人處于對等關系,仲裁協議的內容也是雙方自由擬定的,旨在維護雙方當事人通過仲裁解決糾紛的利益,根據主體說、服從說、強行法說和利益說,仲裁協議都屬于私法協議。且實體法領域的契約自由理念是仲裁制度得以產生的重要理論依據,仲裁協議和合同都是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理論下的產物,中國也曾以合同法條款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中國法院以原《合同法》第128條規定的“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根據仲裁協議向中國仲裁機構或者其他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為由認定仲裁協議無效。】英國有關仲裁條款效力的判斷適用的也是合同解釋的規則,【參見楊良宜、莫世杰、楊大明:《仲裁法——從1996年英國仲裁法到國際商務仲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5-73頁。】這些也都符合仲裁協議是私法協議的屬性。
(二)對于仲裁協議錯誤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
司法實務中對于“朝來新生案”等適用中國法律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無效的依據是原《合同法》第128條第2款和《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78條。原《合同法》第128條第2款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根據仲裁協議向中國仲裁機構或者其他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78條也僅規定“涉外經濟貿易、運輸和海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在合同中訂有仲裁條款或者事后達成書面仲裁協議,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或者其他仲裁機構仲裁的,當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訴”。依據這兩個條款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無效適用的是授權性思維,亦即“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此外,司法慣例否認該類仲裁協議效力的主要理由是認為仲裁權是準司法權,認定該類仲裁協議有效會損害中國的司法主權,故應當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參見張珍星:《無涉外因素糾紛約定外國仲裁協議無效的司法慣例剖析》,載《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第124頁。】然而對于仲裁協議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是錯誤的做法,理由如下。
首先,如上所述,仲裁協議是私法協議,適用中國法律判斷仲裁協議效力時,對于《仲裁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形,應當適用《民法典》。而《民法典》已經舍棄了授權性思維,確立了“法無禁止即自由”原則。
作為判斷仲裁協議無效的原《合同法》第128條第2款和《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78條最早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原《合同法》制定于1999年,《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78條源于《民事訴訟法》(1991年)第257條。】那時還盛行“行使權利需要獲得授權”的理念,故可以認為當時涉外爭議可以“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仲裁機構或其他仲裁機構仲裁”本身暗含著境內爭議不得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之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立法思維都是“權利需要授予”。比如,20世紀80年代制定的原《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稱《民法通則》)第55條【原《民法通則》第55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從積極肯定的角度規定民事行為的有效要件,而世界許多國家的民法多從消極否定的角度進行規范。【參見易軍:《“法無禁止即自由”的私法精義》,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第127頁。】在當時的立法背景下,上述條款可以解讀為不允許將境內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但是在社會經濟、法制等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的當下也應進行反思。特別是,盡管2021年開始實施的《民法典》第143條保留了民事行為的有效要件,但也僅僅是為了方便不太熟悉法律的人們了解法律并按照法律從事交易,【參見崔建遠:《合同效力規則之完善》,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第1期,第26頁。】而且《民法典》已在私法領域確立了如下兩大原則:第一,民事行為原則上有效、例外時才無效;【參見《民法典》第136條、第143條至第154條。】第二,法無禁止即自由。【參見《民法典》第153條第1款。其實早在2009年發布的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14條中就體現出這一轉變。】換言之,《民法典》第136條和第153條從正反兩個方面強調民事行為原則上有效、只有違反強制性法律法規才無效。
《民法典》第153條的意義在于,以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為由認定仲裁協議無效必須且只能依據強制性規定,在沒有強制性規定或只有授權性規定的情況下,不能認定仲裁協議無效。而《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78條是授權性條款,據此不足以認定該類仲裁協議無效。而且
即使中國民事訴訟法明文禁止將境內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對于已經在境外取得的仲裁裁決,若不具備《紐約公約》所規定的拒絕承認和執行要件,中國依然應當承認和執行:因為中國是《紐約公約》成員國,且《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67條規定了國際條約高于國內法的原則。
其次,能否以仲裁權是準司法權為由,認為判斷仲裁協議的效力應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一方面,如上文所論證的那樣,仲裁協議屬于私法協議,應適用實體法判斷其效力。只有涉及不確定的第三人的公權力的行使才應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雖然仲裁權具有準司法權屬性,簽訂仲裁協議會涉及仲裁權的行使,但不應對仲裁協議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理由如下:第一,當事人只是通過仲裁協議授予仲裁庭仲裁權,仲裁權行使的主體是仲裁庭,故對仲裁權的限制不應針對當事人。第二,仲裁權的行使與公權力的行使涉及的對象范圍不同。公權力的行使可能涉及不特定的第三人,出于對不特定的第三人的保護,才需要限制公權力,因此遵循“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而仲裁權必須經當事人簽訂的仲裁協議授權后方能行使,其能影響到的主體僅限于仲裁協議的當事人,不涉及不特定的第三人。因此,出于對第三人的保護,只需對仲裁協議的效力進行規范,防止當事人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的利益即可,無需也不應對仲裁協議適用“法無授權即禁止”原則。學界幾乎一致認為應當認可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理由在于,國際商事仲裁的性質應為國際私法,是民間行為。
再次,認定該類仲裁協議有效不會損害中國的司法主權。因為仲裁協議的當事人目的是解決糾紛,當事人將無涉外因素爭議提交境外機構仲裁,并不等同于將無涉外因素爭議提交外國法院審判。【參見孫建麗:《國際商事仲裁中當事人意思自治問題研究》,對外經貿大學2020年博士學位論文,第57頁。】因而認可該類仲裁協議有效并未違反國家司法主權。【參見許旭:《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法律與中國實踐》,華東政法大學2019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39頁。】
法理層面,是否應當禁止將境內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仲裁協議本質上是私法協議,應當遵循私法自治原則,除非違反公共利益,否則應當認可其效力。鑒于中國仲裁協議所針對的法律關系是當事人享有意思自治的財產性爭議,這就決定了簽訂仲裁協議僅涉及私人利益,不涉及公共利益,當事人對于可以進行仲裁的糾紛有權選擇糾紛解決方式。當通過自行和解或調解達成解決方案時,該調解書或和解書對當事人具有約束力。同樣,一旦選擇仲裁,則仲裁裁決類似于間接和解結果,對當事人也應當具有約束力。《自貿區司法保障意見》第9條第1款認可在自貿區內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可以將商事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這也說明認可該類仲裁協議有效并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礙。限制當事人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本質上是在應由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領域橫加干涉,最終背離了當事人簽訂仲裁協議時的共同意愿。這種限制不僅無法徹底落實,而且即使落實了保護的也是違約方。
中國司法部2021年7月30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修訂)(征求意見稿)》第26條規定:“法律規定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但未明確不能仲裁的,當事人訂立的符合本法規定的仲裁協議有效。”這一新增條款認可了仲裁協議的私法協議屬性,也體現了“法無禁止即自由”原則。
三、是否具有涉外因素的認定結果與適用程序之間存在矛盾
關于爭議是否具有涉外因素的判斷標準,起初中國多部法律均規定三要素即主體、客體或法律關系的得喪變更,其中之一具有涉外因素的,即構成涉外爭議。【參見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304條、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78條。】2013年開始多部司法解釋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兩個要素——“經常居住地”以及“其他情形”中具有涉外因素的,也構成涉外爭議。【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2020年修正)第1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2年修正)第520條。】從這一變遷可以看出,認定是否具有涉外因素的標準日漸寬松。【參見顧維遐:《無涉外因素爭議的域外仲裁問題》,載《中外法學》2018年第3期,第652-654頁。】但遺憾的是,在“朝來新生案”“西門子案”之后,很多地方法院仍然僅以爭議主體、爭議標的、法律關系三者作為涉外因素的識別要素。【參見秦男:《論選擇境外仲裁機構仲裁協議效力的司法審查路徑》,載《法律適用》2021年第10期,第129頁。】
關于當事人是外資企業是否構成涉外因素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對“江蘇萬源案”以及“朝來新生案”【“朝來新生案”雖是在仲裁裁決在外國作出后到中國申請承認和執行,但是受案法院依然在認定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的基礎上認為仲裁協議無效。】等案件的復函或裁定中都明確表明外資不構成涉外因素。【參見《“江蘇萬源案”復函》《“朝來新生案”復函》以及“內蒙古霍煤鴻駿鋁扁錠股份有限公司與美鋁渤海鋁業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上訴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5)冀立民終字第70號民事裁定書。】值得注意的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處理與涉外仲裁及外國仲裁事項有關問題的通知》第2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處理與涉外仲裁及外國仲裁事項有關問題的通知》第2條規定:“凡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執行我國涉外仲裁機構裁決,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請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機構的裁決,如果人民法院認為我國涉外仲裁機構裁決具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情形之一的,或者申請承認和執行的外國仲裁裁決不符合我國參加的國際公約的規定或者不符合互惠原則的,在裁定不予執行或者拒絕承認和執行之前,必須報請本轄區所屬高級人民法院進行審查;如果高級人民法院同意不予執行或者拒絕承認和執行,應將其審查意見報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復后,方可裁定不予執行或者拒絕承認和執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仲裁司法審查案件報核問題的有關規定》第2條、第3條,對于純粹的國內案件的司法審查也適用內部報告制,由中級人民法院上報給高級人民法院的情形與涉外案件相同,只是相對于涉外案件,由高級人民法院上報給最高人民法院的情形僅限于以違背社會公共利益為由不予執行或者撤銷時。】對于具有涉外因素的仲裁案件,受案法院若認為應拒絕承認和執行的,則應上報;如果所屬高級人民法院也持同樣意見,則應當繼續上報到最高人民法院。雖然“江蘇萬源案”最終被認定為不具有涉外因素,卻適用了當時只有涉外仲裁和外國仲裁才應適用的內部上報制。即在認定該案是否具有涉外因素方面,法院的判斷結果與對其適用的程序之間存在矛盾,這說明受案法院潛意識里也認為該類案件具有涉外因素。這種潛意識可能是因為外資,也可能是因為約定境外仲裁機構域外仲裁本身與涉外相關,比起外資,更適宜認定約定境外機構域外仲裁構成涉外因素,因為約定境外機構域外仲裁會導致法律適用意義上的涉外性更具穩定性。
筆者認為不宜認定外資構成涉外因素,如果認定外資構成涉外因素至少應當考慮外資的比例等問題,而且資本具有極強的流動性,甚至可以借貸外資認繳股份,所以根據外資認定涉外因素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在國際仲裁領域,一般只有在法人人格被否定、需要揭開公司面紗的特殊情況下,才例外地去探討控股股東作為主體的問題,而且該理論尚未被普遍接受。【參見[英]艾倫·雷德芬、[英]馬丁·亨特:《國際商事仲裁法律與實踐》,林一飛、宋連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60頁。】即法人主體與外資之間隔著股東,以股東為主體去判斷是否構成涉外因素只有在法人人格被否定的特殊情況下才會被考慮,而且外資本身極具流動性,原則上不宜認定外資構成涉外因素。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西門子案”中仲裁裁決最終被承認和執行,主要理由是雙方當事人均為在上海自貿區內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此類公司的資本來源、最終利益歸屬、公司的經營決策一般均與其境外投資者關聯密切,為貫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可以認為構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條第5項中的可以認定為涉外民事關系的其他情形,因此認定本案仲裁協議有效。【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西門子國際交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請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一案的請示的復函》和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一中民認(外仲)字第2號民事裁定書。】本案裁定中法院所指出的“此類公司的資本來源、最終利益歸屬、公司的經營決策一般均與其境外投資者關聯密切”這一理由成為最高人民法院在“朝來新生案”等案件中所明確的外資不構成涉外因素這一司法觀點的例外。筆者認為這一理由不夠妥當,因為依此外資也應構成涉外因素。認定本案仲裁協議具有涉外性最主要的原因是雙方當事人均為在上海自貿區內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這一點在此后頒布的《自貿區司法保障意見》第9條第1款中獲得明確。自貿區擔負著中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行政審批效率、進一步與國際市場接軌的歷史使命,就仲裁而言,允許將在自由貿易區內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之間的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意味著中國正在嘗試給予企業更多的仲裁自由,這也將是未來仲裁整體改革的方向。但是,因為該文件僅是司法政策,不是司法解釋,不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第5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具有法律效力。”第6條規定:“司法解釋的形式分為‘解釋、‘規定、‘規則、‘批復和‘決定五種。”】依此認定爭議具有涉外因素時,可能會在申請確認仲裁協議階段或者申請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階段引起新的爭執。
可以說,中國司法機關否認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在法理和法律上缺乏根據,同時也與中國近年來力求為仲裁提供良好環境的司法政策不符。201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若干意見》發布,強調要貫徹實施《紐約公約》,及時承認和執行相關外國商事海事仲裁裁決;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增強中國裁判的國際公信力,維護公平競爭、誠實守信、和諧共贏的區域大合作環境。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和《自貿區司法保障意見》頒布,前者強調完善仲裁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尊重商事仲裁規律和仲裁規則;后者強調正確認定仲裁協議的效力,規范仲裁案件的司法審查,對于在自貿區內注冊的外商獨資企業之間率先進行以下嘗試:第一,打破“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不得提交境外機構仲裁”的司法慣例;第二,突破仲裁法不允許臨時仲裁的規定,認可其約定臨時仲裁的協議效力;第三,適用禁反言原則,不允許在承認和執行階段首次對仲裁協議的效力提出異議。這些司法政策充分正視了外資企業約定提交境外機構仲裁的需求、商事仲裁的商業服務屬性,并作出了合理回應,這些回應也符合仲裁協議的私法協議屬性。
四、有關仲裁司法監督的域外經驗及其借鑒
全球范圍內司法對仲裁的態度都經歷了從敵對到友好的轉變過程。在20個世紀70年代,當時的《意大利民事訴訟法典》第2條明確禁止將雙方均為意大利人的爭議提交境外仲裁(現在該條款已被廢止)。當時,在相關案件中,當事人違反上述規定約定將爭議提交境外仲裁,仲裁裁決作出后當事人到意大利申請承認和執行時,雖然一審法院以當事人之間的仲裁協議違反了《意大利民事訴訟法典》為由拒絕承認和執行,但這一做法被上級法院糾正,最終該仲裁裁決獲得承認和執行,理由是公約的效力高于國內法的效力,而且《紐約公約》僅要求仲裁裁決在外國作出,并不要求當事人具有不同國籍。【Pieter Sanders ed.,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ume I-1976),Kluwer,1976,p.190.】意大利即使在國內法明令禁止境內當事人將爭議提交境外仲裁的情況下,也遵守了作為《紐約公約》成員國的義務,樹立起嚴守公約的國際形象。與當時的意大利相比,中國法律并未明確禁止將不具有涉外因素的爭議提交外國仲裁,且當下《民法典》已經確立了“法無禁止即自由”原則,所以中國現在更應認可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
此外,中國對該類仲裁協議效力的限制也有違商事仲裁中盡量讓仲裁協議有效的國際趨勢。自1958年《紐約公約》以來,支持仲裁的理念逐步在國際上得到確認。有些國家通過立法確立了盡量讓仲裁協議有效的原則。例如,1987年《瑞士關于國際私法的聯邦法》第178條第2款規定,如果仲裁協議符合(1)雙方當事人選定的法律;(2)支配爭議主要事項的準據法;(3)瑞士法律三者之一,仲裁協議即為有效。在國際商會仲裁中,仲裁庭曾在當事人對仲裁協議所適用的法律選擇不明確的情況下,選擇了瑞士法律作為仲裁協議的準據法,以保持仲裁協議的有效性。【Albert Jan van den Berg ed.,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Award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p.202.】
在英國,如果國際商事仲裁協議中表明了通過仲裁解決爭議的意思,該仲裁協議即為有效。未明確約定仲裁協議準據法時,如果約定了仲裁地,根據最密切聯系原則,一般以仲裁地法律作為準據法;如果未約定仲裁地,則英國的默示規則是適用主合同的準據法。【參見[英]莫里斯:《法律沖突法》,李東來等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75頁。】對于仲裁條款效力的判斷適用的也是合同解釋的規則。英國法下唯一會否定個別條文甚至整個合同的情況是其違反了公共政策,比如合同基于非法或者欺詐等。【涉及非法的情形,比如有關走私、販毒、娼妓等的合同是無效的。涉及欺詐的情形,比如在商貿或航運領域,只有在租約約定倒簽提單,或者裝船貨物已經損壞,但發貨人卻要求簽發清潔提單、作出保函時,這類合同才因涉及欺詐銀行和收貨人而無效。參見楊良宜、莫世杰、楊大明:《仲裁法——從1996年英國仲裁法到國際商務仲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頁。】對于仲裁協議而言,即使仲裁機構約定得不明確,只要雙方達成了仲裁的意愿,該仲裁協議也有效。在英國上訴法院1969年審理的Hobbs Padgett & Co.(Reinsurance) Ltd. v. J.C. Kirkland and Kirkland案中,仲裁協議中只有“適當仲裁”的字眼,法院認定該仲裁協議有效。法院的解釋是:“適當仲裁”條款的含義是雙方當事人已經同意本合同項下所產生的任何爭議,包括對合同含義的爭議,均應提交仲裁而不是由法院解決。【John Parris,Casebook of Arbitration Law,George Godwin Limited,1976,p.62-65.】因為該案涉及的是兩個英國公司之間的爭議,當事人只要表達了通過仲裁解決爭議的意思,其他問題可以通過適用英國仲裁法得到解決。【參見趙秀文:《國際商事仲裁法》(第3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頁。】
中國香港地區也高度尊重當事人的仲裁意愿,只要當事人達成了仲裁意愿,仲裁協議就有效,即使當事人約定的仲裁機構并不存在。在1993年的Lucky-Goldstar International(HK)Limited v. Ng Moo Kee Engineering Limited案中,原告和被告均為在香港注冊并在香港有營業場所的公司。仲裁條款約定“應在第三國依照該國法規并根據國際商事仲裁協會的程序規則仲裁解決”。盡管“國際商事仲裁協會”并不存在,但該仲裁條款依然有效,因為當事人通過仲裁解決爭議的意圖十分明確,此項約定并不能因為選定的仲裁機構及其仲裁規則不存在而無效。仲裁應當根據原告所選擇的第三國的法律進行。【Neil Kaplan,Jill Spruce & Mechael J. Moser,Hongkong and China Arbitration:Case and Materials,Butterworths Asia,1994,p.221-224.】再比如,在1993年的William v. Chu Kong案中,當事人約定爭議應在中國內地法院起訴或中國內地仲裁。法院認為該條款并不因不確定而無效,而是賦予原告以選擇權,可以選擇仲裁或訴訟;一旦選定,這種選擇就是終局性的,另一方只能服從。【William Co v. Chu Kong Agency Co Ltd & Anor,[1993]2 HKC 377,p.13-14.】
為保持仲裁協議的有效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商事仲裁發展起了一種全新的理論,即仲裁的“非國內化”理論。該理論主張國際商事仲裁應當排除仲裁程序地國家法律的限制,在認定仲裁協議效力方面表現為對當事人意愿的完全尊重。在國際商事仲裁的司法判例中,一些仲裁機構采用不具體適用某一國家法律,而是依據超越各國內法體系的一般法律原則來確定仲裁協議所適用的法律。如20世紀80年代著名的Isover Saint Gobain v. Dow Chemical案中,仲裁員就適用了國際貿易慣例和客觀標準以及當事人公平合理的期望與當事人所表達出來的共同意愿這一主觀標準,作為確定仲裁協議有效與否的準據法。此外,法國法院在Khoms EL. Mergeb v. Dalico案中判定仲裁條款的效力時,認為仲裁條款受當事人的共同意愿支配,而沒有必要依據某一特定國家的法律。【參見[瑞士]M. Blessing:《論仲裁協議》,載中國國際商會仲裁研究所編譯:《國際商事仲裁文集》,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290頁。】
綜上,對于仲裁協議的效力,根據英國、瑞士、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等地的立法和實務,只要當事人表明了仲裁意愿,一般認定仲裁條款有效。法律在解釋仲裁條款時,應對仲裁條款的內容放寬限制,盡量使其有效,以尊重當事人的仲裁意愿并幫助其實現,這已成為當今國際仲裁的一大趨勢。【參見趙健:《國際商事仲裁的司法監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在中國成立的外資企業約定發生糾紛時在英國、瑞士、德國、韓國、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等地仲裁的,不管是否具有涉外因素,也不管是否約定了境外仲裁機構,這樣的仲裁協議都被認定為有效。在仲裁裁決的承認(認可)和執行階段,適用中國法律不認可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不僅違反了《紐約公約》第5條第1款(a)項,【世界范圍內的糾紛解決趨勢是統一準據法,為此《選擇法院協議公約》(第5條、第6條、第9條)只允許當事人選擇管轄法院,不允許當事人選擇適用于管轄協議的法律,而是統一適用被選擇地法院法。】也違反了《民法典》第153條。同時,作為《紐約公約》成員國,中國司法實務所作限制也有違反《紐約公約》第2條第1款、第3款所確立的盡量執行仲裁協議這一政策之嫌,不僅傷及仲裁的公信力,也有損中國的法治形象。
最后,世界范圍內的趨勢是淡化國際仲裁(涉外仲裁)與境內仲裁的區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簡稱《示范法》)中認定涉外或國際的標準是只要當事人約定的仲裁地位于當事人營業地點所在國以外的,即具有國際性。【《示范法》第1條第3款對“國際性”作出了明確的定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為國際仲裁:(a)仲裁協議的各方當事人在締結協議時,其營業地點位于不同的國家;或(b)下列地點之一位于各方當事人營業地點所在國以外:(i)仲裁協議中確定的或根據仲裁協議而確定的仲裁地點;(ii)履行商事關系的大部分義務的任何地點或與爭議事項關系最密切的地點;或(c)各方當事人明確同意,仲裁協議的標的與一個以上的國家有關。”】現在《示范法》的這一標準已經被很多國家采用。比如,根據《新加坡國際仲裁法》第5條第2款,【《新加坡國際仲裁法》第5條第2款規定:“無論《示范法》第1條第3款如何規定,如果(a)仲裁協議至少有一方當事人在簽訂協議時營業地位于新加坡之外的國家;或(b)下述地點之一位于新加坡之外且當事人在此有營業地:(i)仲裁協議規定的或根據仲裁協議確定的仲裁地,或(ii)商事關系的主要義務履行地或與爭議事項有最密切聯系的地點;或(c)當事人明示同意仲裁協議所涉事項與多個國家有聯系,仲裁即屬于國際仲裁。”】只要當事人約定的仲裁地位于當事人營業地點所在國以外的,即具有國際性。可以認為新加坡也允許境內糾紛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參見李莉、喬欣編著:《東盟國家商事仲裁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6-97頁。】此外,1990年4月6日之前中國香港地區區分本地仲裁和國際仲裁,而其后修訂的《仲裁條例》將《示范法》適用于中國香港地區的本地仲裁和國際仲裁,從而在實質上淡化了二者的區別。【參見張斌生主編:《仲裁法新論》(第4版),廈門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388頁。】
很多國家和地區之所以不再限制將境內爭議提交境外仲裁,原因在于尊重當事人在商事仲裁中的意思自治、限縮法院司法審查權的行使可以使該國在國際商事仲裁中獲得競爭優勢。反之則必將導致仲裁的封閉發展,并在封閉中越來越喪失競爭優勢。
結合前述分析、論證以及參照目前國際上較為通行的做法,鑒于中國是《紐約公約》成員國,且經常作為仲裁地的大部分國家都認可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而中國司法實務對仲裁的限制并不能徹底落實,這導致整體上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不可以預見、容易引發平行訴訟、保護違約方、違反《民法典》以及法院處理該類案件時存在潛意識等一系列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考慮到中國對境內仲裁與涉外仲裁適用不同的監督制度,以及法院在處理該類仲裁協議時適用當時只有涉外案件才能適用的內部上報制,可以認定外資企業約定提交境外機構仲裁構成涉外因素,即構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520條第5項規定的“可以認定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
五、結語
中國司法一直以《民事訴訟法》(2021年)第278條等授權性條款為由,限制外資企業將境內爭議提交境外仲裁機構域外仲裁,除非雙方都是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如前文所分析,從法理的角度,對中國仲裁法上可以仲裁的事項,當事人享有處分權,故不應作此限制;鑒于仲裁協議是私法協議,且《民法典》第153條已經確立了“法無禁止即自由”原則,故即使依據中國法律也應認定該類仲裁協議有效。
考慮到中國是《紐約公約》成員國,對于已經在境外作出的仲裁裁決到中國申請承認和執行的情形,關于仲裁協議效力的判斷,應當適用《紐約公約》第5條,當事人未明確約定仲裁協議準據法的,應當適用裁決地國法律。當下支持仲裁、盡量讓仲裁協議有效已經成為國際商事仲裁的趨勢,在中國成立的外資企業約定在英國、瑞士、新加坡、韓國、日本、德國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等地仲裁時,依據仲裁地的法律,該類仲裁協議有效。這就導致:首先,中國對該類仲裁協議效力的限制不能徹底落實,因不同階段適用不同的準據法,該類仲裁協議的效力不可預見。而且即使適用該限制,最終保護的也是違反仲裁協議的一方。其次,上述限制違反了《民法典》第153條在私法領域確立的“法無禁止即自由”原則。再次,中國對該類仲裁協議是否具有涉外性的認定結果與適用程序之間存在矛盾,不認可該類案件的涉外性也與處理該類案件時適用涉外程序的潛意識不一致。考慮到中國對于境內仲裁與涉外仲裁適用不同的監督制度,可以借鑒《示范法》以及國際上較為通行的做法和經驗,認定外資企業約定提交境外仲裁機構仲裁的情形構成涉外因素。這將既符合中國法律,又令仲裁協議的效力可以預見,且執行了《紐約公約》第2條第1款、第3款規定,符合盡量認可仲裁協議效力的國際趨勢,也符合中國近年來力求為仲裁提供良好環境的司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