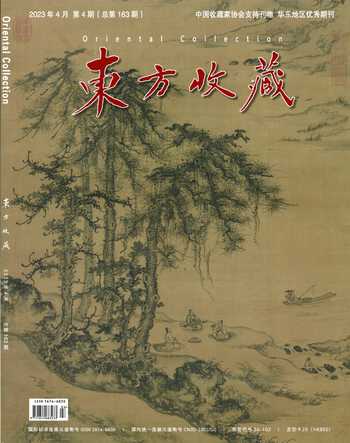劉海粟與潘天壽美術教育思想比較研究
摘要:文章圍繞20世紀中國美術教育的代表性人物劉海粟與潘天壽的美術教育思想展開對比分析。劉海粟創立近代中國第一所美術學校,擔負起向社會宣傳藝術的重任,提倡“融匯中西”;潘天壽則在“西化”熱潮洶涌的年代提出“中西繪畫拉開距離,獨立發展”的論斷,在當今社會尤其是在美術教育領域仍然不斷地被驗證其正確性。二者的藝術主張和美術教育思想,對于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產生與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因此,對二者美術教育思想進行比較與分析,對于當今美術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
關鍵詞:劉海粟;潘天壽;美術教育思想;美術教育改革
20世紀初期,中國迫切需要探索出路,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將目光轉向西方。從學習科學技術,到學習政治制度,再到學習思想文化,伴隨著經濟、政治的巨大變革,緊隨而來的便是教育方面的革新。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時代風氣之先,創辦新式學校,從此學習西方文化成為一種熱潮,教育改革的序幕由此拉開[1]。
進入20世紀中期后,社會巨變、思想激蕩,藝術領域同樣受到影響,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推動著中國繪畫開始轉型。中國繪畫形成“改良”與“全盤否定”兩大主流對峙的局面,其中改良派藝術家們在探索中國畫出路的過程中形成了“融匯中西”和“傳統出新”兩個主流走向。作為20世紀美術教育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劉海粟與潘天壽對中國美術變革分別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劉海粟力圖“融匯中西”,將中國畫和西方的后印象主義繪畫進行連接;潘天壽則提出“中西繪畫應拉開距離”,讓傳統國畫按照自己的規律獨立發展[2]。對比分析劉海粟與潘天壽的美術教育思想,其關鍵在于二者對中西藝術觀念的差異。
本文圍繞二者的時代背景、文化環境、求學經歷以及任教經歷等方面展開論述,梳理二者美術教育思想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分析比較二者具體的美術教育思想,以及二者的教學觀念、教育思想、教學模式對于當代美術教育的啟示。
一、劉海粟與潘天壽美術教育思想的形成
(一)劉海粟“融匯中西”思想的形成
劉海粟(1896—1994),江蘇常州人。幼時在家塾學習傳統書畫,10歲入繩正書院讀書,開始接觸西方課程,14歲入周湘上海布景畫傳習所學習西畫。早年受教期間恰逢新舊教育模式轉變,因此劉海粟同時接受到中西方的美術啟蒙教育,幫助其開闊視野,為后期劉海粟“融匯中西”的美術教育變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12年,年僅16歲的劉海粟自籌經費,與好友烏始光、張聿光等人共同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所美術學校——上海圖畫美術院(后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以下簡稱上海美專),這是我國現代美術教育史上第一所私立美術專門學校。該校不僅培養了大批優秀畫家,滿足了社會對美術人才的需求,更“融匯中西”,擴大了西方美術在中國的傳播。1919年,劉海粟受“五四”思潮影響,立志革新教育,而后的20年間里,劉海粟曾多次赴日本、歐洲考察學習,海外交流拓寬了他的眼界,歐洲之行幫助其與西方美術正式接軌。考察期間,文化的異彩促使劉海粟進一步研究比對中西方藝術,他將中國畫與西方的后印象主義繪畫相銜接。劉海粟一人兼中西繪畫之長,偏愛潑彩之法,色彩絢麗飛揚,畫面氣魄動人,其油畫作品《前門》入選1929年法國秋季沙龍,他也因此成為第一位參加法國沙龍的中國畫家。
劉海粟一生投身藝術,致力于探尋中國美術的出路,上海圖畫美術院成立之后,他更是勇開先河,力求通過革新教育模式培育新式人才,使中國美術緊跟時代發展,從而迸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在這樣的教育實踐與探索中,劉海粟的美術教育思想逐步形成。
(二)潘天壽“中西拉開距離,獨立發展”思想的形成
潘天壽(1897—1971),浙江寧海人。7歲時進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蘊。14歲進入寧海縣新式小學,而后就讀于浙江省第一師范學院,接受新式教育,學習數理化知識、進化論、民主思想、哲學思想等。潘天壽兼傳統文化底蘊與新式思想于一身,同時也奠定了其思想的多元性。
潘天壽畢生致力于中國傳統繪畫的繼承和革新。1923年,應劉海粟邀請,潘天壽進入上海美專教授國畫;1928年,受聘為杭州國立藝術院國畫系主任教授;1944—1947年,擔任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無論是在“全盤西化”或是“全盤蘇化”主張盛行之時,他始終堅持要讓中國畫按照自己的規律獨立發展,主張中國繪畫應與西方繪畫拉開差距,多次提出中西繪畫分系主張,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畫體系。潘天壽一生起起落落,但無論身處何種境地,他的藝術始終飽含著民族骨氣。
二、劉海粟與潘天壽美術教育思想在教學實踐中的體現
教育思想形成于教學實踐之中,不僅凝結了時代因素、社會環境、文化屬性,更與個人選擇息息相關。在當時這樣一個外來文化熱潮洶涌的年代,劉海粟與潘天壽立足現狀,在教學實踐過程中逐漸摸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育理念。
(一)劉海粟“融匯中西”思想在教學實踐的體現
上海美專作為我國現代美術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規的美術專門學校,早在建校之初,劉海粟就提出三條宣言,分別闡述了中西方藝術的關系、上海美專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對于教師的要求,以藝術救濟世人,其中“誠心”一詞可以看作是當時對于畫家、教師、學子的最高準則,也為上海美專奠定了教育基調。劉海粟曾說過:“以藝術之真理代興一切信仰。”美術教育的目的不僅要造就純正的美術人才,更是對個人情感、自由意志、完美人格的培養,時代不僅需要畫家技藝高超,更需要有走在時代前沿的勇氣與決心。
辦校治學方面,劉海粟大膽革新,引入西方教學模式,以破封建禮教之氣,力求改變當時中國藝術的困頓局面。劉海粟首開中國美術院校男女同校之先河,培養了包括潘玉良在內的大批女性藝術家;其次,在教學中大膽起用人體裸體模特,尤其是女性模特。此外,劉海粟還提出春秋兩季的旅行寫生,帶領學生們走出畫室,對景寫生;再者變更學制,隨時代變化調整教學模式,不以分數高低評價學生,而是形成一套專門的考核方法,在教學中強調創造,倡導藝術自由,培養學生美的意識[3]。
劉海粟欲開藝術先河,怎奈世道守舊。藝術與封建禮教大相徑庭,改革舉措與當時社會環境格格不入,男女同校歷經重重挑戰才得以被社會所接受,而大膽起用裸體模特則直接引出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口舌風波。1917年,上海美專舉辦成績展覽會,展出人體素描作品,各界的批評謾罵蜂擁而至,“藝術之叛徒,教育界之蟊賊”之類的批評話語直指劉海粟,但其初心不改[4],而后更是直接以“藝術叛徒”自居,直言中國當代藝術需要各種“叛徒”來打破成規,否則畫壇難掃一派萎靡之風,更是發出了“我為藝術而生,愿為藝術而死”的無畏宣言。
劉海粟的藝術人生與上海美專的發展交織在一起,其改革舉措可謂目光長遠。他的革新不僅代表著新的教育模式的到來,更代表著教育體制的結構性變化,上海美專更是為接下來的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發展奠定了基調。
(二)潘天壽“拉開距離說、獨立體系說”在教學實踐中的體現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時代,潘天壽并沒有受到美術界“西化”思潮的影響,而是沿用傳統的教學方式,教學實踐圍繞中國藝術的傳承和發展而展開。
早期,潘天壽任杭州國立藝術院國畫系主任教授,他反對學校實行的中西畫系合并的教學體系。在充分研究比較中西方藝術特點之后,潘天壽提出了“中西繪畫應該拉開距離”的論斷,強調教育辦學不能一味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要由內及外,從中國內部謀求發展民族繪畫藝術的道路,在保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礎上進行創新。自古以來,中國繪畫的獨特之處就是不以描摹為能事,而重視表達意境、氣韻和格調,對于藝術家的個人修養有很高的要求。因此,潘天壽強調帶領學生臨摹古畫,體會古人氣韻,效仿古人“目識心記”的作畫方式,以替代當時美術界流行的西方對景寫生,不是單純地復制景色,而是師法自然,經過眼、心、手的藝術加工,以此提升自身審美修養,充實文化底蘊。
20世紀50年代,潘天壽再度提出中西繪畫分系設立的主張,并且拿出系統的實施方案,沿襲古人傳統,畫分三科,提出人物、山水、花鳥分科而立的基本構架。為滿足技藝與文化相一致的要求,潘天壽提出“強其骨”這樣一條基本準則,“強其骨”不單指藝術作品中要有民族骨氣,同時也指美術教學中的“骨”,從詩詞、書法、篆刻這些支撐起中國畫的骨架入手,開設書法篆刻、古典文學、古典詩詞、美術史等課程,旨在提升中國畫內在境界,提倡中國畫里的白描和雙勾技法,教學頗具古風。這一系列舉措不僅豐富完善了中國畫的體系,更是被各大美術院系沿用至今。
潘天壽的一生都在為中國傳統畫系而斗爭,他牢牢堅守了40年,在從傳統跨向現代這一必經之路上,他將傳統中國畫與日趨現代的中國藝術相連接的同時,又保有中國畫的書香墨氣。在他看來,中國畫是沉淀著前人智慧的藝術,其中蘊含著豐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千百年來無數畫家的傳承,不應該被遺忘。
三、劉海粟與潘天壽美術教育思想的異同
在多年的美術教學實踐當中,劉海粟與潘天壽自成體系,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美術教育思想。無論二者如何革新教育,其初心都在為民族繪畫謀出路,為中國藝術拓邊界。時代之下,總有人身先士卒,與其說是劉海粟與潘天壽的相似之處,不如說是同時代美術教育家的相似之處,包括徐悲鴻、林風眠等人在內的一切教育改革,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培養人才,希望中國藝術在新時期再放光彩。
如今美術界將劉海粟定義為20世紀“融匯中西”的主將,將其一切教育成就歸根于中西結合的大膽舉措。但在對劉海粟的教育理念做進一步的了解時,筆者發現劉海粟教育思想中的異彩。劉海粟并非一味倡導“融匯中西”,更在將中國藝術推向世界。劉海粟曾說過:“中國人所作的西畫,仍然可稱為中國人的繪畫,雖然是利用西方繪畫的技法和工具,但作者是中國人,他的民族性不會因此而喪失或者削弱,反而是利用他人的工具來施展自己民族的特色。”[5]當時的中國美術界,藝術家能接觸到西方藝術已實屬不易,更不用說像劉海粟這樣能夠牢牢把住中西方藝術脈絡,以西方的藝術理論與技法滋養東方藝術。
劉海粟“融匯中西”的根本目的,不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發展西方藝術,而是要促進中國傳統畫跟上時代,相較于其他倡導“融匯中西”的藝術家,劉海粟在引進西方藝術的同時也將中國傳統藝術推向世界。1934年1月20日,劉海粟負責主持中德兩國政府聯合舉辦的“中國現代美術展覽會”[6],這是中國傳統藝術在世界舞臺上的一次正式亮相,劉海粟也被邀請到各個學校進行演講。劉海粟借此機會宣揚中國傳統繪畫的精髓,他帶著中國的傳統藝術走向世界,帶著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自信,向世界展示千百年來中國畫中的氣韻。
而在藝術融合的大背景下,潘天壽也曾將目光移向西方。他在編撰的《中國繪畫史》里寫道:“歷史上最活躍的時代就是混交的時代,期間因為外來文化的傳入與固有的特殊的民族精神互相作微妙的結合會產生異樣的光彩。”[7]但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藝術融合變了“味道”,不斷地發展為反傳統的思潮,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想作洶涌澎湃之勢而來,中國畫一再地被批評冷落。在此情況之下,潘天壽敏銳地察覺到了中國畫的生存危機并挺身而出,提出“中西繪畫應拉開距離”學說。潘天壽在“全盤西化”和折衷主義之風盛行的時候,仍然能夠堅定自己,保存藝術中的民族性不被時代所取代,中國畫中應包含著中國藝術家的自尊與骨氣,中國畫的出路不在于照搬西方模式的“皮肉”上,而在于中國藝術根骨上的自信。
四、總結
通過對劉海粟與潘天壽美術教育思想的梳理,不難發現二者教育思想的相通之處。無論二者如何進行美術教育革新,其根本都在于復興中國傳統藝術,劉海粟以西方藝術理念和繪畫技術滋養東方藝術,潘天壽則在本土壯大中國畫自身以探尋出路。藝術史上將劉海粟視為“融匯中西”的主將,把潘天壽看成“堅守傳統”的代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總有人高瞻遠矚,帶著對中國藝術的滿腔熱血合力為中國繪畫謀求生機與出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劉海粟與潘天壽為民族繪畫的發展、為國家藝術的光輝發聲,將中國藝術家的骨氣、中國藝術的民族風骨展現得淋漓盡致。對于劉海粟與潘天壽二者的藝術主張和美術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帶來了新的思考,如何讓中國畫在新時代中煥發生機,將古人的智慧、民族的藝術融入當下,是我們每一位當代學子的責任。二者的教育實踐對于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許多教育舉措至今仍然被參考采用,他們的藝術主張與教育思想對新時代美術教育的創新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與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劉曉方.我國高中階段德育文本建設問題研究[D].浙江理工大學,2012.
[2]高天民.潘天壽“中西繪畫拉開距離”說的內在意蘊[J].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03):18-30.
[3]王鏞.中外美術交流史[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張建哲,徐姝彥.百年油畫 百年人體[J].美術大觀,2001(09):47.
[5]祖洪越.劉海粟美術教育思想研究[D].上海師范大學,2020.
[6]馬海平.張弦與劉海粟的上海美專往事[J].中國美術,2019(02):70-79.
[7]潘天壽.中國繪畫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作者簡介:
紀星宇(1996—),女,漢族,吉林白山人。延邊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專業2021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術理論、美術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