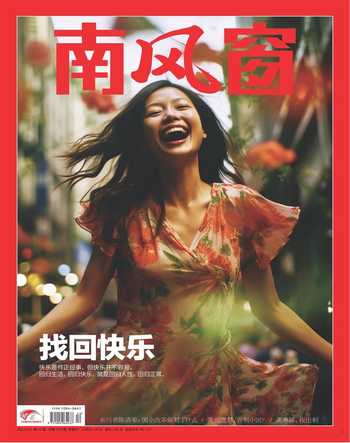工作從哪里來?
李井奎
最新各一線城市統計局公布的信息顯示,北上廣深這四座一線城市均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人口流動性最好的一線城市,這種集體開始的人口流出局面,到底說明了什么,又是否具有轉折性意義呢?
其實,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負增長并非始于今日,但深圳和廣州也加入負增長的一線城市之列,多少讓人感到不安。不僅這兩座城市在過去十余年間,常住人口均增長了數百萬,是全國增量最高的兩座城市,而且,2022年的負增長,乃是深圳自1979年建市以來常住人口的首次下降,對廣州來說也同樣罕見。
對于這種局面,若還以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為托辭,恐怕不能得到較為準確的解釋。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并不是人口負增長的原因,相反高生活成本反映的是城市人口增長的結果。一旦城市規模穩定在最優水平上,大城市中人的生活成本并不會無限上漲,也會趨于穩定,與大城市中人們的收入形成穩定的比例。反過來說,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低,也是小城市中人們收入與支出形成的均衡結果。離開具體的城市談論生活成本的高低,是沒有意義的。
撇開政府的人為限制,我們看到,城市人口的規模會穩定在一個與城市中人們的收入相適應的水平上。那么,人們的收入從哪里來?對于在城市間流動的人口來說,他們的收入恐怕主要還是來自工作。如果一個城市創造工作崗位的能力下降,那么,人們能從工作中獲得的收入也會下降。現代的青年要想找到一份有前景的工作,當然要到大城市去,那里不但工作機會更多,收入也更高。
而根據2022年8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7月我國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為19.9%,連續多月創下新高。
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調整,那么,這一因素疊加失業壓力,這些人口流出一線大城市就是很自然的趨勢了。畢竟,離開一線大城市,至少可以減輕壓力。
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工作從哪里來?工作崗位只能來自企業的投資項目,而無論是由內需還是外需拉動的投資。這部分的決策,則是由企業家來完成的。企業家投資開辦企業,對未來的收益預期充滿期待,工作崗位的需求就會增加;如果企業家階層對未來缺乏信心,他們就不會投資建廠,不會擴大經濟規模,甚至為了安全過冬,還會縮小規模,把本來打算開展的投資項目撤下,這個時候,經濟就會趨于蕭條,失業也就隨之而來。
如果只是外部需求出現了短暫下降,企業家對經濟的整體判斷和未來的長遠打算并不會受到根本性的影響。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所說,人們總是有一種干事的沖動,這就是所謂的“動物精神”。企業家總會在外部需求有所恢復時,迅速開始尋求新的經濟機會,此時再輔以適當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經濟的復蘇也就不遠了。那些離開這些一線大城市的人們,也會很快回來。
當預期轉好,收入增加,人口規模還會加大,不需要擔心城市過大,因為它受那只“看不見的手”調節,會停留在邊際最優的水平上。危險的是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企業家精神的低迷變成了常態。這種情況下,投資萎靡將會導致經濟長期失衡,資源配置的優化趨勢受到阻礙,經濟最終會穩定在一個低水平均衡上。
如果這種情況成為現實,那么,今天我們看到的這種一線大城市人口負增長的局面,就可能將持續下去,直至經濟萎縮到另外一個均衡水平上,而龐大的失業人群也將成為那樣一個時代傷痛的背影。希望這樣的事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