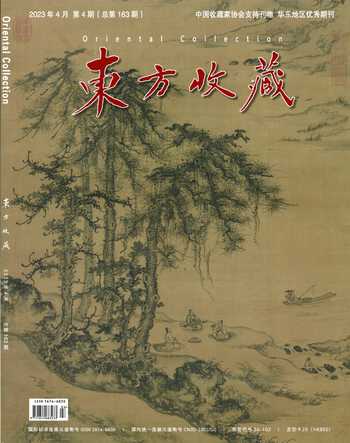傳統圖像的重構與表達



摘要:武漢博物館館藏的碧玉仙人四靈圖對碗,其用料為單色碧玉,有黑色點沁,玉質油潤,通透晶瑩。從用料和制作工藝判斷當其為仿痕都斯坦玉器,在圖案裝飾上保留著我國傳統的仙人和“四靈”組合,但又經過了歷史的重構,形成了新的表達。這種重構和表達不僅反映了深層次的社會歷史原因,同時也體現著一定的地域性和民俗性。
關鍵詞:仙人;四靈;圖像;重構
武漢博物館收藏的清代碧玉仙人四靈圖對碗(圖1),器型規整,端莊大氣,高7、口徑18厘米。器壁極薄,侈口,微束腰,矮圈足。口沿和近底足部位各飾一圈陰線紋,中部淺浮雕仙人手持兵器騎乘四靈獸。碗底心有“乾隆年制”四字款(圖2)。
這對碧玉碗的制作工藝等爭議不大,筆者不再贅述,主要針對玉碗的裝飾圖案——“四靈”和仙人的組合展開討論。“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由于圖像本身不便區分先后順序,文中就以“麟、鳳、龜、龍”作為“四靈”組合,最早出現在《禮記·禮運》中的記載來排序展開敘述。
四幅圖像的仙人面相和裝束基本一致,初步設定為同一仙人的四種表現。第一幅為仙人騎麒麟(圖3),右手握鉤,左手握二股叉;第二幅為仙人騎鳳(圖4),雙手舞劍;第三幅為仙人騎龜,左手執戟,右手持拂塵;第四幅為仙人騎龍,雙手張弓搭箭。
一、“四靈”圖像的演變和重構
“四靈”無論作為個體或整體,在古代整個圖案的裝飾應用中都比較活躍,常見于畫像磚、建筑構件、服飾、壁畫和各類器物上,同時在古代的人文觀念中也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
根據考古物證和史籍記載,古人認為龜能通靈,其預測吉兇的功能在殷商甲骨文中體現無遺,麟、鳳、龍至少在戰國時期就已作為各自物種領域的主要代表而確定下來,但是在發展過程中都有各自的經歷和地位的沉浮。總體來說,麟、鳳變化不大,一直作為祥瑞和政治身份的象征而貫穿于整個古代社會。龍的地位因“天人感應”而與皇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總體的發展趨勢是上升的,這在“四靈”當中是無可比擬的。龜的地位直到唐代還很尊崇,但在元代以后卻一落千丈。這就造成了此對玉碗中“四靈”圖案的重構,用“龍生九子”之一的赑屃代替了原組合中的龜。這一點,許維瑩在其博士論文中也有相應的論證。因此,“四靈”圖案的組合重構,正是當時社會文化發生變化的一種重新組合后新的表達,也是清代龜的地位下降的一個實物例證。
二、仙人圖像的考疑和推測
在該對碗的紋飾圖案中,仙人的女性特征比較明顯。縱觀中國古代神話信仰體系中出現的女性仙人,常見的有女媧、西王母、后土、九天圣母、碧霞元君、媽祖、斗姆元君、無生老母等,她們分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文化地域當中占據著信仰的主流。那么,此對碗紋飾圖案中的女仙究竟是誰呢?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又經歷了哪些重構呢?經筆者綜合各類資料信息推測,其當為斗姆(圖5)。
斗姆,又稱斗姆元君、斗姥、紫光夫人、斗姆摩利攴天等,是北斗眾星的母親。斗姆本身的圖像,就經歷了本土信仰和佛教經義的互相組合滲透和重構。斗姆信仰脫胎于九皇信仰,而九皇信仰則是繼承北斗信仰而來,所以從根源上來說,斗姆是古代星斗信仰的集大成者。據考,斗姆信仰形成于宋代,在元代和佛教的摩利攴天結合在一起,明清時期盛行。
《道法會元·卷八十三·先天雷晶隱書》云:
天母圣相:主法斗母摩利攴天大圣,四頭八臂,手擎日、月、弓矢、金槍、金鈴、箭牌、寶劍,著天青衣,駕火輦,輦前有七白豬引車,使者立前聽令,現大圓光內。
刊于清代的《九皇斗姥戒殺延生真經》也有這樣的記載:
九皇斗姥金輪開泰元君,頭挽螺髻,身被霞綃,耳墜金環,足登珠舄,左手執拂,右手執杵,乘五龍之車,趺八寶之座會,三登上真于摩利攴天,談生天生地之道,闡不生不滅之旨。
此外《道藏》中還有記載:
斗母紫光天后摩利攴天大圣,化身四頭八臂……兩手抵日月,一手執戟,戟上有黃幡,上有金字,云九天雷祖大帝;一手劍,一手印,或曰杵;一手金繩,一手弓,一手箭。坐七豬輦。
據此看來,從裝束上,文獻中所述“頭挽螺髻,身被霞綃”和碗上仙人的穿著表現基本吻合;從法器上,弓矢、拂、寶劍、戟基本吻合;從顯像上,碗外壁四面四幅圖案表達正好對應了斗姆元君四面八臂的形象,這在民間信仰中則是一個整體圖像的另一種表達;從坐騎上,一般是火輦前有七頭白豬或是五龍車,而在玉碗中則演變為和傳統的“四靈”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圖像重構。
三、整體圖像重構之成因
在該對玉碗中,斗姆與“四靈”圖像的組合在目前現存的圖像中較為少見,這種組合與斗姆信仰的興起演變有著緊密的聯系。斗姆的神職,據《道法會元·卷八十五·先天雷晶隱書》云:“(天母默朝急告)凡袪雷、祈禱、殺伐、禳星、避難、釋冤憎、救死亡,無施不可,務在專心致意,依法奏告,有求必應。”這種靈應也見諸清代的文人筆記中——
清王嗣槐《桂山堂詩文選》 文選卷一載:
祖母土夏月遘危疾,父景和公遠館于外,先生憂惶不知所為,日夜禱于天,愿以身代,家奉斗姥案前盎水忽結為冰,飲之得汗而疾愈。
清褚人獲《堅瓠集》 秘集卷三《斗姆救焚》載:
康熙壬申仲冬二日渾暮,屈駕橋人,見綠衣兩人在巷門口坐,以為代役看柵者,轉瞬不見,咸詫為奇,隨火起橋陌,延燒三十余家。至張君安鋪,屋柱焦損,火飛入檐,君安合掌稱“斗姆”寶號不輟,火光照耀之間,人見君安屋上有老人策杖巡行,火焰隨滅。蓋君安奉斗齋多年,極其誠敬,故斗姆垂救及門而止,奉斗之力昭然可信。
清齊學裘《見聞隨筆》 卷二《斗姥送保命燈》載:
咸豐紀元中秋前一日,大雨如注,天井成池,余病頭風將及兩月,夜間跌坐,云起樓榻上。童子壽康赤腳踆在榻旁,頭而睡。余閉目宴息,聞門有聲,見一丫鬟持燭臺進房置方桌上,又聞門聲,見一老嫗珠翠滿頭,盛裝盛服,抱一斗燈上籠碧紗,上踏步床,置斗燈于床頭,復以百齡襖掛在帳鉤。
以上三則材料中,一則是救火,二則是救命,說明了斗姆在清代神職的進一步擴大,幾乎達到有求必應、無所不能的程度。再看下面一則史料,來源于清沈起元的《敬亭詩文》文稿卷九:
今士大夫往往尊奉斗姆,為舞乩、為圓光,其術尤足感人。無論二氏之神鬼,都屬不經要,與夫子敬鬼神而遠之之訓相背。
文中出現了對斗姆信仰的批判,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斗姆信仰在當時的流行。
道教圣地武當山太子坡現存有相當數量的碑刻,從碑刻的考察中能獲知,至清末年間,分別經歷了大小6次修建。此外,龍虎殿的八字山墻下以及走道兩側的部分碑刻并未嵌入到墻壁中,是可以活動的。雖然有6通碑刻與斗姆閣修建有關,但是在資料中并未提及相關內容。在被提及的內容中,有4通的年代為乾隆三十六年(1771),1通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1通為乾隆五十年(1785)。這些被提及的碑刻總共修建過4次,第一次為1755年—1761年,主要是對太子坡進行了全面修建,包括復真殿的重建、大殿的重點維修;第二次為1771年,重新塑建了斗姆閣救苦樓的神像;第三次為1783年,在斗姆閣中作了彩畫油漆;第四次為1850年,主要為太子坡的整體維護。
此外,在武昌城西有斗姥閣。碑刻《重修武昌府斗姥閣碑記》 記載:“斗姥建自前唐,道光九年(1829)毀于大火,道光十四年(1834)重修而成,主要為扼奔流、鎮靈怪。”在此,斗姆的神職又轉化為鎮水害、鎮靈怪,這也許就是斗姆的坐騎轉化為“四靈”的直接原因。
當然,在上述提到中國傳統信仰的女神中,還有一位也與玉碗中的形象比較接近,那就是在黃帝與蚩尤大戰中助黃帝戰勝蚩尤的九天玄女,《頤道堂集》文鈔卷十一載:“元(玄)女授兵鈐位尊斗姥。”這也就進一步說明了傳統圖像在歷史的演變中會發生多種組合、層累和重構。
“出于某種功利心理,他們對神的躬逢其盛也以人們普遍喜愛的物化形式來進行。”這也許就是制造這對玉碗的最初目的。這種重新整合的圖像表達,與其說是普通民眾信仰意識的錯位表現,不如說是將信仰中的不同神靈和諧統一到日常的信仰實踐之中,體現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參考文獻:
[1]劉固盛,梅莉,胡軍等.湖北道教史[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
[2]侯杰,范麗珠.世俗與神圣:中國民眾宗教意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3][美] 韋思諦.中國大眾宗教[M].陳仲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4]王小盾.中國早期思想與符號研究:關于四神的起源及其體系形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陳垣.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6]李信軍.水陸神全:北京白云觀藏歷代道教水陸畫[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
[7]姜守誠,張海瀾.道教女仙考[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
[8]張繼禹.中華道藏[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
劉明哲(1985—),女,漢族,山西左權人。本科學歷,藝術設計專業,文博館員,研究方向:器物的圖案與紋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