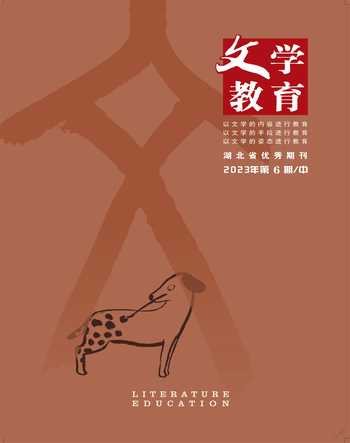論巴金《寒夜》中的身體書寫
黃平丹
內容摘要:文學中的身體包含多層次的文化內涵,能從微觀角度探究出作者深層次的思想。身體的文學化,不僅隱秘傳達了文學的話語內涵,也促進了身體研究進一步走進大眾的視野,成為獨立的象征體系。《寒夜》通過對“疾病”“創傷”“死亡”三個維度的書寫,反映出了小人物生存的邊緣化、女性“出走”的矛盾化、國統區統治的不合理化等問題,達到了隱射和批判的目的,強化了《寒夜》的現實性和真實性。
關鍵詞:《寒夜》 疾病 創傷 死亡 隱喻
“身體”不能僅僅理解成生理或者心理意義上的身體,因為“它是一個文化、權利和自然交雜的產品。”[1]101《寒夜》中的身體書寫主要集中于“疾病”“創傷”“死亡”等方面,折射出了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內容。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國統區文學實行了嚴格的文化審查制,作家的創作空間和自由被限制了。面對文化管制,“身體”便可成為“失聲”語境下發聲的武器。只有正確理解“身體”是如何成為文本意義的增殖,是如何傳達時代的話語,被賦予了何種文化想象,才能對小說的思想內蘊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疾病的病態呈現
在文學史上,疾病是常見的意象主體并且被賦予了多種功能,“隱喻和寫實,分別代表了疾病的修辭和敘事功能”[2]5。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指出因科學技術的落后而造成了疾病的神秘化,使疾病處于一個相對懸空的狀態。同時,疾病的文學化、政治化,使得疾病的隱喻意義變得更加多樣,并產生了與之相應的變體。
1.肺結核:浪漫隱喻的消解
對于疾病的書寫可有兩種情形:“一是作家所面對的現實存在性的生存與生命的困境,即書寫疾病,表現疾病與社會與人之間的關系。另一種情形則是寫作者本身就是顯在或潛在的帶病者,因自身的疾病與生命的壓抑,而激發出一種創作能力”[3]。疾病是巴金小說重要的敘事對象,尤其是對肺結核的敘事,這是因為巴金本人就是肺結核患者。
蘇珊·桑塔格認為癌癥和結核病是被隱喻修飾物所復雜化的疾病。[4]換言之,肺結核不是純粹的疾病,被賦予了多種隱喻。在西方人眼中,它具有浪漫和自我升格的意味,“結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標志。”[4]56在汪文宣身上,這種意味被解構了。一方面病態美的失解。肺結核因面色潮紅的病理學癥狀,而被西方人認為是一種病態美。但汪的疾病表現是“多么瘦!多么黃!倒更是像雞爪了!”[5]395病態的黃色成為了身體的主色調,肺結核的病態美被丑化了。“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嚨上擦揉,動作仍然遲緩而且手指僵硬。”[5]467這樣駭人的場面和肺結核的羅曼蒂克沒有任何勾連之處。另一方面,自我人格的湮沒。肺結核被認為是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家病,藝術家往往是充滿活力和生命力或者說對事物充滿好奇的,但汪身上的氣質完全相反,死氣沉沉、沒有活力。看似是疾病讓他頹廢,實則是他自我的消沉和湮沒。
結核病和癌癥是互為對照的疾病,是“丑”與“美”的對照。肺結核的浪漫在汪身上被解構了,但是汪從患病到死亡的整個過程的惶恐、掙扎到最后的放棄的心路歷程,可以看成是四十年代“大后方”社會、制度的患病,肺結核的浪漫隱喻被解構了,但社會隱喻仍值得深思。
2.心理危機:時代病的顯現
《寒夜》注重人物情感的流露與宣泄,心理描寫成為了主要手段。大量的夢境描寫、內心獨白、環境烘托等構成了小說的藝術張力。“人物的心理活動是人物與環境經過撞擊而生發出來的各種想象活動的有機組合”[6],巴金先生的心理描寫透視出了社會萬象、表現出了人物的創傷和苦難。
夢境。夢境本質是人物內心欲望的一種顯現,是人物內心活動的不自主的延伸。“夢境肯定來自于我們已客觀地或主觀地體會過的事情中。”[7]6汪經常做一些不愉快的夢。或夢見婆媳爭吵,或夢見樹生拋棄他去了蘭州,或夢見唐柏青可怕的面容等等。“這些夢境不單是汪文宣對過去生活境遇的特殊形式的回憶,而且是他對未來境況的形象化預側。”[8]夢中的一切在現實生活中或實際存在,或夢魘成真。“在心臟病和肺部疾病中,經常出現焦灼的夢。”[6]22汪自患病后,甚至害怕睡覺,因為“我怕睡著了,又會做怪夢”[6]305。在第十八章中,汪將夢境當作了現實,以為樹生去了蘭州,醒來看見樹生在床前,顫抖地問道:“你不會丟了我走開罷?”[6]358其實汪常做夢實則也是過度審視自我、過度貶低自我的表現。
內心獨白。《寒夜》中有多處內心獨白形式,比如說書信、內心對話等。內心獨白將汪的懦弱與敏感、樹生的善與欲望刻畫得栩栩如生。小說開頭汪和自己的對話,將他“老好人”的性格告知了讀者。汪有埋怨和怒氣,但僅限于埋藏在內心。汪譏諷周主任刻薄,卻只是在心里暗罵,并且“他連鼻息也極力忍住”[6]235。對兩個女人的爭吵有著不滿,但選擇在心理埋怨“這是怎樣的一個家”。樹生既有著自己的道德操守,又不甘心在這個黑洞般的家庭蠶食青春。她想要反抗,卻一直彷徨與猶豫。她曾想過相夫教子,但現實的一切,讓她無法忍受。總有聲音在告訴她“滾啊”“飛啊”,看似是外在的因素將她推了出去,實則是內心欲望的顯現。
《寒夜》能夠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成功之作,不僅僅是它具有現實性和真實性,同時也是因為心理描寫的高度成功。巴金先生的現實主義心理描寫不似前期具有浪漫質素,后期的筆鋒直指人物內心處,將人物內心的善與惡、嫉憤與懦弱都一展無余,使人物更具矛盾化,文章也更具張力化。
二.創傷的隱喻書寫
創傷是二十世紀興起的學術熱點,逐漸成為精神學、心理學乃至文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在文學層面上,創傷主要是指精神創傷和心理創傷,以及文化創傷。《寒夜》中,描寫了眾多圓形人物。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過創傷,或者是本人受過創傷而成為了加害者,他們的性格變得多元、扭曲甚至是病態。
1.歷史性創傷:封建文化的迫害
“歷史性創傷是指特殊的、常常是人為的歷史性事件”[9]。《寒夜》中歷史性創傷主要是封建舊文化、舊道德。巴金常常站在人道主義、個性主義的角度書寫和關懷女性,這與他“愛”的信仰有關,因而巴金沒有批判汪母和樹生,留出了足夠的空間給讀者。
婆媳矛盾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她們之間的糾葛不是簡單的婆媳矛盾,更是新式文化和舊有觀念碰撞的表征。汪母是封建舊文化的犧牲者,是男權文化下婦道婦德的典范。同時,她是典型的母職代表,“母職便是父權社會中父權執行指令的工具,是歷史文化中壓迫女性,默許男權的根源”。[10]70她瞧不起和貶低兒媳,是因為她沒有傳統女性的“安分守己”。汪母其實是想摧毀兒媳的尊嚴來捍衛自己和父權的莊嚴地位,對樹生產生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創傷。樹生看似是一位具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但她的反叛是帶有動搖性的。她受到了傳統觀念中“男主外,女主內”思想的影響,她會反省和自責自己為什么不能夠像汪母一樣投身家庭。“曾樹生的形象彷佛說明女人一旦擺脫了對男人的依附,就既不像人妻,也不像人母了”[10]75,樹生拋棄了丈夫和兒子,最后留個世人的是寒夜中的一個背影。
汪母對樹生的苛刻本質上是封建舊文化對女性的束縛,曾樹生的反抗本質上是女性意識的覺醒。曾樹生不顧世人的眼光,也要堅決地做花瓶,何嘗不是她擺脫束縛人性鎖鏈的方式。巴金不只是簡單的描寫婆媳矛盾,更是將矛頭指向封建舊文化以及一切壓抑人性的束縛,對傳統的男權文化、婦道婦德進行了解構。
2.結構性創傷:邊緣人物的困境
“結構性創傷是指超越歷史的失落”[9]。不能完全融入群體便是一種結構性創傷。受到結構性創傷的人物在《寒夜》中比比皆是。他們永遠是活在他人“凝視”下的小人物,沒有話語權,主體意識完全消融了,成為了“他者”。
根據帕克邊緣性的人格表現特征,“由于邊緣人不可能歸屬于兩個群體中的任何一個所以邊緣人嚴重缺乏歸屬感再加上邊緣人需要經常出入兩種不同的文化,所以經常陷入自我分裂,顯示出焦慮不安、空虛和寂寞的心理癥狀”[11]。汪處于傳統和現代之間,置身于兩個時代之間,又分明不屬于其中一個時代的分裂感,讓他產生了焦慮、不安。汪像極了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受過高等教育卻被不被社會所容納,心懷大志卻沒有施展的空間。汪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同事和上司不重視他,妻子不在乎他。他承受著多重的擠壓,將他原本的生存空間壓縮到無,最終成為時代的陪葬者。唐柏青的一生可謂是短暫且悲慘,出場便是不幸的。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最終卻成了城市的流浪漢、漂泊者,且死相慘烈。
汪文宣和唐柏青作為中華民國的同齡人,他們都是受過五四新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受到新舊文化的沖擊,又處于黑暗的統治和不合理的制度下,在這種情況下極容易對自己產生懷疑。他們具有憤世嫉俗和自卑頹唐的二重性,無法寬恕自己的無所作為,也無法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和歸屬感,最終淪為時代的邊緣人。
三.死亡的理性反思
社會性小說一般都會有死亡,死亡仿佛成為了小說敘事的一種動力,成為了作者控訴社會或者某種不合理現象的武器或者象征某種東西的不復存在。《寒夜》中,出現了眾多死相。他們的死亡都有隱射意味和指涉功能。如果只是簡單地描寫生理死亡,稍缺少張力和深度,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死亡會更有指控力度,更具有一種徹底性。
1.對病態社會的控訴
巴金先生不僅是簡單地描寫死亡,而是立足死亡本身又超越死亡,思索死亡背后耐人尋味的意義。“當我們走進文學的世界,透過鉛字所散發出來的壓抑的、頹廢的、接近死亡的氣息總是更能打動我們的心,因為這類文學觸及了人類最感到恐懼的話題。”[12]這也是作家們描寫死亡的原因之一。
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死亡是作家們所忌諱的。“到了現代,中國文人對待死亡不再那么唯美,有更多作家去‘面對淋漓的鮮血。”[13]巴金先生直面死亡,杜大心為革命犧牲、鳴鳳為“人”投河等等。死亡是悲劇的一種高級形式,“死亡對于生者來說是一面鏡子,只要我們認真審視死亡,就一定能折射出人類生存中的問題”[14],汪文宣、鐘老的死亡就是照射國統區的鏡子。汪死于肺結核,這只是作者賦予死亡的一個借口。若汪不是患有疾病,最后也會在時代的洪流中死去,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國統區黑暗的統治分不開的。政府的壓榨、逃難的恐慌、經濟的失衡,使人民遭遇精神和身體的雙重創傷。汪的不幸和時代無法割裂,如果汪和樹生能夠擁有穩定的收入,也許這個家就不會有那么多裂痕,汪也不會這么早死去,汪的悲劇只是社會悲劇的縮影。鐘老死于霍亂,其實是批判當時國統區對霍亂管理的不得當。當時霍亂流行,由于統治者的疏忽,太多人遭受了折磨,而鐘老只是其中一個。就像巴金前期的《家》,作者并不是寫一個家庭的不幸,而是通過一個家庭寫出整個社會的悲劇,以小見大,將個人、家庭與國家聯系在一起。
《寒夜》中發生的事情并不是虛構,而是作者親身經歷、看見的真實,正如巴金所說:“我只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死,但是我并沒有撒謊”[15]448。魯迅的《吶喊》《彷徨》通過死亡指控了封建舊文化、舊制度,批判了國民性,余華《活著》中死亡的重復頗有特色。因此真正的作家應該是直面死亡,而不是逃避死亡,削弱悲劇的蘊意。
2.對生存價值的思考
作為寫人的文學,不可避免地要對人的生存價值進行探討,特別是在混亂的時代,人注重尋找自我的價值。巴金先生對生命價值的探討不止是停留在表面,而是在從孱弱的身體、虛無的靈魂等圖景中挖掘靈魂深處的內容,將人物和人性置于可見之處,從而對人的生存價值進行思考。
汪代表的是迷茫的一代知識分子,找不到內驅力和自我價值,“更是深刻反映了現代精英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他們現實社會身份的難以確定性”[16]。汪身邊都是接受過教育的人,但沒人是幸福的。他們沒有生存空間,最終屈服于世俗。汪所受的新式教育,是鼓勵他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但在孱弱身軀和現實的摧殘下,最終失去了自我的靈魂和個性,從而自我價值流失了。“汪文宣失敗所揭示的,是意識形態對個體的期待要求與個體的生存條件之間不可逾越的矛盾和隔閡”[17]106。《寒夜》中沒有人是擁有完整的靈魂的,雖然樹生最后逃離了家庭這個實體空間,但她始終沒有逃出對男人依附的精神空間,始終是男人的附屬品。汪母是男權的附屬品,沒有自我。汪母似乎想通過扭曲變態的愛來找尋自我的價值,但“她需要的是世俗的倫理名分”[18],并不是真實的身份認同和自我價值。
《寒夜》寫的雖是平凡人物,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卻依托家庭這個小窗口透視出了四十年代社會的風云變化以及小人物的悲慘命運。這些小人物具有深刻的內涵,他們稱不上是人,只是一具具失去了靈魂的肉體,在世俗中苦苦地掙扎,卻依舊難逃失敗的命運,或是冰冷地死亡,或是孤獨地活著。
巴金通過人物的疾病、創傷、死亡對舊制度、國統區的不合理統治、舊文化進行了猛烈地抨擊,正如巴金所說,“我的目的無非就是要讓人看見蔣介石國民黨統治下的舊社會是什么樣。”[7]231而人物所受到的所有不公和傷害,都通過身體的各個切入點得到了反映,身體作為反映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情況的載體作用也得到了極大的發揮,社會的黑暗、小人物的掙扎、戰爭的恐懼、經濟的蕭條等均得以展現,達到了控訴和批判的目的。
參考文獻
[1]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余悅.疾病·性格·敘事——對巴金小說《寒夜》的一種解讀[J].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02):51-55.
[3]蔚藍.疾病:文學創作的內在驅動力[J].長江文藝,2019,(15):134-137.
[4][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社,2003.
[5]巴金.巴金選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6]劉必蘭.中國現代小說中的心理描述系統[D].揚州大學,2003.
[7][奧]弗洛伊德.夢的解析[M].姜春香,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19.
[8]徐道春.《寒夜》心理描寫藝術初探[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91,(4):97-101.
[9]王欣.文學中的創傷心理和創傷記憶研究[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4(06):145-150.
[10]李秀香.巴金中長篇小說之女性意識研究[D].臺北:中國文化大學,2011.
[11]車效梅,李晶.多維視野下的西方“邊緣性”理論[J].史學理論研究,2014(01):81-90.
[12]康藝青.死亡與文學的糾纏——論死亡與文學的關系[J].文學界(理論版),2012,(02):32-35.
[13]晁真強.論中西文學里的死亡意識[J].安陽工學院學報,2008,(01):67-69.
[14]吳圣剛.死亡的敘事方式及其文學價值——遲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批評[J].南都學壇,2008,(04):67-69.
[15]李存光.巴金研究資料[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
[16]宋劍華.寒夜:巴金精神世界的苦悶象征[J].燕趙學術,2009,(02):94-104.
[17]唐小兵著.英雄與凡人的時代解讀20世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18]張繼紅,張學敏.從《家》到《寒夜》看巴金小說的文本裂痕——兼論其家族倫理演變與敘事邏輯的關系[J].理論界,2009(09):136-138.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