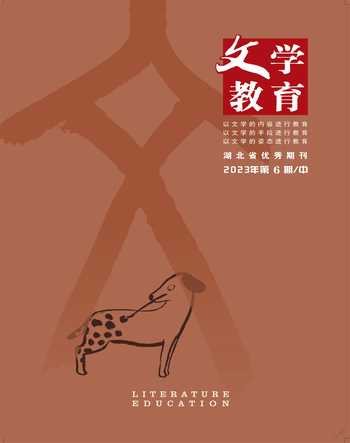論《現實一種》中的暴力敘事
邱心怡
內容摘要:暴力敘事作為一個復雜的審美范疇,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醒目特質。從晚清到中國現代乃至當代,由于受到不同時期社會現象的呼喚,作家們常傾向于在文學創作中使用暴力敘事這一手段,在發揮啟蒙作用的同時對社會進行重新審視。余華作為先鋒小說的代表作家,其中篇小說《現實一種》,憑借“暴力”的敘事特點,顛覆了對傳統道德理念的理解,體現出先鋒小說的創作特色。
關鍵詞:余華 《現實一種》 暴力 刑罰 荒誕 意象
《現實一種》是余華早期的作品。本該和樂的一家子最后互相殘殺,上演了一場人性的鬧劇。皮皮的錯誤看似是整個悲劇的開始。在我看來,悲劇早已開始。皮皮無心的殺害比山崗處心積慮的殺害更為殘酷,一個孩童在心里種下的不是友愛不是純潔,而是從虐待堂弟的暴力中得到安慰和快樂。在我們為之驚嘆的時候不禁要問,這所有荒誕的一切到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呢?于是我們看到了,母親只關心自己日漸干枯的身體而不顧皮皮需要關懷的感受,我們看到了夫妻之間的暴力給皮皮留下的陰影,看到兄弟媳婦之間近乎病態的連環報復,所有的一切也就清晰起來,所有的暴力和扭曲也都可以理解。暴力敘事是本作品的一大特色。
一.暴力敘事的主題——復仇與刑法
“暴力敘事”這一概念主要是指以使用“暴力手段”進行思想啟蒙的一種文學創作傾向。70年代末,中國涌現出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家,但由于其創作手法的刻板,故隨著時代發展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改革開放后,受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以余華為代表的先鋒作家接過形式實驗的大旗,挑戰了傳統的敘述方式,在以往暴力敘事的創作基礎之上,進一步發揮自己的創作意識。通過表層文字的“暴力”表現,反映出深層的時代與社會問題,實現了文學“回歸自身”的創作。
余華的中篇小說《現實一種》發表于《北京文學》1988年第1期。作者采用零度敘事的手法講述了山崗、山峰一家人以復仇為主題,不斷挑戰倫理秩序的底線的故事,整個文本都籠罩著暴力的陰影。“那天早晨和別的早晨沒有兩樣,那天早晨正下著小雨。”[1]作者以飽含深意的一句話開始對文章的敘述,但是隨即就將讀者拉入一個陌生化世界,去審視那個異化的早晨。自山崗的兒子皮皮無意中殺死了山峰的兒子始,血腥與死亡就成為稀松平常的存在。從扇耳光的沖擊聲到掐喉管的爆破聲,最后到摔下致死的清脆聲,兒童皮皮都在用不同的聲音去證明生的象征,然而這一切卻是以暴力和死亡為代價,復仇的戲劇也由此拉開了序幕。當山峰回到家發現兒子死亡已成為事實時,便要皮皮為兒子償命。隨后,山崗一家也發瘋似的重復上演復仇的戲碼。“兄弟相殘已不再是一個道德事件,確切地說,這也不是一個歷史理性規范下的倫理事件,而僅僅是一次現代性敘事中的倫理事件,它徹底顛覆了‘親親、‘愛仁等歷史理性認可的傳統倫理。”[2]在山峰因山崗喪命后,山崗又受到山峰妻子的控告接受了槍斃。故事到此并未完結,在文章結尾山崗的遺體被捐贈后,留下的睪丸卻移植成功了。不久后世界上又多了一個十分壯實的嬰兒,下一個皮皮的出世,使山崗后繼有人了。文本從皮皮的暴力行為始,經過一個敘事過程又回到皮皮本身而終,突破了以往單一的線性敘事描寫,構成了一種圓形敘事的結構模式。在一個圓形復仇敘事結束的同時,意味著新一輪復仇的開始。暴力、復仇成為文本世界永恒的存在,而親情則蕩然無存。
刑罰作為暴力手段的特殊表演常常被作家們所青睞,如莫言的《檀香刑》、王小波的《似水流年》、阿來的《行刑人爾依》,等等。當代作家渴望通過對刑罰的敘述進而挖掘其背后更深層次的寓意。在作品《現實一種》中刑罰表演也上升到了極致,一家人仿佛“殺人機器”般共存在一個空間下,不斷從施刑者到受刑者身份轉換,從而完成一出血淋淋的“鬧劇”。皮皮以舔血跡的方式來消解山峰的怨恨,卻由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山崗為了給兒子皮皮復仇,讓狗舔舐山峰讓他活活笑死。作為文本中一個唯一不流血的刑罰,在笑聲嘹亮節奏鮮明中的死亡卻存在著詭異的殘酷。受到懲罰的山崗被拉去行刑,“想起先前他常來這里。幾乎每一次槍斃犯人他都擠在前排觀瞧。可是站在這個位置上倒是第一次。”[3]此時,在這里“看”與“被看”的角色進行了互換。現代許多作家為達到國民性批判這一要求,刑罰與示眾常常成為他們的重要選擇。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對阿Q行刑的刻畫,在《藥》中對夏瑜砍頭的刻畫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余華承襲了魯迅小說的特點,在刻畫看客的麻木愚昧的同時,余華對被看者進行新的審視。例如山崗在行刑前尋找自己曾經觀看的位置,以一個“被看”的主體去尋找“看客”的新角度,這是麻木到了極致還是想用靈魂觀摩自己的死亡?
二.暴力敘事的手法——荒誕敘事
荒誕(absurd)一詞由拉丁文(sardus)演變而來,最初的含義是“音樂不和諧”,而后在哲學上指個人與生存環境脫節。荒誕作為一種藝術手法,具有強烈的諷刺功能。在《現實一種》中作者就利用了這種陌生化效果,構筑了一個荒誕的世界。
在余華的諸多作品中,兒童這一身份常常用來諷刺和反映現實。作品中的皮皮從一開始就展現出異于常人的興趣,他將成人世界的暴力行為復刻在心里,同時又作用于無法反抗的堂弟身上。如同余華所述,“暴力因為其形式充滿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內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4]充滿暴力血腥的環境所帶來的陰影,遏制了兒童的天性在試圖打破孤寂氛圍的情況下,皮皮的無意識行為展現了在荒誕的時空中兒童的情感缺失與本能選擇,暴力在這里成為他的本質存在屬性。在皮皮被逼迫舔存留在地上的堂弟的血時,他“伸出舌頭試探地舔了一下,于是一種嶄新的滋味油然而生。接下去他就放心去舔了。”[5]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道:“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6]在這里魯迅所描述的吃人并非真的吃人,而余華所描述的卻帶有一絲真的吃人意味。但是兩者都是對社會進行控訴,凸顯時代與人性的冷漠,以此來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
在文本中荒誕敘事還表現在親情關系的疏離上。祖母看見孫子倒地而亡,卻是嚇了一跳,趕緊回自己的臥室。本是血濃于水的關系卻展現出難以透視的淡薄,在這荒誕行為的背后是對生命的無知還是對死亡的恐懼?同樣的行為發生在孩子的母親身上,“走到近旁她試探性地叫了幾聲兒子的名字,兒子沒有反應。這時她似乎略有些放心,仿佛躺著的并不是她的兒子。”[7]在這里,作者展現出兩個層面上的荒誕含義。首先,當她否定倒地而亡的不是她的孩子后,她迅速轉為看客的角色,做出了與祖母一樣的舉動,走向屋內。在諷刺和荒誕的背后展現的是家庭濃烈的分裂感。其次,面對孩子死亡的另一荒誕表現是母親的僥幸心理和自我欺騙,在極其夸張的自我催眠背后透露出人民深深的麻木。伊麗莎白·庫伯勒·羅絲在她的著作《論死亡和瀕臨死亡》中把死亡過程分成五個心理階段,即拒絕,憤怒,掙扎,沮喪,接受。在文本中這位母親所做出的反應就是第一個心理階段——拒絕。在這里“否認”成為她的緩沖器,但是所激起出的心理防御機制卻強大到辨認出是自己的孩子后依然毫不猶豫離開,在荒誕中讓人唏噓不已。
此外,死亡在文章也是作為一個荒誕的存在。在被行刑后的山崗只剩下半個腦袋,本該死亡的他并沒有在刑場倒下。作者突破了現實世界的羈絆,讓意識清醒的山崗在他筆下大刀闊斧地跨步前行,并且構成與妻子進行正常交流的荒誕情節。隨后,山峰的妻子為了復仇以山崗妻子的名義將山崗的遺體捐贈了。作為牙醫的余華從解剖學角度展示了死亡。但是對挽救生命為業的醫生,余華所用的詞卻是“瓜分”。在異化的世界里,醫生的神圣存在被抹殺,拿著手術刀的他們從救人轉向“殺人”。“中國當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時候,他她的敘事才得心應手,顯示出力道和內在的激情。因此,這促使我們去審視中國現代以來暴力美學的傳統”[8]在手術室外排隊等待的醫生,正如在等待著施暴的狂歡一般。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國全面融入全球化浪潮,商品經濟給人們帶來利益的同時改組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追求物質豐裕的同時,所帶來的精神空虛讓人們開始思考自身的價值。余華在作品中將思考投射在山崗這個虛擬人物身上,一個高等生物的價值到最后卻是從物品的“實用性”角度去考慮,生命本身乃至精神的價值及內涵卻被丟棄,在這里價值也被賦予另一種解釋。同時,在醫生們的解剖狂歡中也暗示了一種社會的暴力風氣,當眾人都在享受暴力帶來的刺激時他們真正想享受的是什么?
三.暴力敘事中的意象
意象是具備美學意義的文學符號,作為主觀的意與客觀的象相統一的藝術形象,它不僅飽含作者的創作意圖,更是具有獨立的象征意義。在作品《現實一種》中,余華也創造了一系列意象,賦予文章多重意蘊。
小說開篇就對文章背景進行渲染:“因為這雨斷斷續續下了一個多星期,所以在山崗和山峰兄弟倆的印象中,晴天十分遙遠,仿佛遠在他們的童年里。”[9]通過對陰冷蕭瑟的環境勾勒,傳達出一家人的灰暗生活。但同時,余華又給富有美學意義的“雨”的意象賦予暴力含義。皮皮把雨的聲音比作是父親用手指敲打他腦袋的聲音,到最后他逐漸數出四場富有不同含義的雨,在這里也象征著文本將發生四場殺人事件。當雨停了即暗示著第一場殺人戲劇即將上演,陽光照在皮皮身上,一雙帶有屠殺意味的手伸向表弟,“你想去看太陽嗎……我知道了,你是要我抱你”[10]隨即,一個生命就此消亡。
此外,由于井的陰森意味,所以作家們常常會選擇“井”作為小說的意象來傳達自己的創作意圖,如蘇童的《妻妾成群》、殘雪的《山上的小屋》中“井”的意象等。在小說《現實一種》中“井”也具有豐富的隱喻內涵性。“他只覺得眼前雜草叢生,除此之外還有一口綠得發亮的井。”[11]這里的井象征著人性的幽暗之處,同時也象征著麻木腐爛的世界,暗示了山崗下一輪的血腥報復。余華對色彩有著獨特的敏感,在描述撲面而來的血腥的紅色后作者馬上轉向“綠得發亮”的描寫,這種鮮明的顏色對比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感,給文本渲染出陰冷、可怖的氛圍。
小說中陽光與血的意象大部分情況下都是伴隨存在的。陽光像是一位在場的隱形人物,觀看著這一輪血淋淋的屠殺過程。當祖母打開房門,她看見的是涌進來的陽光與地上的一灘血,此時陽光是作為強有力的壓迫象征以及審視人性的工具存在,親情的淡薄在這種壓迫下促使祖母馬上走回自己的臥室。但同時在小說中又體現出陽光在文學傳統中作為光明和正義的象征,“他記得自己一路罵罵咧咧,但罵的都是陽光,那陽光都快使他站不住了。”[12]對于陽光的謾罵,突顯出麻木腐朽的人們對于鮮活的恐懼。而后用同樣的筆法描寫山峰在面對陽光時的天旋地轉,這種重復的手法更是顯現在光明的照射下人性難以掩蓋的腐爛。小說中每一場死亡事件都是在陽光下發生的,“血在陽光下顯得有些耀眼。他發現那一攤血在發出光亮,像陽光一樣的光亮。”[13]陽光下的罪行比夜晚更富有恐怖意味,赤裸裸的人性在陽光下沐浴,與正常的現實秩序形成強烈反差,構成一種特殊的超現實韻味。此外,小說對血的意象有著較大筆墨的描寫。“他俯下身去察看,發現血時從腦袋里流出來的,流在地上像一朵花似的在慢吞吞開放著。”[14]余華用浪漫主義的筆法去書寫暴力,給予小說詩意的光暈,在暴力與詩意的互相轉換中充滿著恐怖美學的韻味。同時,血在小說中也不僅僅是作為自然物質的存在,也象征著血緣關系。“在中國文明的形成中,宗法血緣關系非但未被沖破,相反,還處在不斷的強化之中。”[15]然而在小說中作者賦予“血”戲劇化的含義,象征親情的血緣在懲罰中被享用了,在突出血的詭異美感同時,作者同樣表達了小說中血親之間的恐怖本質。
余華顛覆了傳統文學的創作原則,以純粹暴力的敘述方式展現了“現實一種”。在作品中不僅以細致入微的手法刻畫了一個個真實的暴力場景,同時,在暴力場景之外,他還發出了對當下社會、人性、情感等問題的全面思考的呼喚。
參考文獻
[1]陳思和,張新穎,王光東.余華:由“先鋒”寫作轉向民間之后[J].文藝爭鳴,2000,(01):68-70.
[2]丁帆,傅元峰.余華的暴力敘事[J].當代作家評論,2013,(06):126-129.
[3]王德威.傷痕即景暴力奇觀[J].名作欣賞,2002(02).
[4]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5]趙毅衡.非語義化的凱旋——細讀余華[J].當代作家評論,1991(05-01):1002-1809.
[6]周艷秋.余華:暴力書寫及其回歸[J].美與時代,2008(01).
注 釋
[1]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2]葉立文.顛覆歷史理性——余華小說的啟蒙敘事[J].小說評論,2002,(04):40-45.
[3]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頁.
[4]余華.虛偽的作品[J].上海文論,1989,05.
[5]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頁.
[6]魯迅.狂人日記[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第14頁.
[7]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8]陳曉明.“動刀”:當代小說敘事的暴力美學[J].社會科學,2010(5):159.
[9]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10]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
[11]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頁.
[12]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頁.
[13]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頁.
[14]余華.現實一種[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頁.
[15]馬新.中國遠古社會史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