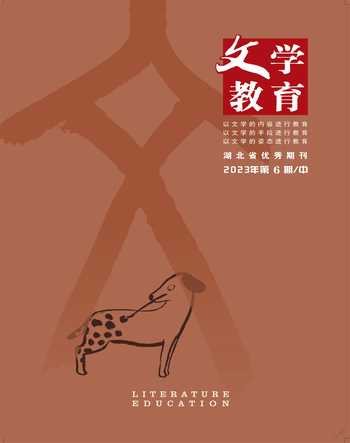河?xùn)|碧梧桐《中國游蹤》中的寧波書寫
李媛
內(nèi)容摘要:河?xùn)|碧梧桐(1873-1937)是活躍于明治、大正、昭和時(shí)期的俳人和隨筆作家,他于1918年游覽中國多地,并在次年出版游記《中國游蹤》。碧梧桐的此次中國行意在以中國為參考,為日本國民帶來啟迪與暗示。因此他作品中的寧波書寫始終統(tǒng)一于以西方文明為標(biāo)準(zhǔn)的審美視角,其在現(xiàn)實(shí)中國中對固有認(rèn)識(shí)進(jìn)行了重新體驗(yàn),并再次確認(rèn)了早已扎根于日本人心中的中國形象。而他與日本近代知識(shí)分子身上共通的“中國趣味”在面對現(xiàn)實(shí)的中國時(shí)產(chǎn)生的巨大落差,又使得他的文字中所反映的中國觀是復(fù)雜且矛盾的,而這種心態(tài)在近代日本來華文人的游記書寫中亦不少見。
關(guān)鍵詞:河?xùn)|碧梧桐 《中國游蹤》 寧波書寫 中國觀
日本近代有大批的文人懷著各種目的到訪中國,以游記的形式記錄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并留下許多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中的“都市書寫”因?yàn)楠?dú)特的文學(xué)價(jià)值和歷史文獻(xiàn)價(jià)值,近年來逐漸成為日本文學(xué)中的研究成為學(xué)術(shù)界的熱點(diǎn)之一,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悠久的交流歷史,而寧波、古稱“明州”, 地理位置的優(yōu)越性使其歷來都是中日之間的交流的窗口,在中日交流史上扮演著不容忽視的重要角色,也是日本文人游歷中國的重要一站。
時(shí)至今日,日本文學(xué)中的“上海書寫”“北京書寫”研究都已初具規(guī)模,但針對日本文學(xué)中“寧波書寫”的研究仍處于被忽略的地位。而關(guān)于河?xùn)|碧梧桐的相關(guān)研究情況,中日雙方的研究現(xiàn)狀也呈現(xiàn)差異。在中國關(guān)于河?xùn)|碧梧桐的作家研究與作品研究比較稀少。彭恩華版的《日本俳句史》[1]和鄭民欽版的《日本俳句史》[2]中的部分章節(jié)都對河?xùn)|碧梧桐的俳句生涯以及碧梧桐自身的“新傾向運(yùn)動(dòng)”都做了詳細(xì)的介紹。此外,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研究中也有涉及碧梧桐的杭州印象的研究[3]以及以碧梧桐的“無中心論”為主要研究對象,對“無中心論”進(jìn)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的相關(guān)研究[4]。而在日本關(guān)于河?xùn)|碧梧桐的研究相對較多。阿部喜三男的《河?xùn)|碧梧桐》是第一部關(guān)于河?xùn)|碧梧桐作家論的著作,其由“作家研究篇”“鑒賞篇”“作品抄”“紀(jì)行篇”四部分組成,卷末附有參考文獻(xiàn)、年譜和俳句索引[5]。瓜生敏一曾評價(jià)以阿部喜三男的研究為首,使得碧梧桐的全貌得以清晰,奠定了碧梧桐研究的基石[6]。同時(shí)也有研究關(guān)注了碧梧桐與日俄戰(zhàn)爭的交點(diǎn),討論了碧梧桐形成了怎樣的俳句觀最后走向了新傾向俳句[7]。除此之外,日本學(xué)界對于碧梧桐的研究基本集中于“新傾向俳句”的俳論探討和作家論研究上。
總的來說,中國學(xué)界對河?xùn)|碧梧桐的研究還不成熟,尚無關(guān)于其的研究著作,基本還停留在初級的介紹作家作品的階段。而針對《中國游蹤》,此本書尚無中文譯本,學(xué)界對于碧梧桐的中國經(jīng)歷與中國觀的研究很少。在日本,雖然有很多關(guān)于碧梧桐的作家論和作品論的學(xué)術(shù)成果。但日本學(xué)界幾乎都忽略了碧梧桐的旅游經(jīng)歷對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影響。所以針對《中國游蹤》中“寧波書寫”的探討不僅成為舊中國近代化和國民性研究的重要參照,也為河?xùn)|碧梧桐相關(guān)作家研究的提供了新路徑。除此之外,也是探討寧波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歷史地位的一個(gè)新視角。
一.河?xùn)|碧梧桐與《中國游蹤》
河?xùn)|碧梧桐生于愛媛縣首府松山市,本名秉五郎,又號(hào)如月、青桐、桐仙。其父河?xùn)|靜溪是朱子派學(xué)者。明治二十三年(1890)成為子規(guī)門人,在正岡子規(guī)膝下進(jìn)行徘句革新運(yùn)動(dòng),活躍于日本徘壇。子規(guī)逝世后,碧梧桐成了《日本》徘句欄的編輯,就《溫泉百句》與高濱虛子展開論戰(zhàn),從此以后逐漸發(fā)展成為虛子、碧梧桐兩派的對立,后來甚至矛盾表面化尖銳化。明治三十九年(1906)和明治四十二年(1909)均受到句佛上人的支持進(jìn)行了兩次全國旅行,于旅途中提出“新傾向派俳句”[8],大力提倡“新傾向俳句”和“無中心論”。之后,“新傾向俳句”迎來全盛時(shí)代,碧梧桐的紀(jì)行文《三千里》和《續(xù)三千里》也先后出版。碧梧桐一派與大正初期的以子虛為代表的號(hào)稱守舊派,強(qiáng)調(diào)尊重定型和傳統(tǒng)的季題的觀念相矛盾,最后斗爭結(jié)果是碧派勢力逐漸下降,而虛子派的影響和威信則越來越高。大正七年(1918)四月至七月游于中國,大正九年(1920)至十一年(1922)游于歐美。昭和八年(1933)在六十壽辰的祝賀會(huì)上宣布退出俳壇。昭和十二年(1937)二月一日,因傷寒病發(fā)敗血癥逝世,享年六十五歲。
《中國游蹤》[9]是河?xùn)|碧梧桐于中國旅行之后在大正八年(1919)十月,出版于大阪屋號(hào)書店的旅行記。碧梧桐在大正七年(1918)四月十二日從東京出發(fā),十八日在神戶坐上諏訪丸,受到船長關(guān)根海峰的邀請延長了旅程。從上海出發(fā)游歷了香港,以及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五月十八日返回上海,之后先后游覽了杭州、寧波、蘇州、南京、蕪湖、廬山、武昌、大治、漢江、宜昌、河南龍門、北京、天津、濟(jì)南、曲阜、泰山等地。七月二十一日從馬關(guān)(山口縣下關(guān))登陸,二十五日回到東京。在這期間,碧梧桐的旅行記和旅吟均發(fā)表于《海紅》和《日本及日本人》雜志,第二年以《中國游蹤》出版[10]。碧梧桐在《中國游蹤》的序記中關(guān)于此書的內(nèi)容構(gòu)成以及他來中國的緣由,這樣寫道:“回國后我著手于寫旅行游記,約一年時(shí)間才完成半數(shù),寫完了在中國南方的經(jīng)歷正要起筆有關(guān)中國北方的見聞。現(xiàn)在,將在中國南方的游記匯總起來編成本書。作為日本人,有緊要的原因需要我們必須去認(rèn)識(shí)中國,認(rèn)識(shí)中國人。要完成這件事,直接去觀察和接觸無疑是最有成效的方式。書中將毫不保留地介紹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感。這樣做的緣由,是我確信在對不可不知的中國與中國人的解讀的過程中,一定會(huì)給國人帶來些許啟迪與暗示。[11]”
從這一段敘述中,我們可以一窺碧梧桐來中國的原因。作為文明母國的中國“有緊要的原因”而“不可不知”,這些形容體現(xiàn)了自幼深受漢學(xué)熏陶的碧梧桐對于向日本人介紹中國這件事的重視程度。而解讀中國的目的是“一定會(huì)給國人帶來些許啟迪與暗示”,可見在碧梧桐看來,以西方文明作為標(biāo)準(zhǔn),在此標(biāo)準(zhǔn)下所書寫的中國形象,可以作為一種“方法”來服務(wù)于日本國家本身,為日本自身發(fā)展帶來多樣化的思考與啟示,成為日本人構(gòu)筑起自我形象和身份認(rèn)同的裝置。
二.《中國游蹤》中的寧波人物書寫
河?xùn)|碧梧桐一生游歷多處,他在《中國游蹤》的開頭部分中曾寫道“無論是游于中國行于印度,還是住于南洋老于北美,這都是我的自由。感念平生是不可能平靜地死于榻榻米之上,我要任性地行使個(gè)人的權(quán)力[12]”碧梧桐從游覽廣東回來后,他受朋友邀請,同行前往杭州,他參觀了西湖的三潭印月、錢塘江、靈隱寺等處,隨即乘車返回上海。之后他又從上海出發(fā)乘船前往寧波,并且先后前往寧波的天童寺、阿育王寺、普陀山。《中國游蹤》中的第八章“寧波”、第九章“天童寺育王寺”,第十章“普陀山”中記錄了他在寧波的經(jīng)歷[13]。碧梧桐在寧波的經(jīng)歷中很少與中國人直接打交道,所陪同旅行的則是日本友人S君和兼吉君。在寧波游記中碧梧桐所記載的基本是他聽說或親眼目睹后對中國人的籠統(tǒng)的整體印象。
寧波人留給碧梧桐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他在游記中多次提到的民眾的“不潔”。碧梧桐在前往天童寺時(shí)乘坐當(dāng)?shù)氐挠未瓦@樣記述道“順著甬江穿過臟亂不堪的后街,就來到了運(yùn)河的碼頭。幾艘船連在一起,船篷都是用竹子做的草席。談好船費(fèi)后,我們登上了其中一條還算整潔的船,仔細(xì)一看船內(nèi)卻像垃圾船似的骯臟難聞。[14]”而當(dāng)他提到人們的飲水“陸地上生活的人們的可怕愚昧的飲水觀念是用明礬將混有泥土渾濁不堪的水過濾后飲用[15]”,游覽美麗的普陀山時(shí)“氣清而景明,環(huán)境的莊嚴(yán)震撼心魂,我們?nèi)缤斡诋嬛小5矍皡s出現(xiàn)了一坨過分真實(shí)隨意、讓人不可忽視的人糞。[16]”碧梧桐對寧波的“不潔”這一印象,準(zhǔn)確地說是對于在寧波遇見的中國人的印象,正是同時(shí)代日本社會(huì)對中國人的一種普遍共識(shí)。
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時(shí),日本對于中國的新聞報(bào)道,文學(xué)作品和流行歌曲等各種宣傳中,就充斥著對于中國人的丑化。比如甲午中日海戰(zhàn)中日本的一名騎兵在給友人岡部亮吉的信中就這樣描述中國的牛莊:“以前支那人垂流下來的糞尿隱居在冰雪之中,現(xiàn)在糞尿露出表面,不可不謂其骯臟。最過分的是,就算是支那人上等人家的大門口也流淌著糞尿,不會(huì)在別處設(shè)置便所。雖然知道這是一個(gè)野蠻國,但也大出意料。[17]”
除此之外對于中國人飲水的“不潔”田山花袋在自己的從軍記《日露戦爭実記》中,寫道“西洋人視支那人為動(dòng)物,不得不說,他們實(shí)際上就是動(dòng)物,是下等生物。試想一下,他們不是滿不在乎地喝著水坑里的,泥沼里的,馬蹄印里的積水嗎?[18]”早在1897年,臺(tái)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初,日本的當(dāng)政者們就擔(dān)心,“中國人的風(fēng)俗中諸如鴉片、賭博、淫穢、不潔、破廉恥等會(huì)傳染給國人。[19]”在明治維新以后逐漸形成的蔑視中國的風(fēng)氣之中,中國人的“陋習(xí)”被夸張放大后,反過來又為蔑視中國的風(fēng)氣提供了依據(jù)。帶著這種認(rèn)識(shí)來到中國的日本人不知不覺間經(jīng)歷了一個(gè)對此重新體驗(yàn)的過程,更加深信不疑。而他們出版的一系列中國旅行記,對于日本國民的中國認(rèn)識(shí)產(chǎn)生了直接的或者潛移默化的影響,讓蔑視型的中國觀在日本人中得到了普及[20]。
除“不潔”之外,碧梧桐在來到寧波前就聽說了關(guān)于寧波人的傳聞,就是“善經(jīng)商”,他這樣寫道“說起寧波,如今以盛產(chǎn)海鮮而聞名。在上海說起寧波人,和在京都聊到江州人一樣,通稱為會(huì)做生意的人。[21]”他也具體介紹了寧波人善于經(jīng)商的一個(gè)例子是他在船上看到的甬江岸邊的茅草冰室,“巨大茅草屋的一部分逐漸浮現(xiàn)出來,這就是傳說中的冰室。而現(xiàn)在據(jù)說是這是為了將此處的海鮮運(yùn)到上海而設(shè)的冰儲(chǔ)藏室。[22]”寧波很早就在全國各地展開了商業(yè)發(fā)展,尤其是在上海。早在1876年的《滬游雜記》一書中曾記錄“沿江數(shù)里,皆船廠、貨棧、輪舟碼頭、洋商住宅,粵東、寧波人在此計(jì)工度日者甚眾。[23]”反映了在上海近代寧波人的從商情況。寧波人為了出口海鮮在甬江岸邊利用茅草屋作儲(chǔ)藏海鮮的冰室則佐證了碧梧桐對寧波人“善經(jīng)商”的看法。
但是,“善經(jīng)商”并不是為了凸顯寧波人的優(yōu)點(diǎn),碧梧桐認(rèn)為善于經(jīng)商的寧波人和文明傳播的窗口寧波如今卻成為了一個(gè)接受他國文明的文明輸入地,這反而凸顯了近代中國的衰落。他寫道“無論是要入唐渡天修行的日本僧人,還是其他的遣唐使,留學(xué)生,他們第一步踏上的中國土地就是寧波。[24]”寧波作為自古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在千年的文化交流中更多的在于輸出和彰顯古代中國的文化與實(shí)力,是古代中國繁盛的象征。而如今卻物是人非,碧梧桐寫道:“寧波曾是文明輸出的源頭。正因?yàn)槭俏拿鬏敵鲋床庞泻芏嘀档抿湴林帲詫幉ㄈ嘶蛟S將引入他國文明看做是國家的恥辱。對外夸夸其談自己國家的中國人,在面對不管是上海、漢口、天津還是青島都是依存國外文明才建起的事實(shí)面前,都只能啞口無言。[25]”
從兩次鴉片戰(zhàn)爭過后,日本人對中國的態(tài)度從依附走向質(zhì)疑,甲午戰(zhàn)爭中國失敗后,日本人更是逐漸從質(zhì)疑到丑化、蔑視中國。日俄戰(zhàn)爭的勝利,日本自信成為世界一等國。寧波人自古的善經(jīng)商善于輸出文明到如今反而凸顯了近代中國的落魄,這代表著昔日的禮儀之邦的失落。日本妄圖成為新的東亞盟主國,自甲午戰(zhàn)爭以來在國內(nèi)就不斷出現(xiàn)了“日本盟主論”和“中國亡國論”的論調(diào)[26]。在這樣的思想加持下,來華觀光的日本人都帶著強(qiáng)烈的優(yōu)越感,他們認(rèn)為中國一切不文明都是國家即將落后和即將滅亡的象征,并且他們企圖認(rèn)為曾經(jīng)老大帝國的失落需要日本人來拯救,日本對中國的侵犯是先進(jìn)文明對落后文明的宣戰(zhàn),結(jié)果是為中國人帶來幸福。
三.《中國游蹤》中的寧波風(fēng)景書寫
河?xùn)|碧梧桐在第一次進(jìn)行全國旅行時(shí),曾發(fā)表關(guān)于旅行的見解,一觀其景,二觀其古跡,三觀其風(fēng)俗,四觀其人情,五聽其傳說古碑,均融合為一[27]。而地方傳說是碧梧桐此番來寧波的重要原因。他曾在書中寫到:我來到寧波一是基于上海總領(lǐng)事有吉先生的推薦,二是因?yàn)榇说嘏c日本淵源最深,受到幾分好奇心的驅(qū)使[28]。與之對應(yīng),他在寧波部分的游記中多次提到諸如阿倍仲麻呂、榮西、道元、雪舟、慧鍔等日本古代與寧波有著深厚淵源的名人,游覽過的地方也都是與這些人有關(guān)的歷史遺跡。
碧梧桐對于寧波城內(nèi)的記載基本集中于他乘坐前往寧波的輪船時(shí),自己看到的甬江兩岸的風(fēng)景和人情,而他并沒有繼續(xù)在寧波城中觀光。到達(dá)寧波的當(dāng)晚碧梧桐一行人住宿在日本人開的旅社“中村酒店”,第二天便和友人一起前往與雪舟曾巡游過的天童山。
而碧梧桐在這短暫的輪船觀光中對于寧波的第一個(gè)印象便是甬江兩岸成片的墳?zāi)埂K@樣寫道:無論是眺望前方還是回看身后,盡是層層疊疊的小山。墳?zāi)拐媸橇钊苏痼@!這些土饅頭的數(shù)量也令人驚訝。無論中國人的死亡率有多高,無論這里記錄了多久的歷史,排列這么多的土饅頭就非常不容易。[29]碧梧桐看到這樣的景象除了覺得中國人本身愚昧迷信,還認(rèn)為這是中國人自私自利,沒有國家觀念的體現(xiàn)。他這樣寫道“一旦確定了埋葬靈柩的公墓,就會(huì)用土饅頭建起一個(gè)城,放眼望去是一望無際的土饅頭平原。徹底貫徹個(gè)人利己主義的中國人,在墓地上面也將利己主義貫徹到底了吧。[30]”而碧梧桐對于中國人“自私”這個(gè)特質(zhì)的提及,也反映了大正時(shí)期日本人對于中國人的整體印象。早在甲午戰(zhàn)爭時(shí)期,中國人文弱、貧窮、自私、不潔形象就深深扎根于日本民眾的思想。這樣丑化中國人的“自私”的一面,德富蘇峰曾在《七十八日游記》的“支那無國論”以及“病態(tài)的利己心”兩節(jié)中便大肆宣揚(yáng)過。德富蘇峰說“支那有家無國,有孝無忠,這是某位支那通的警句,今天的支那不僅沒有國家觀念,而且過去也沒有國家觀念之類的東西。[31]”他辱罵中國人是個(gè)人利益至上,缺乏公德心的國民。這種觀念在日本的傳播又助長了日本人蔑視中國人,而這也非常多的體現(xiàn)在日本人的旅華游記中。被麻痹了的日本公民大力支持政府侵華的行動(dòng),最后也導(dǎo)致日本人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
甬江之行途中,碧梧桐還發(fā)表了對于中國吸收西方文明,進(jìn)行近代化的看法“如今在新興地上海,從前的通商港口,貿(mào)易港急劇增加,說起來盡是不忍目睹的丑態(tài)。與唐宋明時(shí)期可以隨心所欲使用楷書文字的時(shí)代相比,如今世界的文明正發(fā)生著巨大的顛覆。[32]”從1868年明治維新起日本開始全面西化,但由于工業(yè)化的快速發(fā)展和文化的滲透,日本人無法準(zhǔn)確定位自己的民族的位置,對此在脫亞入歐浪潮中的日本知識(shí)分子也進(jìn)行了反思。夏目漱石于1911年11月在關(guān)西以“西方的開化是內(nèi)發(fā)的,日本現(xiàn)代的開化是外發(fā)的”為主題,發(fā)表了題為《現(xiàn)代日本的開化》的演講。夏目漱石說:“一言以蔽之,現(xiàn)代日本的開化是膚淺的開化。[33]”,并得出了日本的發(fā)展是外部壓力造成的結(jié)論。漱石認(rèn)為日本的近代化與其說是基于對西洋文明的理解而進(jìn)行的,不如說日本的文明開化只是單純地模仿了西洋文明。而夏目漱石也曾作為正岡子規(guī)的門生學(xué)習(xí)俳句,其對近代化的觀念一定程度上可能影響了碧梧桐。碧梧桐在游記中對中國上海一味地追逐西方近代化的現(xiàn)狀進(jìn)行批判的同時(shí),也包含著對日本自身的近代化發(fā)展和日本與西方關(guān)系的反思。
碧梧桐一行人在到達(dá)寧波當(dāng)天晚上住宿在“中村酒店”,第二天一早便懷著與雪舟同行的心情前往天童寺。碧梧桐一行人穿過被他形容為臟亂不堪的后街,乘上了一條垃圾船。此時(shí)他便感嘆道:“如果要去天童寺恐怕不管誰都要乘艘船吧。無論多想來一場奢華的旅行,這艘破敗臟亂的小船上肯定是沒有轎車和轎輦的。(中略)不管是道元、榮西還是雪舟,都一定搭乘過這條船吧。我不禁能想象到當(dāng)時(shí)他們被視為劣國國民,在乘客眾多的船上也只有一個(gè)小角落棲身。總之,如今我能夠租一條整船并且神氣十足地前往天童寺,憑此就必須感謝這個(gè)時(shí)代。[34]”
從想象中道元榮西“棲身于船的角落”到“租一整條船神氣十足”地前往天童寺的轉(zhuǎn)變,可以看出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通過戰(zhàn)爭的勝利,使得傳統(tǒng)東亞地緣政治中的中日主從地位,發(fā)生了根本性的顛倒,中日兩國的相互認(rèn)識(shí)也隨之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35]。日本國民沉浸在濃厚的蔑華氛圍之中,而這種意識(shí)都以文字的形式體現(xiàn)在來華旅游的文人旅記。
除了關(guān)于交通工具的感想,來到天童山少白嶺的碧梧桐路過“揖讓亭”時(shí)還記敘了關(guān)于這座亭子的傳說。
揖讓亭的來歷則是大慧宗杲禪師與正覺禪師在此地相遇,入亭暫憩時(shí),兩師謙讓不已。看到此情形的張安國不勝感動(dòng),說:“三代禮樂,今歸釋氏矣!”于是就為這個(gè)亭子寫下“揖讓亭”匾額。無論是揖讓亭名字的由來,還是看到此情形感嘆三代禮樂等等的故事,都仿佛是中國風(fēng)格的戲劇,十分有趣。[36]
碧梧桐的父親河?xùn)|靜溪是朱子派學(xué)者,老師正岡子規(guī)有著深厚的漢學(xué)基礎(chǔ),碧梧桐以先賢的經(jīng)歷為向?qū)韺幉ㄖ販赜^光,并且途中“十分有趣”的“揖讓亭”傳說的記述,都反映了他自身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認(rèn)同,而這也折射出日本近代知識(shí)分子身上共通的“中國趣味”。總的來說,來華的日本近代作家大都從小便受到中國古典文學(xué)的熏陶,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很高的評價(jià),并抱有濃厚的興趣。但是對當(dāng)時(shí)接觸到的中國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感到失望,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巨大差距使很多作家對現(xiàn)實(shí)的中國表現(xiàn)出蔑視、不滿的情緒,這與他們一直以來的觀點(diǎn)相悖,因而這一時(shí)期日本文人的游記中反映的中國觀都是復(fù)雜的、分裂的、矛盾的[37],這在稍晚于碧梧桐,于1921年來華參觀的芥川龍之介的《中國游記》中可見一斑。
碧梧桐在寧波的最后一站便是與慧鍔有關(guān)的普陀山,陪同旅行的是中村酒店的負(fù)責(zé)人兼吉君。與之前的論調(diào)均不同,碧梧桐眼中普陀山,是一座海中的孤島,風(fēng)景如畫,仿佛世外桃源。他這樣寫道:“這座海中的孤島處處都有像冰一樣澄澈的泉水涌出。無論是近海還是山頂,都有不會(huì)干涸的豐富水源。正因?yàn)槭怯^音的圣地,所以才出現(xiàn)了這樣的奇跡吧。這片中國海的方圓三四十里都漂浮著駭人的赤黃色泥土,而在這卻有一座春暖夏涼、處處涌出清澈泉水的小島。就如同污穢的礦渣中提煉出的一塊金子,讓人感到不可思議。[38]”
在普陀山上碧梧桐評價(jià)法雨寺的精進(jìn)料理頗有風(fēng)味,讓人感到身心放松悠然自得,更說道“普陀山之旅到此已經(jīng)是十分完美了。[39]”游覽這么多地方,為何碧梧桐會(huì)對普陀山所持的態(tài)度與其他地方迥然有異呢?總的來說,其原因可能在于普陀山的美景與清澈泉水更符合他所喜歡的風(fēng)景,這與碧梧桐自身所提倡的俳句“新傾向論”的主張殊途同歸。碧梧桐所代表的碧派倡導(dǎo)的俳句“新傾向論”與代表古典派的高濱虛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是否嚴(yán)格遵循俳句季題與十七字音限制。虛子主張要像能、歌舞伎那樣規(guī)范俳句,碧梧桐則主張吸收西歐文藝思潮,不受傳統(tǒng)季題和擺脫俳句格律制約。以西方自然主義為標(biāo)準(zhǔn),他認(rèn)為創(chuàng)作俳句應(yīng)擺脫人為的規(guī)制,不受束縛地表現(xiàn)自然[40]。而碧梧桐在記述普陀山時(shí)經(jīng)常提到這座受菩薩保佑的小島處處流露這自然原始的氣息,而此種不受人為因素干擾的自然,可能正是碧梧桐思想主張的具體體現(xiàn),也是其思想主張和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再確認(rèn)。
在中國旅行的近代日本人見到的中國,不是書本上間接的、或象征意義的中國,而是在實(shí)在的歷史空間里接觸到的現(xiàn)實(shí)中國。《中國游蹤》中的中國書寫就像一面鏡子反映出了近代中國在特殊歷史時(shí)期的真實(shí)面貌,形成以他者的視角來分析舊中國的近代化和國民性的重要參照系。而《中國游蹤》是河?xùn)|碧梧桐全部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本人的思想觀念也或多或少地滲透于游記中,也成為其作家研究的一條新路徑。
通過對《中國游蹤》中關(guān)于寧波書寫的研究,反映了河?xùn)|碧梧桐統(tǒng)一又矛盾的中國觀和對寧波的認(rèn)識(shí)。一方面,碧梧桐對于寧波風(fēng)景人物的評判始終沒有擺脫同時(shí)代日本對中國認(rèn)識(shí)的固有框架,始終統(tǒng)一于西方文明的標(biāo)準(zhǔn)之下。因此,碧梧桐他以高高在上的傲慢態(tài)度去再次確認(rèn)中國人早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眾心中的不潔、自私、迷信、落后的形象,這也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日本人思維中強(qiáng)固的蔑視型中國觀。與之相對,因?yàn)槠胀由降娘L(fēng)景符合西方自然主義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故而碧梧桐又喜愛這座與他主張的“新傾向論”志趣相似的海上孤島,這也是對其自身文人身份與審美觀念的再次確認(rèn)。另一方面,碧梧桐追隨日本先賢的腳步來到寧波,體現(xiàn)了他自身的漢學(xué)修養(yǎng)和對古中國文化的認(rèn)同,但是這種日本近代知識(shí)分子身上共通的“中國趣味”在面對現(xiàn)實(shí)的中國社會(huì)時(shí)產(chǎn)生的巨大差距,又使得他的文字中所反映的中國觀是復(fù)雜且矛盾的,而這一點(diǎn)也折射出近代日本來華文人的主流心態(tài)。
參考文獻(xiàn)
[1]安善花.近代日本中國觀的變遷及其東亞強(qiáng)國地位的確立[J].日本學(xué)論壇,2008(03):55-60.
[2]復(fù)旦大學(xué)文史研究院編.中國的日本認(rèn)識(shí)日本的中國認(rèn)識(shí)[M].中華書局,2015.
[3]荊曉霞,李莉娜,孫立春.明治、大正時(shí)期日本文人的杭州游記研究——以內(nèi)藤湖南、河?xùn)|碧梧桐、青木正兒、村松梢風(fēng)為中心[J].語文學(xué)刊(外語教育教學(xué)),2016(05):71-73.
[4]高潔.佐藤春夫《南方紀(jì)行》的中國書寫[J].中國比較文學(xué),2012(04):113-123.
[5]葛元煦.滬游雜記卷1[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李鈴.明治時(shí)期日本人中國游記中的中國認(rèn)識(shí)研究[D].北京外國語大學(xué),2021.
[7]李煒.都市鏡像近代日本文學(xué)的天津書寫[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8]劉亞男.河?xùn)|碧梧桐的“無中心論”[D].河北大學(xué),2020.
[9]彭恩華.日本俳句史[M].學(xué)林出版社,1983.
[10]宋協(xié)毅.日本俳句的歷史、現(xiàn)狀及其發(fā)展趨勢[J].日語知識(shí),2001(04):24-26.
[11]楊棟梁.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M].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12]尹曉亮.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對華行動(dòng)選擇[J].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人文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49(02):49-50.
[13]鄭民欽.日本俳句史[M].京華出版社,2000.
[14]阿部喜三男.河?xùn)|碧梧桐[M].東京:南雲(yún)堂桜楓社,1964.
[15]瓜生敏一.阿部喜三男氏著「河?xùn)|碧梧桐」[J].連歌俳諧研究,1965(28):41-42.
[16]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huì).近代日本思想史第3巻[M].東京:青木書店,1956.
[17]近藤直美.1900年代以降の日本人の中國観の変遷について[J].経済史研究,2011(14):197-203.
[18]正津勉.忘れられた俳人河?xùn)|碧梧桐[M].東京:平凡社,2012.
[19]田部知季.剣花坊·日露戦爭·碧梧桐[J].日本近代文學(xué),2018(99):33-48.
[20]東アジア近代史學(xué)會(huì).日清戦爭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上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
[21]徳富蘇峰.七十八日遊記[M].東京:民友社,1906.
[22]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9卷[M].東京:漱石全集刊行會(huì),1925.
[23]博文館.日露戦爭実記(47)[M].東京:博文館,1905.
[24]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臺(tái)灣:霧社事件·植民地統(tǒng)治政策の研究[M].東京:藤原書店,2008.
[25]藤田昌志.日本の中國観―明治時(shí)代―:日中比較文化學(xué)の視點(diǎn)[J].三重大學(xué)國際交流センター紀(jì)要,2015(10):46-61.
[26]山本健吉.明治文學(xué)全集第56高濱虛子,河?xùn)|碧梧桐集[M].東京:筑摩書房,1967.
注 釋
[1]彭恩華.日本俳句史[M].學(xué)林出版社,1983:86.
[2]鄭民欽.日本俳句史[M].京華出版社,2000:118,128,135.
[3]荊曉霞,李莉娜,孫立春.明治、大正時(shí)期日本文人的杭州游記研究——以內(nèi)藤湖南、河?xùn)|碧梧桐、青木正兒、村松梢風(fēng)為中心[J].語文學(xué)刊(外語教育教學(xué)),2016(05):71-73.
[4]劉亞男.河?xùn)|碧梧桐的“無中心論”[D].河北大學(xué),2020.
[5]阿部喜三男.河?xùn)|碧梧桐[M].東京:南雲(yún)堂桜楓社,1964:1.
[6]瓜生敏一.阿部喜三男氏著「河?xùn)|碧梧桐」[J].連歌俳諧研究,1965(28):41-42.
[7]田部知季.剣花坊·日露戦爭·碧梧桐[J].日本近代文學(xué),2018(99):33-48.
[8]阿部喜三男.河?xùn)|碧梧桐[M].東京:南雲(yún)堂桜楓社,1964:47.
[9]原名《支那に遊びて》,“支那”是近代日本對中國的蔑稱,抗美援朝戰(zhàn)爭后逐漸廢止。此書尚無中文譯本,本稿中采用李煒《都市鏡像:近代日本文人的天津書寫》中對本書題目的譯文。另外,文中引用的《中國游蹤》原文均為筆者拙譯。
[10]阿部喜三男.河?xùn)|碧梧桐[M].東京:南雲(yún)堂桜楓社,1964:84-85.
[11]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1-2.
[12]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4.
[13]本稿中的提到的寧波范圍,除了2022年寧波市轄范圍的六區(qū)二縣二市之外,也包括1918年河?xùn)|碧梧桐來中國時(shí)屬于寧波市管轄范圍內(nèi)的普陀山。
[14]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09.
[15]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36.
[16]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34.
[17]東アジア近代史學(xué)會(huì).日清戦爭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変容上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392.
[18]博文館.日露戦爭実記(47)[M].東京:博文館,1905:25.
[19]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と臺(tái)灣———霧社事件·植民地統(tǒng)治政策の研究[M].東京:藤原書店,2008:176.
[20]楊棟梁.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M].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79.
[21]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198.
[22]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197.
[23]葛元煦.滬游雜記卷1[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
[24]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199.
[25]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01.
[26]楊棟梁.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M].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99.
[27]正津勉.忘れられた俳人河?xùn)|碧梧桐[M].東京:平凡社,2012:54.
[28]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08.
[29]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194.
[30]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195.
[31]徳富蘇峰.七十八日遊記[M].東京:民友社,1906:232,260.
[32]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01.
[33]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9卷[M].東京:漱石全集刊行會(huì),1925:881.
[34]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10.
[35]楊棟梁.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M].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102.
[36]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14.
[37]孫立春.日本近現(xiàn)代作家訪華游記研究[M].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6:36.
[38]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37.
[39]河?xùn)|碧梧桐.支那に遊びて[M].大阪:大阪屋號(hào)書店,1919:236.
[40]山本健吉.明治文學(xué)全集第56 高濱虛子,河?xùn)|碧梧桐集[M].東京:筑摩書房,1967:378.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指導(dǎo)老師:李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