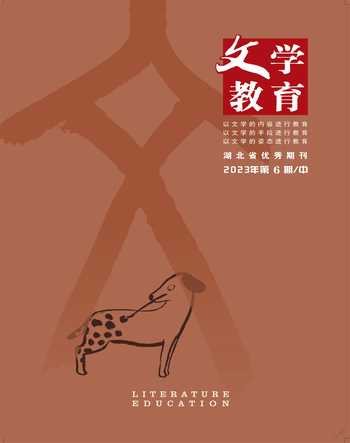日本能樂與“幽玄”觀演變
趙昕
內容摘要:能和狂言是日本傳統的古典戲劇代表,二者合并起來稱為能樂。在其一千多年的發展歷史中,經過反復凝練、升華為極具“幽玄”性質的獨特曲藝。“幽玄”作為日本文藝理論和傳統美學的范疇之一,往往被闡釋為“微暗、朦朧、神秘、難以知曉的微妙境界”等,是富含日本民族特色的美學代表。能樂與“幽玄”觀的演變相互糅合,交錯發展,將演出和理論結合,不僅形成了輝煌的藝術成就,而且對于現代音樂、文學等領域也有著巨大的影響。
關鍵詞:能樂 幽玄 日本美學
日本的能與狂言、文樂、歌舞伎并稱為日本四大古典戲劇。能作為一種傳統的日本藝術表演,和狂言一同發源于日本南北朝時代,合起來統稱為能樂,經歷多次變遷和革新延續到現在,可謂世界上擁有最長的戲劇生命和歷史傳統的舞臺藝術,在2001年被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能樂有獨特樣式的能舞臺,像世阿彌所言“舞歌二道”一樣,是融合了用精妙的演技抽象化的舞蹈要素和歌謠、伴奏等音樂要素的戲劇。而自世阿彌即能樂大家世阿彌元清著《風姿花傳》以來,能樂作為一種特殊的舞臺演劇其藝術性首次被詳細整理論述,世阿彌指出能樂的本質即模仿、花和幽玄,能樂即是與之修行的過程。中世,能樂在足利氏將軍的幕府庇護下逐漸發展壯大,盛極一時。但無論是中世祭祀春日神社的大和四座流派還是后來江戶的新興喜多派,伴隨著他們的“幽玄”能樂美學理論卻一同演變至今。
早在奈良時代,我國唐朝的唐樂隨著大量漢文化的輸入也登入了日本貴族的雅堂。唐樂中,與雅樂相對應的俗樂稱為“散樂”,主要是以曲藝、雜技、魔術、歌舞等為主的各式各樣的表演藝術。到了平安時代,散樂中滑稽而令人捧腹的模仿藝術漸漸成為主流并在庶民之間流行起來,被稱為“猿樂”。與之相對,在農村農民們在田地耕作時,有表演農耕祭祀和禮法的“田樂”。這兩者不久間也在貴族階級之間流行起來,特別在室町時代受到了幕府將軍和武士的喜愛。后來,“猿樂”和“田樂”被加入了歌舞伴奏和角色對話,成為一種對話劇并被稱為“猿樂能”和“田樂能”,也就是今天所謂能樂的起源。中世,因佛教廣泛傳播,經常伴隨著大寺院法會和神社祭禮的藝術表演逐漸興盛,尤其在鐮倉時代末期,這些宗教藝術表演者自發結成“座”這樣的集團,從屬于有權勢的大寺院,比如當時最有名的“大和猿樂”和“近江猿樂”兩座。
“猿樂”的表演者擔當的表演內容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在寺院的法會上上演念咒,一是扮作老翁的樣子演示神的祝福,也是現在被視為神圣的屬其他系列演劇《翁》的原型。到了南北朝時期,“大和猿樂”和“近江猿樂”已發展至多種支流派系。其中“大和猿樂”包括隸屬于奈良興福寺的圓滿座、阪戶座、外山座、結崎座這四座,侍奉于春日神社,也就是今天的金春、金剛、寶生、觀世流派的起源。再到了江戶時代,能作為一種成熟的藝術形式,成為了幕府官署正式的式樂,表演更加凝練考究,曲目數量達到二百四十曲之多。能每日正式的表演從形式和內容上一般分為叫“五番立て”的五種類型,也就是神事物、修羅物、蔓物、現在物、鬼畜物這五種依次表演的順序[1]。此外,除了大和四座之外,還形成了新的喜多流,這“四座一流”統歸江戶幕府管轄,一直延續至今。
創立了能樂這一完全嶄新類別的戲劇的是曾組織過結崎座的觀阿彌清次和世阿彌元清父子二人。觀阿彌對能的功績在于對以模仿為本位、主張猛烈風格的大和猿樂中,改編加入田樂和近江猿樂等歌舞的要素和把幽玄之美放到中心位置,另外還要把節奏本位的曲舞的技法導入到以旋律為主的大和猿樂當中,寫出吸引大眾的活潑生動的能本。世阿彌吸收了近江猿樂的名人犬王道阿彌的唯美主義,在大和猿樂戲劇性本位的基礎上,確立了以幽玄的情趣為中心的詩劇類能及其理論。在世阿彌的能樂論中,主張與強硬猛烈的表現相反,變現優雅、柔和、典麗的美。不僅有存在于美女、美少女等具備自然的幽玄,甚至有具備卑賤的人物、鬼等演出來的高深的幽玄[2]。要理解世阿彌的幽玄美,則必須了解幽玄這一思想的演變與發展。
幽玄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國后漢時期,記載在《后漢書·何后妃》中漢少帝的《悲歌》中:“逝將去汝兮適幽玄。”[3]而在隋朝漢譯佛典《金剛般若經疏》中,智顗將這個詞解說為“微妙難測”,唐朝的法藏在《華嚴經》中解說為“甚深”[4]。無論哪種解釋都意為佛法深遠,不易理解。幽玄一詞傳入日本后有所改變,在平安末期已經不只限于佛典使用,但也幾乎不離原意。此后幽玄大都醒目地出現在歌論的場合,被賦予了新的不同的含義。紀貫之在《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把幽玄用在日本的詩歌評論中,“或事關神異,或興入幽玄”,由此把“幽玄”引入文藝批評,隨著日本和歌的創作漸趨成熟,和歌也明顯表現出輕言辭而重意境的“幽玄”詩趣。
日本的和歌名人藤原俊成認為日本當代歌人應該把自己置于歌學的傳統之中,而和歌的這種傳統猶如佛門《天臺摩珂止觀》的金口相承,萬古不易。今人應該了解和歌的歷史,尤其應該了解和歌的“姿、詞”的變遷,了解在其變遷中保持永恒不易的普遍意義上的美的諸相。歌人只有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牢固地確立發現這種普遍美的主體性才能創作出“風體幽玄”的上乘之作。我國學者高文漢認為:“俊成倡導的‘幽玄已與壬生忠岑等中古歌人之說有所不同,他努力使和歌的傳統美進一步內潛、深化,旨在尋求一種深邃、靜寂的氛圍和意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韻味清幽、余味綿長的復合性情調美。同時他強調和歌的聲調視其為和歌的生命。”[5]在《古來風體抄》中,他說:“凡歌者,頌于口詠于言也,故應有艷麗而幽古之聲。”其子定家不僅繼承了他的這些觀點,而且又進一步發展了他的歌學理論。
藤原基俊在《作文十體》中賦予“幽玄”深邃和悠遠的余情,幽玄開始接近余情。后來藤原正徹以“幽玄”作為詠歌的最高理想,他的歌論以禪的精神深化了藤原俊成、定家的幽玄理論。他在《正徹物語》中寫道:“幽玄者,人人內心應有,進而用詞表達出來,心里應有鮮明的理解,只把漂泊之體稱作幽玄體。”他用“心中萬般有”的禪的精神強調了幽玄的“有心”,使幽玄帶有一種異端的飄渺感,一種無邊無際的心靈宇宙。所以,“幽玄”不僅僅局限于感覺上,而是發展成一種精神性、內在性,達到了“有即是無,無即是有”的超越意識的幽玄世界[6]。他又在《正徹日記》中解說:“所謂幽玄,就是心中去來表露于言詞的東西。薄云籠罩著月亮,秋露灑落在山上的紅葉上,別具一番風情,而這種風情,便是幽玄之姿。”因此,幽玄是由朦朧和余情兩大因素構成,形成難以用言辭表達的超越現實具象的神妙意境。這樣,定家和正徹等人就把幽玄理解為朦朧、隱約、含蓄、悠遠、空寂和余情之美。
大西克禮在《幽玄·物哀·寂》中進一步闡釋了“幽玄”的含義,他認為“幽玄”有七重。第一,“幽玄”意味著審美對象某種程度上被隱藏、遮蔽、不顯露、不明確;第二,“幽玄”是“微暗、朦朧、薄明”,這是與“露骨”“直接”“尖銳”等含義相對立的一種優柔、委婉、和緩;第三,是寂靜和寂寥;第四,是“深遠”感,它往往意味著對象所含有的某些深刻、難解的思想(如“佛法幽玄”之類的說法);第五,是“充實相”,是以上所說的“幽玄”所有構成因素的最終合成與本質;第六,是具有一種神秘性或超自然性,指的是與“自然感情”融合在一起的、深深的“宇宙感情”;第七,“幽玄”具有一種非合理的、不可言說的性質,是飄忽不定、不可言喻、不可思議的美的情趣。[7]“‘幽者,深也、暗也、隱蔽也、不明也;‘玄者,空也、黑也、暗也、模糊不清也。”[8]對日本傳統美學研究大家王向遠也對此重新作出解釋。“幽”“玄”二字并置,在一定程度上是近義的重復加強,也各有獨特內涵的闡釋,更強化了該詞深邃、神秘、曖昧、模糊、不可名狀的氣氛與境界。而在日本,隨著日本文學中“最純粹的民族形式”——和歌體系的建立,日本人漸漸構建了蘊含著強烈獨立意識、有意與漢民族文學創作相區別的審美批評體系,他們在中國主流的詩歌體系之外,摘取了“幽玄”這一抽象概念,賦予它最高的統率地位,指導著和歌、能樂等等諸多文學樣式的創作。通過文人及其作品的不斷闡釋、演繹、豐富,給予了“幽玄”一詞更為廣闊的解讀空間和更為哀切動人的感染力,“幽玄”最終成為了日本民族美學顯著的特征。
在日本歌道創作、實踐、批評體系基本成熟之后,“幽玄”的理想已然融入到了各種文學樣式的創作理想之中——世阿彌在其一系列能樂理論著作中,都反復強調著“幽玄”的追求,這一取向體現在他創作的方方面面,都要力求“幽玄”化。能樂的前身猿樂,滑稽可笑,難登大雅之堂,在世阿彌看來,如果不將其脫去低級趣味,進行高雅化、貴族化的處理,能樂難以成為一門真正的藝術。在論及藝術的主體時,世阿彌在《至花道》中指出:“觀賞藝能之事,內行者用心來觀賞,外行者則用眼來觀賞。用心來觀賞就是體。”[9]此處“體”可以理解為本體、主體。可以說“幽玄美”,作為世阿彌理論的中心,不僅僅局限于感官上美的刺激,更要生發出一種內心的審美體驗,是精神上、向內散發的美。
就能的藝術性而言,美即幽玄,幽玄即美。這種美是集“柔、麗、雅、順”為一體的美,是演員余生俱來的一種氣質。世阿彌在《風姿花傳》寫道:“少年之舉皆美”、“人中女官、宮女、娼妓、好色、美男子,草木中花類,如此種種,其形皆幽玄之物。”[10]在舞臺藝術方面,扮相逼真,形同神似即謂幽玄,世阿彌一改觀阿彌時代“模仿表演為主”的傳統形式為置能的舞蹈和音樂因素于表演之上的藝術形式,使能成為極富戲劇性、象征性的獨特的舞臺藝術。
能的劇本即謠曲。謠曲大多在《源氏物語》、《平家無語》等古典文學或民間傳說中取材,尤其是在古代和歌和文章的基礎上,使用緣語掛詞等技巧修飾點綴,形成韻、散文相互交織的華麗七五調文章。謠曲充滿幻想象征性的幽玄之美的同時又能達成劇本演出的效果。謠曲作者大多是能樂演員自己本身,創作沿襲觀阿彌和世阿彌的能本或其改編。世阿彌稱能的美麗和趣味為“能之‘花”,“花”意為能的趣味、新奇。與幽玄之美相對應,能應具備從“時節之花”到“妙花風”也就是從感官上的美到無心無位的美的豐富性和深奧性。而“年年來去之花”就是兩者的和諧統一。[11]四川大學何春蘭認為此處的“花”是能樂的生命,它的形象象征著一種藝術魅力,是能樂的精髓所在。要想在表演藝術上取得成功,就必須要有“花”,從而達到“闌位”的最高境界。對于什么是“花”,世阿彌在《風姿花傳》中寫到:“感動、有趣、新奇此三者同為心也”。在他看來,“花”就是要不斷地磨練自己精湛的演技,懂得怎樣給觀眾帶來新奇感和視覺上的沖擊,即強調它的感染力。因此他大力批判粗糙露骨的下品味的表演,提倡幽遠清寂、典雅含蓄的上品味的幽玄美意識[12]。
能樂對后世文學文化的影響之巨不言而喻。在能的開創期,上演了很多與歌舞伎的世界相近的戲劇性曲目,不久夢幻能占據了能樂首位,但隨之而來也迅速從能的世界淘汰,其戲劇性的性質就這樣轉移到了凈琉璃和歌舞伎。將能原封不動地轉化為歌舞伎的《勸進帳》《紅葉狩》等“松羽目物”,雖有從幕末一直發展到昭和的軌跡,但能的《翁·三番叟》、《道成寺》等還產生了在近世以后的舞蹈、邦樂等很多流派。在文學與藝術方面,《閑吟集》中記載了很多能的詞章、狂言歌謠,而江戶時代謠曲的流行,起到了為古典文化總括簡編的作用,為俳諧、川柳、假名草子、讀本等提供了題材。松尾芭蕉說,謠曲是俳諧的《源氏物語》,也就是原著。近松門左衛門和井原西鶴的文學也大量利用了謠書中的句子。泉鏡花、郡虎彥、野上彌生子等人也有從能樂中取材而寫成的作品,三島由紀夫的《近代能樂集》也在西歐上演。愛爾蘭的耶茨受到能樂啟發寫了一部的《鷹之井》,后來被反進口成為了新作能樂。此外,能樂對現代音樂、電子音樂也產生的巨大的影響也是不容置否的,“幽玄”在現代其意義上的豐富也有待當代人的進一步挖掘和升華。
參考文獻
[1]肖霞.日本文學史[M].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
[2]周建萍.“幽玄”范疇的審美闡釋[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05(4):52-54.
[3]高文漢.日本中世文論[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4):93-96.
[4]陳雯蓓.試論世阿彌能樂中的美學特色[J].長江文藝評論,2020(6):122-123.
[5]王向遠.釋“幽玄”——對日本古典文藝美學中的一個關鍵概念的解析[J].廣東社會科學,2011(6):90-96.
[6]王向遠.論日本美學基礎概念的提煉與闡發——以大西克禮的《幽玄》、《物哀》、《寂》三部作為中心[J].東疆學刊,2012(3):1-7.
[7]宿九高.集能藝術之大成 開能理論之先河——世阿彌及其《風姿花傳》[J].日語學習與研究,1997(9):54.
[8]邱紫華.日本美學范疇的文化闡釋[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1(1):58-76.
[9]何春蘭.論日本能樂中的幽玄美意識[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7):91-92.
注 釋
[1]肖霞.日本文學史[M].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
[2]肖霞.日本文學史[M].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
[3]周建萍.“幽玄”范疇的審美闡釋[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05(4):52.
[4]日本大百科全書[Z].小學館,2001.
[5]高文漢.日本中世文論[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4):94.
[6]周建萍.“幽玄”范疇的審美闡釋[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05(4):52-54.
[7]陳雯蓓.試論世阿彌能樂中的美學特色[J].長江文藝評論,2020(6):122-123.
[8]王向遠.釋“幽玄”——對日本古典文藝美學中的一個關鍵概念的解析[J].廣東社會科學,2011(6):90-96.
[9]陳雯蓓.試論世阿彌能樂中的美學特色[J].長江文藝評論,2020(6):123.
[10]宿九高.集能藝術之大成 開能理論之先河——世阿彌及其《風姿花傳》[J].日語學習與研究,1997(9):54.
[11]肖霞.日本文學史[M].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
[12]何春蘭.論日本能樂中的幽玄美意識[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7):91-92.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