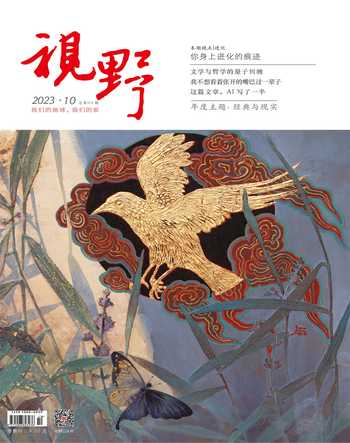被親情傷害的我,在別人家學習“正確表達”
群青色

在我們家二樓,曾經有一戶住戶一住就是好多年,直到最近才搬走,可謂是我家最長時間的鄰居。雖然他們搬走了,但我還時常想起他們在的時候。盡管在現代的都市文明熏陶下,即使是相處時間最長的鄰居,也不過是見面會微笑點頭的“君子之交”,但每次上下樓的時候,我總能從他們家那扇常年敞開的門中窺見一些“別人家的生活”。
這一家人有老有小,日子過得并不富裕——每次上下樓梯,都能看見門里家具寥寥的客廳,是拖得埕亮的地板也掩蓋不了的空蕩——吃飯的桌子折疊好靠在墻邊,以及客廳一角堆成小山一樣的五顏六色的兒童玩具。
每每看到這幅場景,我的內心總是閃過一些微妙的感覺。
小時候,我對自家的感覺應該可以概括為兩點:忙碌、貧窮。父母一年到頭忙著干活,并且喜歡用“家里很窮”來教育孩子們要懂得節約勤勞。家務常常是疏于打理的,一些對孩子們來說較為難做的會交由母親,剩下的則由幾個孩子平攤。半大的調皮孩子的家務活實在不能說做得好,常常是做到一半就已經開始不耐煩,心飛到更遠的地方去了。久而久之,許多物品隨意擺放在家里的每個地方,有些使用頻率低的更是像披上了“隱形衣”,在家庭成員的視線范圍內自動消失,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會適時展現。
父母勞累一天回家,心里還帶著火氣,看著幾個正處于上房揭瓦年紀的孩子蹦蹦跳跳,心情就更為暴躁。于是飯桌上的談話往往變成嚴肅的“領導訓話”甚至批評指責,溫馨的餐桌氛圍,對我們來說是在課本上、文字里、別的孩子口中的遙遠的生活。
至于純粹屬于孩子玩樂的東西則更少。父母是不折不扣的實用主義者,即使是孩子們想買書,也得再三盤問清楚所買的書與學習的關系;純粹娛樂性質的玩具更是低級幼稚,不僅不配人們花費血汗錢購買,更會對家務整理造成不必要的負擔。
于是,我對家的最初模樣也就這樣形成了:物品被隨意地擺放在各種地方,有些久未使用已經漸漸蒙上了灰,屬于孩子們的東西與大人的并沒有什么不同,書,衣物,一些日常用品,透露出一股嚴肅的氣息,卻又散發著矛盾的對生活的漫不經心來。
回想起來,那股對生活的隨意的漫不經心,或許是來源于我們的父母也并未真正將那里當作我們的家——因為工作的關系,我們搬過好幾次家。對于他們來說,那也許只是一個落腳處。
但在那個時候,在現在的很多時候,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將這一切歸咎為貧窮和忙碌。
記得有一次陪媽媽在一條早些年很繁榮現在早已沒落的夜市逛街,我們走到一家老舊的服裝店,一股“古早”的氣息撲面而來:各式各樣的男裝看不出款式密密麻麻地堆疊在晾衣桿上,只布料泛出廉價而亮眼的光澤;掛在墻上的倒是款式一目了然,但浮夸的印花如補丁一樣左一個右一個地釘在衣服的各個角落;冷調的白光陰慘慘地鋪瀉而下,更是給本就所剩無幾的購買欲重重一擊。店主是個女人,正窩在柜臺上百無聊賴地刷短視頻,即使有客人來了,也提不起她的興致。而店鋪的另一個角落則擺放著一張中小學里常見的課桌——仿木紋膠層桌板以及掉漆的鐵桌架——一個同樣歪著身子的小男孩正伏案寫作業。在他的身后,還堆疊著如山的密密麻麻的紙皮箱子和小學的舊課本,想必是積攢著要賣出去的廢品。
一種久遠的熟悉感讓我一陣恍惚,仿佛還帶著塵封的灰塵味道。但我已經有將近十年沒有踏足過這條業已衰敗的商業街,生平所歷更是和服裝售賣毫無關系。我有些困惑,直到那些等待回收的卷邊的老舊課本與記憶中屬于我的每一次被回收的小學課本重合。
原來讓我熟悉的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把當下只當成不得已而為之的短暫停留,因而對生活顯現出一種疏于經營的漫不經心的懶怠。
而我的鄰居帶給我的是另外一種顛覆:不富裕,但井井有條,尤其是那小山似的兒童玩具不經意中透露出來的對孩子的關愛,無一處不透露出對生活的細致和溫馨。
偶爾,我到街上拍照。事后往往發現,能令我觸動的也是一些“野蠻生長”的場景:牽牛花藤纏繞著灰撲撲的久未使用的水泥攪拌車;夜晚老舊居民樓陽臺上隨意擺放著清潔工具以及大咧咧地懸掛著的未干透的衣服,但一棵張牙舞爪的綠植垂下長長的枝條;一面被丟棄的穿衣鏡碎裂在地上,鏡面倒映著夏日碧藍的晴空以及蔓長的野草;一輛鋪載滿水果的車子,旁邊是一張鮮紅色塑料椅,守攤的老爺爺坐在其上,而在這些背后,是寬闊的六車道川流不息的車輛和行色匆匆的路人……
一切充斥著人的痕跡的,看似荒涼破敗而又生機勃勃的,都使我著迷。
隨著認識的人越來越多,見識過的生活模樣也更加豐富,我早就明白對生活的懶怠并不總是與貧困、忙碌“捆綁銷售”,父母小時候對我們耳提面命的“家庭貧困教學”更多地只是想讓孩子們明白父母的辛苦。而我們家也早已一改從前四處奔波的狀態:父母的脾氣比從前更加溫和;家里換了整潔的新裝修,一磚一木,所有布局擺設都由家庭成員共同完成;天臺上栽種著好幾種不同的月季,我能聞出每種月季散發香味的微妙不同;客廳常亮著暖黃的燈光,擺放著父親喜歡的全套茶具,哥哥喜歡的智能家居……一切欣欣向榮,溫馨而細致。
但那種著迷卻沒有消失。
鄰居家那扇敞開的門時不時鉆進我的腦海里。
門內是另一個隱秘的世界:如同老宅子門口盛開著的不名貴卻燦爛的報春花,過著苦日子的人們端午節家門口懸掛著的艾草,透出的讓人羨慕的忙碌和困苦也無法消除的溫柔特質。
也許人們所說的“觸及心靈的美感”,不過是在挖掘、重復生命最初尚未來得及咀嚼弄透,卻又留下明顯痕跡的一切?又或者我只是單純地羨慕著那種回不去的關愛和溫柔?
據說有童年缺憾的人往往在成年以后會出現過度自我補償的心理:一個被嚴格管控零食的孩子,能夠自由支配錢財以后往往過度購買零食;缺愛的人總是要證明自己有被愛的價值;一個有困苦潦倒童年的人可能會變成一個守財奴。兒時發生的重大事件,總會以我們自知或不自知的方式影響著我們的選擇。但發生的一切無法重來,錯過的成長也已永遠錯過,只有缺憾一直留在心里,等待著日后漫長的消化和理解。
當我一次又一次以現在的自我去代入當年的父母,真正以成年人的姿態在心中和過去的他們對話時,那些曾經讓人受傷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再引起我的應激反應,我也早已不把父母當作全能的神,認為他們應該給孩子提供全身心的愛護而不犯一點錯誤。但某些片段卻仍在特定的時候在我的腦中閃回。
也許在我一次又一次看向鄰居家那扇半開著的門的時候,我最希望的,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可以推開門,向我走來,對我訴說他們的生活,好讓我知道,那一切是不是只是我的美好想象。接著,那些成長過程中所發生的困惑、遺憾、埋怨,都可以有一個合適的參照系,得到合理的解釋和安置。
直到今天,即使我和父母的關系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童年沿襲下來的相處模式仍然在影響著我,更影響著我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看法:孩子的喜惡、煩惱不過都是不值一提的小打小鬧,過分活潑的性格則應歸為惡劣,且看上去充滿了對父母辛勞的漠視,應予矯正。意識到這一點后,我們便不再與父母訴說任何生活中的小事,無論是喜悅還是成長過程中遇到的煩惱。而父母則嚴肅慣了,加上對孩子知之甚少,即使偶爾興致來了,想要和孩子交談,也找不到什么話題,于是只好將學業、工作、婚姻幾件人生大事祭出來,輕松的交談變質為嚴肅的說教,更加激起了孩子的緊張感和逃避欲。
越是親近,越無法正確、坦誠地表達,而以互相指責為首的錯誤表達則“暢通無阻”,這樣不健康的關系惡性循環,時至今日仍然保留著巨大的效力。但我仍想看清楚看似糟糕的表面下真實隱藏著的對彼此的感情,而我仍在學習的,是找到一種自然不別扭的方式,讓一切得以正確表達。
(油畫摘自微信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