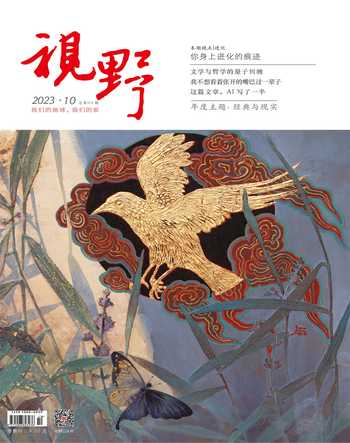假期往事
柳生春

工作之后會特別羨慕有寒暑假的人,寒暑假就像我們的理想國,在那個國度,可以做在操場上想做卻無法做到的很多很多事情。我們不需要面對那些熟悉的同學和老師凌厲的目光,可以暫時忘了作業和遲到,會遇到同姓不同輩、干活不怕累的新伙伴。
我在縣城長大,上學的時候和發小玩,放假了就被送回老家和爺爺奶奶同吃同住。老家里有五畝果園、三畝田,果園里有各種果樹,田里種的是玉米、麥子和稻子,還有的就是一群年紀、輩分各不相同的“親戚們”。
收麥子、掰玉米的確很臟很累,摘蘋果、打棗子卻也著實開心熱鬧,干完活后,一瓢清甜的井水,一碗地三鮮拌面,頓時會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這一切只為你吃得更香更爽。
月色透亮的回家路上,回想著方才的鬼故事,腳步飛快,但好在離家不遠,還有月光陪伴,便不覺害怕。
夏日田間,晚風吹著玉米葉子“唰唰”作響,這響聲,在傍晚時柔和斯文,玉米和人們都享受著涼爽和愜意;到了深夜,便是凄厲狂飆,玉米之間摩擦不斷像是在打架,讓人膽戰心驚。冬天雪后,望著田野上“白茫茫一片真干凈”,也會感嘆純潔和荒涼不過是極致的統一,而這些,卻是大地的被子,為她保暖,為春天而來。
統統這些,構成了活色生香的理想國度,也正是我們無比懷念的暑假寒假。
暑假正值盛夏,各種水果、植物、動物競相爭艷,好吃的好玩的比較多,金木水火土都給占全了。洗澡游泳打水仗,摸魚上樹搗鳥窩,偷果子烤蘋果烤玉米,和泥捏盤子和罐子,走在田間路上渴了餓了就隨手摘個柿子和黃瓜,集體打場就是變工許諾的兌現。在涼爽寬大的炕上翻來滾去,窗外不遠的楊樹樹影婆娑,房頂上的星星和蚊子一樣多,夜色雖美卻要付出“血”的代價。
寒假,分為過年之前和過年之后,三個字可以概括:吃、睡、賭。年前大多也都是為了過年做準備,烤饃饃,鹵肉,炸面蛋蛋做夾板。過年期間,似是無聊,扎金花、打麻將、砍牛腿都不是我可以玩的,只能在一邊應和驚呼過過眼癮。年過罷,就要趕作業了,為的是能輕輕松松舒舒服服地在正月十五看煙花。
托饃饃
我一直覺得年前的聚會,才是最最開心的團聚,一起為年后的“懶惰”忙忙碌碌、各司其職,固然累,但都明白苦盡甘來,憧憬著即將到來的過年大聯歡,我想這也是苦難生活的意義所在吧。
年前除了做肉,就是做饃饃,不是電烤箱,而是生鐵鑄成的托盤,所以我們叫“托饃饃”。托盤為圓形,由上下兩部分組成,外加一副長鉤子。下托盤是放饃饃用的,相對深一點;上托盤是放火用的,火料是耐燒的大粗木棒子,還有兩個耳朵。長鉤子掛在耳朵上移動上托盤,用來查看饃饃的情況,判斷火候。
托饃饃前,先打爐臺,爐臺的材料是“土垡子”(沒找到合適的詞,形狀是長方形土塊),材質和炕面子是一樣的,黃土麥秸和成泥,堅實耐燒。留一個燒火口,留一個煙囪口,下托盤固定則在爐臺上。然后就是準備火料,爐洞子需要的是易燒的干柴草,一般是麥秸或稻草,每開一爐,就點一把柴草,目的主要是保持爐底的溫度不要過低;上托盤需要的是耐燒的粗木棒子,是托熟饃饃的主要火力。
爐子支好了,同步開始制作的饃饃也準備好了。常做常吃的有三種,分別是托羅子、蜜轉子、棗旋子。
托羅子,這個名字我是至今也不曉其涵義,可能是最早的一種用托盤托出來的饃饃吧,所以就和托盤一個姓氏了。托羅子也確實符合早期饃饃的特質,為的就是填飽肚子,沒有花里胡哨的造型,就是單純的面和油,和托盤一樣的圓形,一面用專用的小鑷子組合捏出一些花紋,整體和新疆的馕很像,沒有馕那么大那么扁,而是會飽滿和軟和一些。剛出爐的托羅子散發著最原始的面香,夾雜著木柴的煙火味,外邊的酥脆和內里的柔軟都恰到好處。因為不甜且沒有餡,小孩子們都不喜歡吃,老人們則依舊喜愛,我也是在餓了又沒選擇的時候才會拿起托羅子。現在縣城本地大超市還可以買得到托羅子,不過是烤的,沒有托盤的味道,似是丟了靈魂。
蜜轉子,一個蜜,一個轉,蜜是甜香,轉是回望,便是她的味道和樣子。蜜不全都是蜂蜜,而是蜂蜜、酥油、白糖的混合,不稀不稠,正好可以緊緊包裹在轉子身上。搟開一個長條狀的面餅,在上面均勻地涂抹上混合蜂蜜,用手簡單一卷,造型就做成了。接下來就是送進托盤,接受烘烤。如此香甜的蜜轉子自然是孩子們的心頭好,可吃多了也難免厭煩,就會想著吃個新鮮的,于是夾心又甜糯的棗旋子就接力了。
棗旋子,也可以說是棗泥餡的包子,不過是烤不是蒸。早期的棗旋子,餡料僅有棗泥,還不去核,吃起來的口感并不友好,被硌壞牙被扎到舌頭的幾率很大,吃起來需要格外小心,特別是小孩子容易被卡嗓子。后來生活條件變好了,餡的內容也豐富了起來,棗子也去核去皮,紅豆沙、花豆沙、葡萄干、蜜棗、花生米都可以成為餡,和棗泥混合后吃起來也不再硌牙,棗泥本身含水量多,吃起來會有稀稀的口感,加上紅豆沙,增加了軟糯,再吃起來層次就會豐富。棗旋子吃多了也會膩,適時地換個托羅子再吃,也許會明白本真的味道,才是最最值得回味的。
最近幾年家里在奶奶的張羅下還在做饃饃,但不用托盤了,而是把面、油、蜂蜜、餡料準備好,拿到烤饃店里直接做,安全、省事、省心,也不擔心會烤糊烤壞。
烤出的饃饃不論是色澤上還是口感上都比托的好很多,托盤也就漸漸生銹了。
烤玉米和騰玉米
小學語文課本里有篇課文中有關農村田野的插圖,是我向往的樣子。幾個農民扛著鋤頭和鍬走在鄉間的小路上,路邊成排的柳樹整齊成蔭,遠處的河水清澈安靜,田里的拖拉機冒著煙突突地工作,整幅插畫帶給人清風送爽的感覺,我那時便琢磨著在這樣的環境下干活也定是愉快高效的,但轉念一想這只是插畫而已,成為現實估計是不太可能的。
有一年暑假,我在老家里真正看見了那幅畫,雖然不完全逼真,但也是有了那份感覺,不過我也沒干活,而是烤了玉米。
黃土路有些硬,是只能單向通過一輛拖拉機的寬度;路邊是長了十幾年的棗樹,大都彎彎扭扭,不像柳樹那樣直直挺拔,但寬大的樹干和樹冠下涼爽無比;田里的玉米被微風鼓動著在親密接觸,滿眼的綠色在夏天的高溫下倒也不顯油膩;田間的小渠子就是大地的毛細血管,為田里的作物輸送著血液;一條退水溝阻斷了小路,匯進了小河,小河是七星渠的支流,她不僅承擔著沿線莊稼的灌溉任務,也是我們的天然泳池;河邊稻田依河道而建,周邊的果園里果子都還沒成熟;我們身上沒有扛工具,是剛掰的玉米、干柴、新折的直溜樹枝。新折的直溜樹枝因為是濕的,有韌勁,更容易插進玉米屁溝,烤起來也不會被點著導致玉米掉進火堆。
火燒起來后,就開始烤。各人有各人的烤法,有專找大火烈烤的激進派,有選擇小火慢烤的溫和派,喜歡煙熏味道的就會跟著風走,喜歡口感醇厚統一的就會尋找中火。吃了烤不熟的玉米會拉肚子,是大孩子告訴我們的常識,于是大家就會把時間拉長。
這期間也自然是不會閑著的,還有一種野外玉米吃法,就是燜玉米,我們這叫騰玉米。烤玉米是要扒光“衣服”,直面炙熱,騰玉米則要保留“貼身內衣”,蒸桑拿。小渠子里面深挖出膠泥,混著淺層的濕泥土,均勻地糊在穿著“睡衣”的玉米上,扔在火堆里就暫時不用再管了,然后就可以專注烤玉米。
玉米烤完了,火也燒完了,把火星子蓋在騰玉米上,就可以吃烤玉米了。
烤玉米就是要烤糊。表面的高溫炙烤,把玉米的汁水都鎖住,第一口下去,忍過滿嘴的糊味和吃土的口感,就會刺探到后面玉米汁水的甘甜,這般先苦后甜充滿復雜情緒的味道,就和吃辣條一樣,讓人停不下來。
吃完烤玉米,騰玉米也基本熟了,撥開泥土,迎面撲來的是泥土的芬芳,玉米的香氣也沒被比下去,和烤玉米截然不用的味道和體驗,我還是更喜歡吃騰玉米。
打場、摸魚
以小孩的視角看,打場是一場盛大的游戲;以大人的視角看,打場是一次變工的變現。暑假的打場就是麥子脫粒,文藝點說是一顆麥穗的旅程。麥子收割之后,不是立即脫粒,每家都會把麥子堆在隊上公用的場地里,讓麥子自然曬干,這樣可以讓麥穗脫得更徹底,不至于浪費。麥堆有圓錐體、正方體、長方體、梯形以及不規則的形狀,這主要取決于麥子量的多少,多的話,就只能是長方體,可以降低脫粒時候取麥子的難度。麥堆,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好玩程度不亞于玉米堆。麥子在場上晾曬一段時間后,幾家就會合計一起打場,一家人打場是干不過來的,一般都是幾家人合力。在收割機還沒有大面積普及的年代,麥子脫粒的程序還比較繁瑣。第一步是脫粒,把麥子送入脫粒機,產出的是麥秸和麥穩。麥秸用三股叉叉到一旁碼成垛,以便之后賣給造紙廠;麥穩則要及時從脫粒機的下部用四股叉叉出來,以免堵塞脫粒機。第二步是揚場,打開大概直徑一米的鐵風扇,順著風向,用四股叉或者方頭木鍬把麥穩揚起來,麥粒會自由落體,麥穩子和雜混進來的麥秸就被吹走。這還沒完,想要完整干凈的麥粒,第三步就是篩,用的也是直徑大概一米的鐵篩子,把揚過之后的麥粒再過一遍篩子,多余的麥穩子和短一些的麥秸會被篩出來,過篩的麥粒就可以裝袋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打場,過程和之前相比沒啥新奇發現,最開心的,是我可以一個人抱起一袋大約50 斤的麥子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大男生了,就是那種我可以扛起任何我想扛起的東西的感覺,威嚴和責任都不在話下,那樣的感覺,只在我結婚的時候才又出現了一次。
打場完了,接下來的大活是掰玉米,但要到九、十月份,這期間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到渠里洗個澡或者到渠邊摸個魚。
摸魚是技術活,我能做的也只有在岸邊加油,加油還不能出聲,怕魚被嚇跑,這就讓我對摸上來的魚的質量和之后的魚肉魚湯的鮮美感到懷疑。
摸魚的手型很重要, 擱在現在來說就是把聚攏比心的手分開,想辦法讓魚兒游到你手心。下渠子后,從靠近岸邊的地方下手, 慢慢地往渠邊探, 一個目的是把魚往渠邊趕, 壓縮它的游動空間讓它盡可能被泥掛住,可以更容易抓住它, 另一個目的是一旦感覺摸到了魚, 就可以迅速提手把魚順勢扔到岸上。我照貓畫虎地學著摸了一次,結果一無所獲。再后來, 我就不做嘗試了。
高中之前我幾乎每個寒暑假都會回老家,老家的伙伴們,年齡大都比我大,輩分比我高,我羨慕他們黝黑的胳膊上那一根根清晰可見的肌肉線條, 這讓我在跟著他們翻墻偷果子、渠里溝里洗澡的時候特別有安全感。我佩服他們掌握的生活常識和生存技能, 這讓我不論白天、黑夜甚至半夜都可以安心地跟著他們, 因為我知道和他們在一起不會讓我餓肚子,不會讓我受欺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