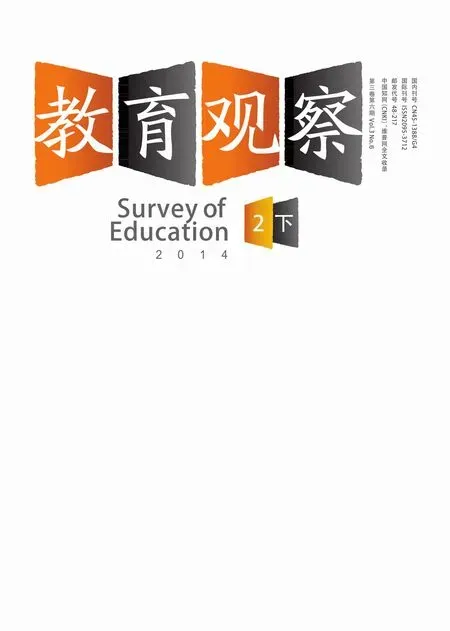行在“幸福文化”之路上
——校園文化建設的且思且行
賀曉彤
(桂林市靈川縣城關第三小學,廣西桂林,541200)
校園文化是學校精神的踐行和外化,是校園精神的動態形式,是學校育人活動中最直接、最廣泛,也是最深刻的部分。校園文化建設是培育學校精神不可缺少的方面。無論是校園文化建設中的顯性文化建設,還是隱性文化建設,都是學校精神孕育的過程。
我校是一所年輕的小學,作為一所城鎮的學校,該如何定位學校的文化,如何在管理中體現校園文化,同時讓校園文化引領學校發展呢?
一、以頂層設計為導向,定位學校的發展方向
學校校園文化頂層設計解決的是學校最高層面上的終極目標和辦學定位等重大思路問題,并繪制出清晰、明確的實現藍圖。所謂“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辦學的思想、宏觀的戰略是學校的觀念文化的體現,是精神文化的內核,它包括師生的思想意識、審美情趣、價值觀念、理想追求,反映了學校師生的群體精神、文明氣質、學校風貌。因此,學校文化的頂層設計要源于學校的歷史沉淀、地域特色、教育環境、學校的現狀(包括環境建設、教育教學、師生現狀、發展的優劣……)等方面。學校可采用專家引領和全員參與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綜合、全面地對學校進行調查、診斷,提煉出適合學校發展的理念。
在2009年以前,我校的辦學目標及相關的“三風一訓”也都是“千校一面”的“奮發創新”一類。后來在鄭杰校長的指導下,于2009年對學校未來的發展進行了重新定位:學校應彌漫書卷氣和人文色彩,物理環境富有精致美感,教師言行舉止高雅、大氣和富有現代氣質,在傳統文化基礎上,著力凸顯關注“合作”“個體幸福”“自由成長”等現代教育理念,為學生可持續發展和未來無限可能創造條件。因此,學校設計了基于“幸福家園”的學校文化理念系統,提煉出適合校情的愿景及相關理念。
理念的形成,對提高師生的凝聚力,鼓舞師生的斗志,均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從此,學校緊緊圍繞“創造一個令人向往的幸福家園”這一辦學目標,以“幸福家園”為學校校園文化建設的主題詞,基于學校所處的環境、生源等實際情況,努力探索校園文化的“生境”,積極開展各項活動,努力構建以“幸福學生、幸福家長、幸福老師”為主干的“幸福家園”文化體系。同時學校將“幸福家園”文化具體到每個學期的工作目標,即:“抓內涵,促提升;抓質量,樹品牌;抓文化,出特色;抓后勤,求發展;抓安全,創平安”的“五抓”工程,各部門每個學期都會依據這個目標,理清思路,結合實際制定出符合學校發展的部門計劃,并落在實處。促使學校工作方向明確,更具實效性與發展性。
二、以制度建設為保障,促進學校文化建設的有效進行
制度文化包括學校的規章制度以及師生員工的行為規范、生活方式等,是校園文化的“行為工程”。加強制度文化建設,不斷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體系,突出管理的系統性和實效性,是學校校園文化建設的關鍵。“不立規矩,無以成方圓。”學校遵循教育規律,依據教育方針和教育法規,圍繞“人”這個核心,建立和健全各種規章制度。在制度的建立過程中,充分發揚民主,經過師生充分醞釀和討論,最后才以條文的形式定下來。學校的規章制度體現了三個特點:一是全,規章制度應該是全方位的,做到事事有章可循,如行政管理制度、德育管理制度、教學管理制度、總務管理制度等;二是細,內容具體明確,操作性強;三是嚴,紀律嚴明,賞罰分明。
為了保證制度的貫徹落實,學校有必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管理網絡。比如學校的德育工作,學校成立以校長牽頭,主管副校長負責,政教處正副主任、少先隊大隊輔導員、教研組長、班主任參加的德育工作領導小組,實行“四線”管理。即:“校行政、黨支部”一條線,主管師生政治學習,組織師生開展各項政治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主管副校長、德育處、班主任”一條線,主要負責師生的一日生活制度,貫徹落實師徒規范和《行為規范》;“少先隊大隊部、班委會、中隊各班值日生”一條線,負責日常行為規范的自查自糾工作;“校長室、政教處、派出所、學生家長”一條線,主要負責學校、社會、家庭“三結合”教育及安全教育。這種管理網絡的建設立足于職責,從樹立事業心和責任感入手,分工明確,職責分明,考核到位。這保證學校各方面的工作能夠有序進行,保證了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激勵著教師在工作中不斷創新。
三、以環境建設為基礎,構筑文化建設的外顯氛圍
校園物質文化具有“桃李不言”的特點,能使學生不知不覺、自然而然受到熏陶、暗示、感染。美國教育家布萊森說:“任何一所學校環境都在默默地對師生發表演說,而且師生的確會注意它,并不知不覺地接受熏陶和影響。”健康優美的校園環境就像是一部立體的、多彩的、富有吸引力的教科書,它有利于陶冶學生的情操、美化心靈、激發靈感、啟迪智慧,也有利于學生素質的提高。蘇霍姆林斯基說:“讓校園的每一塊墻壁都‘說話’,讓每處環境都育人。”整個校園,就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大課堂,要讓學生視線所到的地方都帶有教育性。為此,學校將環境布置與學生的學習生活緊密結合,努力營造一個“高雅”而又不失“朝氣”的“美麗家園”,使師生耳濡目染,接受校園文化的熏陶,達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最佳效果。
一幅圖畫,訴說著一個動人的故事;一段文字,演奏著一首美妙的樂曲;一處建筑,就是一面育人的旗幟。花園式的校園環境為師生創設了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一個優美的生活環境、一個勤奮的學習環境,它時時處處塑造著師生美的心靈,陶冶著師生高尚的情操。
四、以各種活動為載體,內化學校文化精神
學校精神歸根結底會體現在師生員工的身上,表現在師生員工的言行舉止之中。學校精神只有內化為師生的動機態度、意志品質、行為習慣,才能真正得到體現,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內化需要經過實踐活動才能實現,實踐是學校精神內化的基礎。只有讓廣大師生員工在一系列的實踐活動中獲得滿足和愉悅,學校精神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實。同時隨著實踐程度的深入和領域的不斷擴大,隨著個體認識的不斷發展,師生員工又會有新的需要和新的沖動,于是學校精神便在這新的需要和沖動中得到提升和塑造。
豐富多彩的校園主題文化活動,是培育學校文化的重要載體,可更充分地使師生施展才華,發展個性。各種活動使學生發展興趣愛好,發揮特長,提高了學生各方面能力與素質,發展了學生的自信心及競爭與合作意識。各種創造性活動也挖掘出學生個體的潛在能力,使他們充分認識自我,克服心理障礙,增強自信心,從而創設良好的精神文化。
校園文化應該是一所學校持久恒定的團隊精神,是一所學校的靈魂,是學校發展的無窮動力。作為年輕學校來講,以“幸福家園”的校園文化來引領學校的幸福發展將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我們期待通過校園文化的建設能引領一種正氣,培植一種精神,實現一種突破,真正實現享受教育的“幸福”,從而真正形成一個學校的精神共同體。
[1] 馬延偉,馬云鵬.課程改革與學校文化建設——一所學校的個案研究[J].教育研究,2004(3).
[2] 劉良華.學校文化的核心精神[J].全球教育展望,2008(5).
[3] 顧明遠.論學校文化建設[J].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