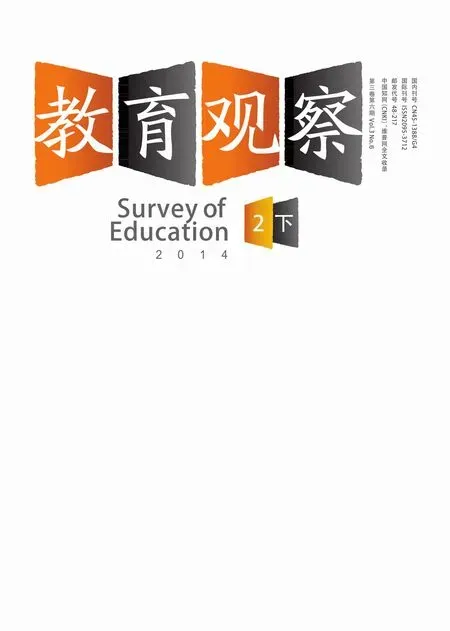尋找對與錯之外的那片田野
陳立軍
(長沙市明德中學,湖南長沙,410004)
“在對與錯的區分之外,有一片田野,我將在那里遇到你。”
——題記
(一)
學生的許多日常行為,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并不會時時符合規矩。為預防學生的不良行為,班主任往往會以班規的形式做出嚴格要求。這些班規中,少不了一些懲罰性的條款,以維護班級的秩序井然與良好運行。
例如,對于學生的遲到行為就可能會有如下懲罰條例:
遲到一次,罰打掃教室衛生一天;
遲到一次,抄寫英語單詞100個;
遲到一次,(男生)做俯臥撐20個或(女生)下蹲練習20次;
……
這樣的懲罰條款一般是師生一起議定并形成文字,全班(大多數)同學舉手表決通過的。班主任(班干部)進行懲罰時依班規執行即可,學生基本上無話可說。表面上看,這樣的效果應該會很好,對違反者能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可是,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一次上學路上,在學校附近,兩位學生不急不慢地走在我前面。
甲:唉,又遲到了。
乙:遲到有什么關系。大不了就做20個俯臥撐嘛。這學期我都做過好幾次了,老師又能把我怎么樣呢。
乙同學的話語中對遲到的不屑讓老師們倍感遺憾。然而,反躬自省,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種懲罰,事實上,是最低層次的管理、最低層面的教育。它不但沒有多少教育的含金量,有時甚至還會誤導學生把錯誤的事情正向化,或者說將錯誤合理化——受了罰就沒事了。所以,我們看到,有些學生沒少受到懲罰,但受懲罰之后依舊我行我素。
(二)
許多老師認識到這種懲罰是毫無意義的。于是,在學生犯錯之后,更多的是教育學生直面錯誤,“改邪歸正”。
下面是一位班主任與一個多次遲到的孩子的對話。
班主任:今天怎么又遲到了?
孩子:我……
班主任:你不要找什么借口了。你倒說說看,遲到好不好?
孩子(低著頭,小聲說):不好。
班主任:怎么就不好呢,有哪些不好呢?
孩子:會影響學習。
班主任:還有呢?
孩子:會惹老師生氣,對不起老師。
班主任(哭笑不得,忍住笑):還有嗎?
孩子:還有……(孩子似乎想不起來)
孩子:老師,我總是給您添麻煩,總是不求上進,我都討厭這樣的自己了。
班主任:是的,你的遲到會給別人帶來麻煩,給班級帶來不好的影響,你每遲到一次,學校就會扣班級評比分一分。你說,你不能為班級增光為班級加分,卻還經常遲到,給班級扣分,你想不想這樣?
孩子:我不想……孩子深深地低下了頭。
……
這位老師試圖引導學生認識錯誤并改正錯誤,初衷很好,但收效甚微。其實,在老師引導之前,許多道理學生已深深明白,但明白了并不等于就可以做到。何況許多違紀現象,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如遲到,也許是生病了,也許是堵車,也許鬧鈴沒響,也許是特殊情況下的助人……老師是不是每次詢問了原因,詢問原因后是不是相信學生并呵護(如果學生真是生病了)學生呢?班主任老師面對學生的遲到,如果單方面認定這是一種錯誤行為,一心分析他遲到的錯誤,以引發他內心無比的慚愧、內疚,甚至是罪惡感,不問學生遲到的原因,忽視學生的感受,就算學生低頭承認了錯誤,這也不能讓學生心甘情愿,感到心悅誠服的。如果他是出于恐懼或緣于內疚來迎合老師,那么,或遲或早,我們將發現孩子會不再友好。一個人總是屈服于外部(老師)或內部(內疚之心)的壓力,很可能使他心懷怨恨,并厭惡自己。正如上例中這個孩子所說,“我都討厭現在的自己了”。內心擔負著太多的沉重,承載著太多的內疚,一個孩子就會對自己失去信心,覺得自己越來越沒用。這其實正一步步遠離我們教育的初衷。
(三)
蘇菲派詩人魯米曾說:“在對與錯的區分之外,有一片田野,我將在那里遇到你。”我們對學生的教育,是不是也可以在對與錯、好與壞、道德與不道德的區分之外,尋找到那么一片田野,去感受學生的需要,去觸摸學生的心靈,讓學生以負責的方式表達自己并糾正不良行為呢。
我想起了這樣一篇關于遲到的敘事:
如果沒記錯的話,自從2012年的第一場大雪后,王同學幾乎每天遲到。三分鐘到十分鐘不等。今天,第一節課已經下課了,他才趕來。我表情有點凝重,問他:“今天又遲到了,有什么特殊原因沒有?”他說:“沒有。”我耐著性子繼續問:“那為什么又遲到了呢?”他竟然面帶微笑,很輕松地說:“我又睡過頭了,醒來的時候已經遲到了,我想今天就裝病不起來了。又睡了一會,可是睡不著,心想,我這周已經連續四天遲到了,現在還裝病,好像很不好,于是我立馬起來,跑到學校。”
他沒有說假話,他是跑到學校的,他推開教室門時還在大口喘氣。那一刻,看到他那個微笑的表情、輕松的面容,我很納悶:平時在老師面前,他要么面無表情,要么沮喪泄氣,今天在一周已連續四天遲到的情況下,怎么還能保持如此陽光般的微笑呢?我問他。他說:“老師,有一次我上課睡覺,你問我晚上干什么去了。我回答說,晚上用手機上網,結果忘了時間,到凌晨1點多才睡。當時你說希望我少上網,并特別指出很欣賞我的誠實,所以我覺得還是誠實地跟你說比較好。”那一刻,我被這個孩子感動。我說:“陳老師除了欣賞你的誠實,還很喜歡你陽光般的笑容。愿你笑口常開。當然,我還希望你能有時間觀念,能養成守時的好習慣,我相信,一個誠實、陽光并且守時的你,會更讓你自己喜歡吧?”
……
之后,不知是天氣暖和些了,還是他良心發現,他沒怎么遲到了,似乎心情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這位班主任在處理學生遲到的問題時,撇開學生遲到的對與錯不談,肯定學生的誠實品質與陽光心態,發現學生內心正向的力量。同時,還不忘提醒學生,做一個守時的學生,使自己更喜歡更欣賞自己。這樣,孩子知道了哪些是自己本擁有的好,哪些是可以生長的好,孩子在這個過程中就能體會到成長的快樂,走向善良與美好。
正如劉鐵芳教授所說,“教育生活的真正品質在于欣賞,而不是苛責。真正的欣賞并不是無視對象的缺點——恰恰是以對方存在的不完美作為前提——只不過,我們的眼睛緊緊盯住的不是他(她)的缺陷,而是在審美之眼中所呈現出來的他(她)的美好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我們與其反復懲罰與說教,還不如在對與錯的區分之外,發現那一片美麗的田野,呵護優點、肯定長處,引導學生悅納自我、欣賞自我,健康快樂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