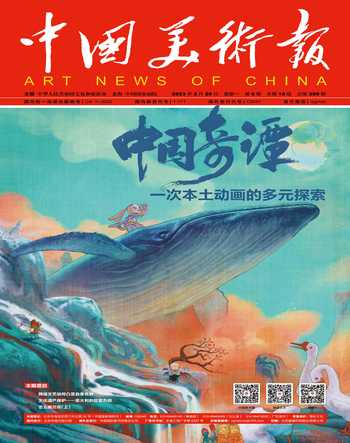共享科技紅利 擁抱AI藍海
馮知軍
近期,國外爆火的ChatGPT引發了一輪輪的關注和熱議,在資本市場上也掀起了基于對人工智能(AI)的想象和前景預期的追逐。在國內,百度推出的生成式對話產品“文心一言”(英文名:ERNIE Bot)也將于3月完成內測并面向公眾開放,而且包含主流新聞媒體、財經類媒體、行業類媒體、戶外媒體等多家媒體平臺宣布接入百度“文心一言”。從早期新聞行業的“寫稿機器人”,到今天的成批量引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新聞時代似乎在悄無聲息中提前來臨了。還有現今各種城市智慧場景建設,讓我們已經在享受著人工智能等科技的紅利了。
其實,人工智能對生活各方面的介入,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在不知不覺中慢慢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對其的認知。但之所以ChatGPT的面世引發如此關注,其核心恰恰也是對于生活的介入更加緊密,更強大的內容生成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讓普通公眾也能借此完成曾經只有專業人士才能接觸或解決的問題。也正是如此,ChatGPT在受到追捧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不安和焦慮。如它在作為聊天工具之外,還可以完成寫代碼、論文、小說等任務。這種基于模式識別和深度學習的感知智能技術,從海量語言數據、知識庫中學習訓練而來,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以往只有人類才可能做到的事情。
然而,上述不安和焦慮,絕不是排斥諸如ChatGPT之類人工智能產品的理由。以學術論文寫作為例,學術不端不是人工智能出現之后的新事物,而是早已有之,只是將傳統的“剪刀+漿糊”進行了升級。所以,在糾結于這類新產品帶來的負面問題之外,更要看到其帶來的各種便利和科技發展帶來的紅利。如以往的學術研究,在博聞強識的基礎上,在浩如煙海的典籍中,是一個繁重的案頭工作,今天,這種案頭工作自然不能舍棄,但科技的發展已經很大程度上解放了雙手、提高了效率。
人工智能的誕生初衷,是對人的解放和輔助,是人與器的關系。在這個大前提下,如何用才是問題所在。就此而言,人工智能不是潘多拉魔盒,打開后釋放的不是必然的邪惡,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中的憂慮也不是其必然歸宿。不可否認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人工智能必將更加強大,和現實生活的聯系也將更為緊密,我們在享受人工智能帶來的便利時,種種基于此的想象甚至恐懼不也是給我們的精神世界增添了許多色彩和靈感嗎?
至于藝術領域,可能是對新技術的接受應用最為敏銳的,各種新生觀點和矛盾在這里匯聚,從而推動形成了今天的藝術面貌。
照相機的出現,沒有摧毀傳統的架上繪畫,恰恰是給了美術新的發展方向。對自然科學的探索,更是催生了現代主義藝術。數字時代,數碼相機的誕生讓傳統的膠卷退出了大眾市場,這是技術的力量,也是公眾的選擇。數字時代和美術的初結合,就讓美術大家庭新生了數碼繪畫,人工智能的出現,進一步誕生了AI繪畫和設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技術,這不正是當代藝術發展的一個維度嗎?而且對技術的消解不等于對技術的否認或拒絕,只是對“技”與“藝”關系的重新考量,更是對“技”與“藝”的進一步推動。正如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對藝術是消解更是重塑,以及阿瑟·丹托等的“藝術終結論”所談的不是藝術的終結而是指向藝術的未來。
由此來看,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在藝術領域帶來的是對既往知識和技藝的總結和梳理,也帶來了對什么是藝術、什么是藝術家的追問。這個話題很大,大到古往今來諸多哲學家、藝術史家都在孜孜探索;這個話題也很小,就是歸結于一點,藝術與人相關,那么藝術創作和接受也就是人的創作和接受。在此意義上,科技的紅利、AI的藍海,也給藝術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國美術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