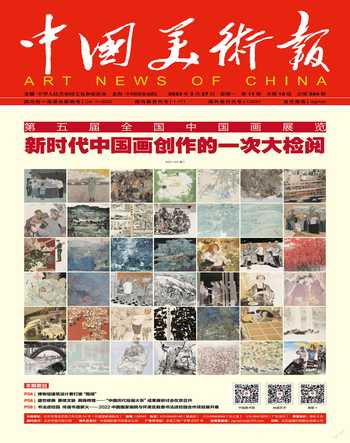文化地標建筑的科學理性塑造
孫一民
長期以來,城市中的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等大型文化建筑,廣泛受到市民的喜愛和關注,地位之高又往往被當作標志性建筑來建設。在產生了許多建筑精品的同時,公共文化建筑與“奇怪”建筑也出現了許多交集,許多造價不菲的建筑成了大家心目中的丑陋建筑。究其原因,恰恰是過分追求標志性的獵奇心態催生了“自以為是、自我炫耀”的建筑設計表達,助長了決策者和部分建筑師標新立異,追求差異性和獨特性,忽略了建筑的文化功能。我們經常看到“以耗能為代價”的大而不當的建筑空間、“以耗材為代價”的扭曲浪費的建筑形體,不僅增加了公共建筑的運行維護成本,其低俗怪異的設計還折射出決策者乃至城市低俗的文化品位。
因此,我們說:大型公共文化設施融入城市、融入市民生活才是根本。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類的公共建筑應該立足公共性、確保開放性。在建筑形象設計方面,大型公共建筑應該堅持有節制的自我形象表達,設計著力點應該是倡導和弘揚科學理性的公共價值觀。我國作出節能減排的雙碳戰略的背景下,大型公共建筑應該注重性能提升,把全生命周期的節能降耗作為最重要的設計要點。
“融入城市、融入市民生活”,意味著博物館、美術館這些習慣于以封閉的、精英殿堂自居的建筑,需要更加重視自己應該怎樣以合理的方式存在于都市。古往今來,優秀的公共建筑都是與城市的街巷脈絡息息相通,大多是市民喜愛和能夠便捷到達的城市節點,成為市民生活中最有意義、最有歸屬感的一部分。諾里地圖顯示的羅馬城市中,將24小時自由進入的教堂空間作為城市公共空間。我國嶺南地區的近代城市建設中,將沿街商業建筑的底層,后退一個柱子的跨度距離,形成了貫通的騎樓街,這樣一個介于公共與私有邊界之間的公共空間,提供了遮陽避雨的步行廊道,也讓行人與店鋪的溝通自然而親切,很快在廣泛的南方地區城鎮得到普及,至今仍然讓人喜愛。對于美術館、博物館這樣的大型公共建筑而言,公共開放的空間從管理上存在難度,但卻是可以通過設計增加空間的通達性,在可管理的狀態下,鼓勵市民使用。
廣州藝術博物院(廣州美術館)新館的設計就非常注重與公眾之間的關系。首先廣州美術館新館的建筑四周設置了類似騎樓空間的檐下空間,給市民提供公共停留空間的同時,又不影響美術館的管理運行。在美術館內部,直達天穹的中庭空間將天光引入,形成了與室外公共空間相似的明亮場所。這樣的空間配置,讓美術館具備了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將底層公共空間向市民開放的可能,市民即使不進入展陳空間,也可以感受美術館建筑的親切和高雅,從而形成城市公共空間向藝術空間潛移默化的交融,把藝術的品質滲透在城市公共空間中。
為了讓美術館的設計與地域文化相結合,反映城市文化,廣州美術館新館的設計非常注重和體現嶺南文化的精神。坐落于水面上的美術館建筑主體,它的東面和北面是雙層立面,相對封閉。南面和西面向嶺南廣場開敞,游人在此可享受城市美景。玻璃亮片為休息空間提供遮陽,這種立面的構造方式,是嶺南建筑語言的傳承與發展,通過對當地氣候的巧妙回應,讓人們可以在建筑中感受到自然的親切。建筑開辟了兩個公眾入口,將城市空間引入建筑內部。游人可通過中庭與共享空間向上到達所有展廳,直至屋頂庭院。廣州美術館新館的設計,最大化公共開敞的同時,也滿足了管理的要求。
美術館、博物館的標志性,往往在不經意間引導了社會的價值觀,珍視標志性建筑的公共導向是規劃師、建筑師的社會職責。廣州美術館新館的建筑設計將光伏太陽能技術作為建筑設計創新的重要亮點。工程經過精心的建筑光伏一體化設計,建筑四個立面和屋頂,都形成了光伏發電的功能。真正實現了:“注重性能提升,把握節能降耗”,讓標志性公共建筑倡導和弘揚科學理性的建筑價值觀。
(作者系全國工程勘察設計大師、長江學者、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原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