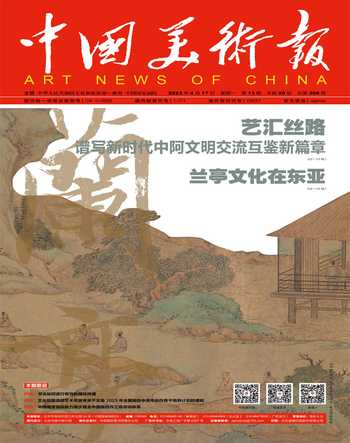擴大書法展覽國際傳播的聲勢和影響力
魏廣君
文化傳播本身有一個“接受”的問題。從圖像、結構等角度,中國的文字和西方文字區別很大,如果讓世界其他民族在文化藝術領域對中國漢字有所接受相當困難。這就像在生活中我們對西方的城市建筑、鄉村田野,乃至文化藝術也會有所了解、有所見識,但很大程度上我們也像旅游中的“打卡”一樣,走馬觀花。再如,中國的宮廷建筑、宮廷文化乃至田園文化,包括村舍屋瓦之間的趣味相映,西方人也無論如何不會從骨血之中對我們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和親近。那么落實在書法上,讓外國人從漢字的空間構成去感受到中國人的藝術精神,也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當然,我們也并不必要完全持悲觀態度。即使讓世界全面接受中國的書法藝術并不現實,但我們讓一部分人接受甚至喜歡中國書法,并將其作為藝術形式的存在還是有可能的。就像我們對西方的繪畫、裝置、行為藝術的接受也是有所選擇的欣賞、喜歡甚至學習。
要增進彼此藝術的交流就需要有相應的傳播紐帶,即通過有效的傳播者、合理的傳播途徑去影響受傳播者。傳播者包括政府主導的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領域的領軍人,傳播的途徑則包括多元的科學技術、開放的政策指導、多向的藝術觀念以及多維的傳播空間。既然中國書法美的實質對于一些國家來講是不可理解的,我們對他們從介紹到意義的揭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徒勞的。即使是對書法有較深理解的亞洲國家,也是依照自身對書法藝術的理解來創作和傳承的。所以,我們要找到一種對他們來說具有吸引力且“合理”的解說方式,來傳播書法的文化魅力,而絕不是讓對方完全接受我們認為的書法的藝術精神是什么。
在西方,畫廊對藝術的傳播有著很大的紐帶作用,但讓西方的畫廊對中國書法感興趣,可能性并不大。偶爾碰見某個畫廊收藏或者出售一兩件書法作品也說明不了問題。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藝術畫廊,使其推動書法的國際傳播還是相對遙遠的事。此外,如巴塞爾文獻展、威尼斯雙年展等國際性的展覽跟書法幾乎沒有任何關系,策展人本身就沒有考慮以中國書畫入展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在書法的國際傳播中,展覽作為有效的主要途徑實際上是缺失的。不僅如此,即使在這樣的國際展覽中展出和中國書法有關的裝置藝術、行為藝術等,也跟我們國內語境下所說的書法相去甚遠。
用現代展覽的觀念來看,書法是個新生事物。但從傳統文化角度看,書法又是古老的藝術。20世紀80年代,以谷文達為代表的藝術家,能把書法的性格和脾氣特征,通過書寫和水墨的自然暈章傳達出來,比如抽象化的傳達、血脈賁張的造境勇氣和水墨用到極端的精神力量。從探索性的展覽角度來看,我們現在搞的前衛、當代、行為、裝置、書法墨像等,傳達出來的感性的東西太多,缺乏一種梳理,尤其是理論上的系統化建構。
在新的歷史時期,需要我們付出精神探索上更多的努力和實踐。今天書法的國際交流與傳播,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已經營造了一個很好的文化形象和環境。國家層面對書法藝術的關注和傳播渠道的暢通,是進行書法國際傳播推廣的重要因素,比如各類社會學科中有書法選題的介入,中國藝術節和上海國際藝術節中書法比重的加大,都有效地起到了國際性推動和傳播作用。此外,如何策劃和持續性推動中國書法在專業網站上的翻譯工作,多種語言、多種渠道的傳播也是重要的途徑。
(作者系中國國家畫院書法篆刻所所長,本文根據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