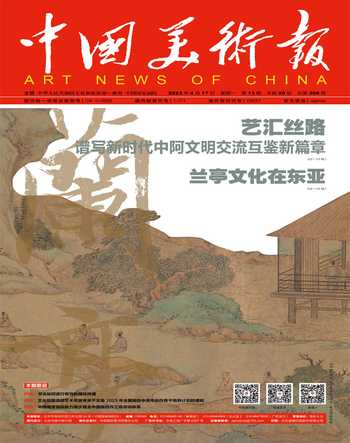當代技術語境下的書法傳播
書法作為與人密切相關的活動,它是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生發出的文化符號,一直以來擁有著大量的群眾基礎。人們通過這些象形的結構,渴望窺探出傳統文化中的某個面相。這既是書法的優勢和獨特性的體現,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事實上,書法所面對的不僅有強大的傳統,還受到了當代各式各樣文化思潮的猛烈沖擊。特別是,在資本和技術雙重夾擊的藝術生態下,它將不再執著于傳統的代名詞,而走向不同的界面繼續生長。
技術環境催生傳統的變革。當數碼科技重塑世界,網絡成為當代社會溝通的重要媒介,轉變了當代藝術的體驗感,成為了展現自我、討論時事的全球場域。這些新的生活形態和技術環境,迫使書寫的觀念隨之更新與拓展。事實上,互聯網為讀者和創作者提供了平等對話的界面,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它不再是遵循從個人到全球的傳播方式,而是伴隨著創作者的軌跡演變為從全球到地方的文化傳播模型。一方面拓寬了書法的傳播途徑,更有利于跨文化之間的文化互動;另一方面,在模糊了觀眾與創作者之間的身份邊界后,進而對傳播的內容提出了更多要求。
這意味著,如果只是將傳統預設為靜態的文化遺產看待,無法與當代的新技術、媒介相融合,那么這樣的傳播也只能是一廂情愿地單向輸出。因為,當我們企圖走出漢文化圈,面對不同異質文化之間的互動,需要理清的客觀事實是:他者始終無法真正地站在中國文化內部思考我們自身傳統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譬如,如何真正講清楚中國傳統繪畫和書寫過程中筆墨與線條的問題。面對這些困難,促使我們在跨文化交流中必須尋找出一條便于相互轉化的文化策略。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中國文化中最為寶貴的精華,而是通過重塑標準的方式篩選出既能夠延續傳統書法,又能鏈接當代語境的藝術范式。因此,我們急需一種具有前瞻性、突破性且具有包容性的嘗試。盡可能地觀照到各個結構中不同觀眾的需求,創造出與其相適應的內容,從而進行有效的文化傳播。
對于展覽的策劃者而言,應該善于利用互聯網發現和轉化與之相適應的藝術形式,才能真正使傳統文化有效地介入當代現實。換言之,如何找到一種新的工作方式對當下藝術的敘事模式進行反思和完善,從而在以小見大的藝術實踐中延伸、乃至跨越藝術的邊界。以“書寫與邊界”為主題的第六屆昆明美術雙年展正是圍繞這樣的問題而展開。在展覽中呈現了書法在當下轉化為不同形態的可能性。既有傳統類別的創作現狀,也有受到現代思潮影響具有表現類型的書寫形態以及跨文化之間的對話。正如西方現代主義作為一場跨文化的藝術實踐一樣,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中國傳統的書寫形式,卻給書寫帶來了重新生長的契機。此外,在作品的表達形式上還囊括了諸多將書寫維度拓展至裝置、雕塑、身體、時間等多維空間,或利用技術代理的邏輯結合書法與現代科技的表達。這些語義多元的作品通過引入不同媒介,借用書法的元素傳遞出復雜的當代書寫精神。
總體而言,從“書法”到“書寫”行為的內在軌跡中,折射出傳統藝術中內部的張力與生命力,呈現出更加開放的學術框架,進而在多重維度中互通藝術類型的邊界。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嘗試,才有了面對不同群體的可能性。事實上,這個不斷選擇與更迭的過程正是書法走向國際的過程。
(作者系“書寫與邊界——第六屆昆明美術雙年展”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