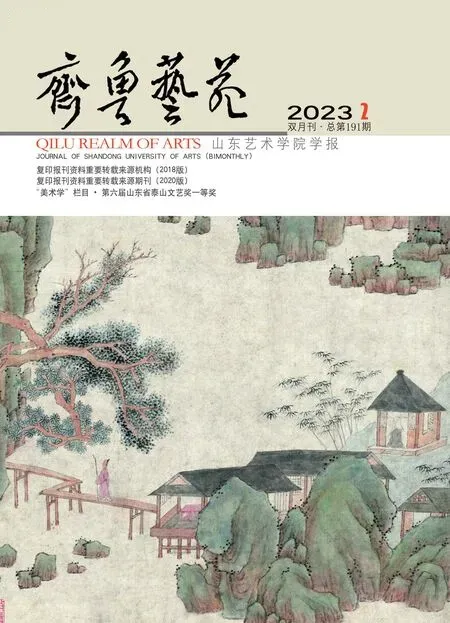文化尋根:從中國古典舞“提沉”辨析“氣”的訓練價值
高 楊
(沈陽音樂學院舞蹈學院,遼寧 沈陽 110169)
引言
“氣”是中國傳統哲學、美學的一個特有概念,也是中國古典舞訓練、審美所獨有的核心元素。它貫穿于舞者身體運動以及情感表達的始終。“氣”在中國古典舞中的地位,就如其在人體生命中一樣重要,對撐持人體生命、激發身體活力、調節身體運動趨勢,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
在中國古典舞課堂訓練上,雖然我們時常會聽到老師強調“氣”的重要性,并告知學生:不要僵,學會呼吸,動作要伴隨著呼吸來做。然而,哪有學生沒有聽過這樣的建議,誰又能將“氣”或者“呼吸”,科學地運用于身體動作之中?李馨、蘇婭談道:“使得學生對‘氣’的把握與運用如同爬‘天梯’,知其重要,但無從落實,甚至有些學習者學了十年的古典舞,但對于‘氣’的掌握與認識,仍是‘外加香油一勺’的添加劑,而不是融于血液中的‘生命能量與運動動力’。”[1]究其根源筆者認為,并非學生不采納運用“氣”舞動肢體的建議,而是他們沒有掌握,甚至不知道如何運用“氣”來帶動身體運動或舞姿展現的方法和能力。縱觀近60年的當代中國古典舞蹈發展,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教學內容源自芭蕾的系統化訓練。雖然有相關中國古典舞專家依據戲曲、武術等傳統,將芭蕾舞手位以及身體姿態進行民族化整理,但從舞者運動形態與身體力量來看,其仍然體現出明顯的西方式身體符號特征。如果說中國古典舞蹈身體符號的變異,是源于芭蕾訓練對它的瓦解與重構,那么,芭蕾對于幫助中國古典舞蹈建設的歷史價值是什么?芭蕾對中國古典舞蹈身體語言展開訓練的目的又是為何?如果說“氣”在中國古典舞訓練和審美中占有核心地位,那么,為什么舞者在如今的中國古典舞蹈表演中,對氣的運用卻顯得無能為力?為什么在中國古典舞課程訓練中缺少一門或一項真正以“氣”為訓練主體的程序化機制?如果說“氣”是中國哲學、美學中所特有的概念,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建構“氣”在中國古典舞中的訓練方法?
(二)相關文獻梳理與研究
新世紀初,隨著跨領域研究的興起,(向開名2006;王芃2007)率先從氣息和身體的融合出發,讓我們對“氣和舞蹈”間的關系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但研究僅做了一次本體論的普及性介紹,并未展開深入探討。隨著跨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入,國內舞蹈學界不約而同地達成一個共識,(雷瑩2010;張海鈺2010;李曼曼2010;姚佩2010;高陽2011;劉艷2011等)認為,“氣”是中國傳統舞蹈藝術之根,對于培養“氣”在舞蹈中的養成是具有一定價值的。雖然他們給出了肯定的聲音,然而,上述研究僅是重新審視了舞蹈與氣的關系而已,仍未開啟一個較新的視角。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攀升,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也逐步提高。打造國際多邊機制,倡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多元發展觀,其中構建世界舞蹈史中國舞蹈學派的意義就越加緊迫,國內舞蹈學者便開始從中國傳統哲學出發,(袁禾2011;李佳妮2013;魯佳2015;呂藝生2018等)圍繞“氣韻與身體”的美進行論述。雖然他們為該領域開啟了一個形而上的新視域,美中不足的是研究總體上呈現出重理念輕方法的現狀。近四年來,“氣與中國古典舞”的跨域研究,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裴兵2018;米夏2018;畢思文2019;王甜羽2020;寧芬2020;李佳妮2020;沈振宇2021等)以個案作品為中心,從多元視角切入,進而對舞蹈教學和表演的氣展開細致的探討。雖然此時期的研究已具相當之規模,但對于建構有關“舞蹈之氣”的訓練方法論而言,仍有待進一步考究。
(三)研究方法
在中國古典舞訓練中,主要分為基本功訓練和身韻訓練兩大部分。在身韻訓練中還分為盤腿坐姿徒手訓練、坐膝徒手訓練、站姿徒手訓練,以及劍、袖訓練等若干單元。雖然上述訓練方式、形態各有不同,但在訓練元素的選擇上,會有許多相同且重復的組合名稱。例如:在盤腿坐姿徒手形態中有“提沉”訓練元素,在站姿徒手和持劍形態中仍有“提沉”訓練元素,雖然元素組合名稱相同,但在不同造型身體形態上所呈現出的訓練效果和價值卻大有不同。由于中國古典舞蹈強調以軀干為審美核心,那么毋庸置疑,盤腿坐姿能夠有效地將軀干從腿部力量的支撐中獨立出來,因此,筆者選擇盤腿坐姿“提沉”為論述核心,以中國舞專業中專五年級的20名學生為實驗對象,通過“提沉呼吸”的訓練方式向外延申擴展,旨在讓學生通過感受軀干內在氣息流動的同時,探尋建構中國古典舞身體氣息訓練的有效方法,以為夯實中國古典舞科學訓練體系,豐富身體表演語匯提供理論支撐。
一、系統化、專業化訓練與中國舞蹈身體文化的變異
自宋代以來,中國古典舞便開始走向衰微,取而代之的是戲曲藝術的盛行。換言之,從宋代到近代(1840),中國古典舞在歷時態發展的進程中,出現了嚴重的斷代問題。到了19世紀中葉,隨著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的爆發,清廷古老又封閉的大門被西方列強撞破。固守千年的中國封建思想與文化遭到重創的同時,又受到來自西方文化的全新洗禮。彼時的有志青年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浪潮中,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西學東漸之機,才通過主動學習和被動傳入的兩種方式,來汲取西方舞蹈文化的營養與精髓。當西方舞蹈傳入中國之時,其異樣的形態、樣貌以及風格,對中國人的視覺沖擊是全方位的。它不僅為國人打開了一個通往“西洋”的審美視域,還為中國日后的本土舞蹈訓練鋪平了看似順暢且平坦的道路。
北京舞蹈學院原副院長、中國古典舞蹈教育家王偉教授,在其主編的《中國古典舞基本功訓練教程》中,談到建國后中國在學習前蘇聯舞蹈訓練經驗時指出:“中國的舞蹈教育在借鑒芭蕾藝術百年積淀的先進經驗和科學的訓練方法的基礎上,以中國傳統戲曲舞蹈的素材按照芭蕾有序的、漸進的、合理的訓練程序進行動作的重新組合和排序。”[2](Ⅴ-Ⅵ)為什么要按照芭蕾的體系對中國古典舞的基本功展開訓練?無非兩點原因:其一,借鑒前蘇聯的舞蹈訓練經驗,進而建構本民族的舞蹈專業訓練體系;其二,借鑒前蘇聯的舞蹈訓練經驗,建構非舞蹈專業的舞蹈培訓體系。建國以來,為了讓中國舞蹈向系統化、專業化、舞臺化方向發展,我們將西方芭蕾的基本功訓練(基訓)拿來運用,旨在使舞者能夠自如地運用身體展開專業化表演的同時,也能滿足于當代人審美的廣泛共通性。然而,事物總要一分為二的看:雖然前蘇聯芭蕾為國人打開了新的審美視野,建構了科學訓練的平臺,但同時也在腐蝕我們本土文化的特征。換言之,借鑒西方芭蕾的訓練方式,從某種程度而言,看似實現了舞者進行專業化表演的目標,實則卻忽略了民族身體文化被西方舞蹈訓練方式瓦解、消融的弊端。日本戲劇大師鈴木忠志(Suzuki Tadashi)在其著作《文化就是身體》中談到文化與身體的關系時指出:“我認為一個所謂有‘文化’的社會,就是將人類身體的感知與表達能力發揮到極限的地方,在這里身體提供了基本的溝通方式。”[3](P7)美國哲學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在其著作《身體意識與身體美學》中指出:“身體,比如某種姿勢,同樣已經成為一種‘間接的語言’以及表達的基礎。”[4](P77)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其著作《符號》中論述道:“人對身體的任何一種運用都已經是最初的表達。”[5](P46-47,67)綜合上述學者觀點筆者發現,身體雖然不像被組織、被包裝過的身體語言一般,具有溝通和理解上的約定俗成性,但前者與后者相比,前者更具透明性。如下圖:

圖1

圖2
以芭蕾和中國古典舞的身體語言展開對比。圖2的控后腿技術,或許在表達有關中國的故事情節與內容,但其身體所呈現出的力量與氣質,與圖1的特征有何差異?我們暫且拋開服裝、舞蹈鞋和身體造型,請問二者的身體符號所呈現出的力量是否具有共通性特征?試想一下,如果保持兩幅圖片中的身體姿態,將二者的服裝調換一番后,我們依然會認為右圖是古典舞嗎?倘若說,觀眾僅能從服裝和道具上來區別舞種的差異,那么民族身體文化的獨有特征又體現在何處?從中西古典舞蹈身體文化的特征而言,西方芭蕾身體風格講究的是“開、繃、直、立”,而中國古典舞蹈身體風格講究的是“圓、曲、擰、傾”。通過對兩張圖片的比對分析后筆者發現,芭蕾基本功的程式化訓練系統,作為一種模式框架,已深深地嵌入在中國古典舞蹈的身體語言表達體系中。雖然它在幫助中國古典舞建立專業化的訓練道路,但也不留余地瓦解了中國古典舞蹈的“原身體風格性”,從而生成一種“中西兼有”的當代中國古典舞蹈身體文化。
二、從“提沉之氣”尋中國古典舞“身體文化之根”
“提沉”是中國古典舞身韻訓練的基本元素之一,也是一切身體運動規范的原型。“沉”主要以“呼氣”帶動軀干逐漸下降,從腰椎發力,一節一節放松,感覺氣沒丹田,直到頭梢神經完全沉到底為止。“提”是在“沉”的動作完成基礎上,通過“吸氣”帶動軀干逐漸提升,同樣從腰椎發力,一節一節向上直立,感覺氣由丹田提至胸腔,頭梢神經無止境地繼續向上生長,直到下一次的“沉”為止。“提沉”不僅是一切有關中國古典舞軀干外部動作運動的原型,其內部所蘊含的“氣”,更是中國傳統文化典型特征的彰顯。在中國古典舞教學中,每當我們談到“氣”,就會將其與有機體的“呼吸”相提并論,雖然二者有著幾近相似的概念,但從廣義而言,我們卻弱化甚至忽略了“氣”所涵蓋的中國傳統哲學內涵。“呼吸”是指有機體與外界環境氣體交換的過程,是撐持有機體生命的不二法門,而“氣”在包含有機體賴以生存的“呼吸”法則的同時,作為人體內活動力強,且運行不竭的細微物質,還與“(氣)息”“(氣)韻”共同組成了身體運動美學之整體。中國古典舞蹈的美,首先在于它的“氣息”,即“味道”,它構成了舞者身體運動的獨特格調。氣息“有長有短”“有重有輕”“有急有緩”。從人體體內氣息的流動來看,其各樣的節律,皆能改變人體動作外部的形態與樣貌,對于豐富舞者身體語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氣韻”,即生命的“魂”,它是在“氣”與“氣息”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說“氣”撐持有機體生命的運轉,“氣息”構成了人體動作的外部形態,那么“韻”則賦予了舞者身體一種“靈性”。它將人體的物質之氣(呼吸)與品格之氣(氣息)高度統一,才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意蘊成為中國舞蹈最為本質的美學特征和美學核心范疇。
我國著名舞蹈教育家、編導肖蘇華先生,在接受北京舞蹈學院學報副主編張延杰的訪談時指出:“無論創作什么,我們都不能沒有中國文化的根。”[6]“如果脫離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只能一直跟著洋人后面跑。”[7]唐滿城、金浩在其著作《中國古典舞身韻教學法》中談道:“身段(韻)課的定位應是一門體現民族精神風格訓練的主干課程。”[8](P3)這種課程就是中國古典舞訓練、創作、表演及欣賞的靈魂,倘若缺少身段(韻)課,我們就無從談起中國古典舞建構民族精神的方向。其次,二位專家進一步指出:“身段(韻)課的開設不是為了給基訓進行風格點綴,而肯定身段(韻)課的內容是訓練與加強民族藝術表現力和語言性的重要手段。”[9](P4)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舞蹈訓練、創作及表演的靈魂核心,其不僅在內容上應表達中國故事,在形式上也要遵從中國文化的根。
筆者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是維系中華民族生存的精神紐帶,也是中華民族靈魂的獨特標識。之所以中華民族的特性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也正是因為中國文化所特有的“根”,才為它的與眾不同劃分出了界限。對比中西方舞蹈的身體風格我們可以發現,西方芭蕾主要運用腿部、足部進行跳舞展現,通過呼吸來調節運動的疲乏感,身體呈現出奔放的風格特征。而中國古典舞主要運用軀干、手臂,以氣帶動肢體進行舞動,身體呈現出內斂、含蓄、溫婉的語言風格與民族特性。然而,在目前的中國古典舞表演中,我們能夠看到的是與西方芭蕾相似的身體力量,卻少能看到舞者真正“以氣帶身,以身顯氣”的身體形態,那么從此現象來看,我們是不是應該思考如何將中華民族所獨有的“氣”“氣息”“氣韻”運用在中國古典舞的訓練中,以為挖掘中國古典舞蹈文化所特有的價值呢?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個場合中談到“文化自信”時指出:“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10]“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1]筆者認為,文化自信能增強我們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民族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我們文化發展的母體,它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
毋庸置疑,“氣”在中國古典舞訓練、創作及表演中,就是我們所尋的文化之一“根”。袁禾在其著作《中國舞蹈美學》中談道:“氣”作為中國哲學對宇宙基礎物質的認識,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無比深刻的。”[12](P201)“凡舞蹈,都需要利用內部的‘氣’來展示外部的‘力’,中國舞蹈所以特別,就因為它除了同西方舞蹈那樣以‘氣’為動作的推動力之外,更注重對‘氣’之流動形態的體驗與感悟,要求一切動作由‘氣’——呼吸引領,在呼吸(‘氣’)上做,依靠呼吸(‘氣’)的‘勢’推動身體。”[13](P200)呂藝生在其著作《中國古典舞美學原理求索》中指出:“氣韻,是中國古典美學一種獨特的美學表現。”[14](P115)“中國古典舞重視氣,就來自于它的來處——戲曲和武術。戲曲就非常重視氣,并把氣當作重要的功夫來練的。”[15](P113)李馨、蘇婭在《“意”“氣”“力”“勢”“態”——中國古典舞訓練核心概念談》一文中談道:“氣關乎于“神”、關乎于“韻”、關乎于“律”、關乎于“情”,是訓練中重要的核心。在教學中,應著力于培養學生控制氣息的能力,這是中國古典舞產生審美與風格的重要方法。”[16]綜合以上學者觀點筆者認為,“氣”是中國文化之根,哲理之本。在中國古典舞教學與表演中,“氣”不是舞蹈的附屬,而是一門真正的學問,它與身體的訓練、表演,幾乎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作為中國古典舞蹈人,我們需要再探索、再挖掘,通過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或途徑,來挖掘“氣”在中國古典舞訓練中的功能與價值,以為尋民族身體文化之根,立中國傳統美學之本,奉獻智慧。
三、從“提沉”看“內部呼吸”與“外部身體”的連帶關系
筆者首先將盤腿坐姿“提沉”這一簡單且重復性較強的訓練,設置出“無視呼吸”“以身帶氣”“以氣帶身”及“呼提吸沉”4種類型,分別將其分配給班里的20名學生,并以5人一組取一類呼吸類型的方式展開4個八拍的“提沉”實驗。通過實驗后筆者發現,這4種類型背后所呈現出的身體質感與美學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第一類,學生軀干雖有韻律地隨著音樂上下起伏,但她們視“氣”為自然流動的氣體,不加以刻意使用,這類軀干就像一個不飽滿的殼,內部呈現干癟之勢,給人一種缺乏能量之感;第二類,學生軀干隨著音樂且帶動“氣”上下起伏,她們視“氣”為身體運動中的一部分,并形成“以身帶氣”“氣隨身行”的運動過程,這類軀干就如盛氣的容器,內部呈現飽滿之勢,給人一種能量之感;第三類,學生軀干伴隨著呼吸上下起伏,她們視“氣”為帶動身體的源頭,并形成“以氣帶身”“身隨氣行”的運動過程,這類軀干在第二類軀干飽滿的基礎上,又呈現出一種智慧的哲思感;第四類,學生軀干的“上、下”起伏與“呼、吸”成逆行之勢,她們以“呼提”,“吸沉”的方式展開身體上下的起伏運動,并形成一種對抗的軀干力量,當然,這種軀干并非是按照生命的常理順勢運行的,但她們卻給我們一種預想掙脫的束縛之感。
通過以上4類學生軀干與“氣”的關系來看,雖然她們皆有不同的運動趨勢,并向筆者呈現出不同的審美形態。但是,我們應該遵從以上哪種形態為標準展開訓練呢?筆者以這4類呼吸的“提沉”形態為問題研究現象,將其拿來與學校中國舞學科教師探討時發現,教師們給出的答案也不完全一致。大部分教師理所當然的認為,應該按照第三類方式進行訓練,因為這種訓練方式非常符合氣脈與身體發力的先后邏輯。還有小部分教師半開玩笑地談道:以上4類呼吸方式與“提沉”之間能夠呈現出審美的多樣性,因而它們的存在應該都是合理的,為什么只有第三類是正確的呢?事實上,前者是站在訓練形式的角度而論,后者是站在多元審美的角度而談。乍一看,以上兩種解釋好像都有道理。但作為旁觀者而言,僅從審美出發是不夠的,我們還應回歸到學生的親身體驗、感悟,來進一步探索。在第一次實驗基礎上,筆者將以上4種呼吸類型進行二次、三次、四次分配,并分別將它們置換給不同組別的學生進行體驗,在經4輪4個八拍的“提沉”后,這20名學生紛紛表示:第三類呼吸方式最為舒適,第二類僅次于第三類,第一類和第四類都很奇怪。經搜集實驗后的學生感悟時筆者發現,一小部分老師的見解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更是經不住推敲的。筆者認為,無論是從身體的外在審美來看,還是從學生的內部體悟而言:美的、舒服的即是正確的;丑的、難受的即是錯誤的。第一類和第四類的呼吸與“提沉”,顯然就處在毫不相干,甚至相互對立的關系狀態中。它們不僅給觀者帶來異常的審美感受,還讓學生感到奇怪,那么,這兩種形態的呼吸與“提沉”又怎能立得住腳呢。
基于以上實驗,以及老師、學生們給予的反饋,筆者便開始反思以往身韻教學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當我們看到學生身體運動路線、姿態不準確時,就會糾正他的外部動作或者姿態。當我們看到學生做出不完美的動作技巧時,就會讓他們重復練習,直到解決為止。事實上,無論是身體運動路線、舞姿,還是動作技巧等外部動作,都由身體內部的氣息進行平衡、調節。當動作技巧出現不協調或者不順暢之時,不一定是肢體本身的問題,很有可能是“氣”所導致的。通過上述實驗我們得知,在日后的教學中,我們不僅要關注學生的身體訓練,更要關注學生的呼吸訓練,以及呼吸與身體間的關系訓練。從此訓練視域切入,在有效提升學生對“氣”運用的同時,也能促使我們及時發現、糾正學生身體的外部問題與錯誤。
四、構建在想象呼吸法則上的形象塑造
“氣”不僅指涉的是宏觀的(氣)場,還指涉的是微觀的(氣)呼與吸,前者構筑了天體宇宙,后者連通著意識與生命。無論是微觀的呼吸,還是宏觀的天地,二者皆由一個“氣”貫穿連通,并形成一種“巨中含微,微中有廣”的一體性特征。此種特征主要體現在人與天地間的關系:人在天地中居,但在人的體內,還皆有一個小宇宙,這個小宇宙便是天地的縮影。
在傳統身韻訓練中,我們或許告訴學生應當關注呼吸,并感受氣息在體內“小宇宙”中的流動,但我們往往忽略了告知學生應該如何體驗氣在體內“小宇宙”所呈現出的具體能量。也就是說,學生應當采取怎樣的方法進行呼吸,才能讓“氣”在體內變得更具可塑性。龐丹在其主編的《中國古典舞教學諺訣匯編》中談到氣和力的邏輯關系時指出:“‘以氣催力,氣與力合,借勁運氣,順氣使勁’。氣不足則力短,力短則神散,神散則完不成人物形象的塑造。”[17](P117)通過龐丹的論述我們得知,呼吸對于促進身體的外部變化,是有一定法則與規律可尋的。它可以幫助學生建立身體內部的運行“方法”,同時也可以幫助學生塑造外在身體的“形”——人物形象。那么,我們又該如何運用“氣”來填充身體的能量呢?俄國杰出戲劇家邁克爾·契訶夫(Michael Chekhov),以想象為起點,通過“由內向外”和“由外向內”的兩種訓練方式來擴充體內的能量。如果說呼吸有兩種,一種是有關形式的呼吸,一種是有關內容的呼吸,那么邁克爾·契訶夫的想象,就賦予了呼吸一種雖隱藏但極具張力的可視形象。
對于“由內向外”的呼吸而言,筆者再次將盤腿坐姿“提沉”這一簡單且重復性較強的訓練,設置出“無想象”與“想象”的兩種呼吸類型,分別將其分配給班里的20個學生,并以10人一組取一類呼吸類型的方式展開4個八拍的“提沉”實驗。開始前,筆者賦予學生一個軟綿的指令。只有10個學生可以帶著這個指令展開想象來做,另外10人則不可以。因而,無想象組別的10個學生,就只能借助“輕呼吸”的形式來完成,身體所呈現出的內容,顯得缺少靈魂與張力。而帶著如面條、米線等具有形象性想象進行輕呼吸的10個學生,身體所呈現出的姿態就出現了不同的質感,其內在力量與外在身體都更具有生命的張力。
對于“由外向內”的呼吸而言,筆者同樣賦予20個學生兩種不同環境的指令:一是清晨陽光明媚的森林;二是夜晚漆黑的幽暗小路,并以10人一組取一類指令展開想象似的呼吸“提沉”。在實驗過程中筆者觀察到:無論是處于“提”還是“沉”的狀態,前者身體給予筆者一種明朗且向外延展的審美感受,而后者卻給予筆者一種灰暗且向內蜷縮的審美感受。綜上所述,想象為氣的內在力量,動作為氣的外在之形,人體內在呼吸的長與短、深與淺,皆能影響人體外在動作形態的發展。如此看來,想象不僅賦予學生體內之“氣”一種運動能量,還為觀眾的“賞”提供了一個有形的可視之象。
結語
“氣”在中國古典舞教學中不僅具有訓練價值,還極大地彰顯出其帶動身體運動的美學意義。雖然說對西方芭蕾的借鑒,為中國古典舞訓練體系的建構與發展開創了一條系統化、專業化的道路,但也正因受西方芭蕾訓練模式的影響,才使我們在中國古典舞教學中,忽略了氣息訓練的價值。因而,我們不僅沒有掌握如何使學生有效運用氣息進行舞蹈的方法與能力,還瓦解了中國古典舞蹈身體語言理應呈現出的文化精髓。
為進一步了解“氣”在中國古典舞身韻中的訓練價值,筆者圍繞坐姿“提沉”這一實驗個案設置出不同類型的呼吸指令,將其分別配給中國舞專業中專5年級的20名學生展開實驗,通過觀察后筆者發現,不同類型的呼吸“提沉”,呈現出的身體效果差異是較大的。但無論是學生的親身體驗,還是旁觀者的觀察,從總體而言,不好看的、不順暢的動作即是錯誤的,而漂亮的、協調的動作即是正確的。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感受者和欣賞者在審美觀念上具有大致相同的共通性,也正是因為這個共通性的存在,才使我們在體驗與欣賞的過程中,具有趨向一致的判斷力。氣的意識和氣的意念在中國古典舞蹈藝術的創作、表演中,更是一種獨特的美學表現。身體運動,造型姿態的外在表現,皆與體內的呼與吸密切相關。科學、正確的呼吸,皆能有效地調整身體的外在形式。因此,我們在規范學生身體語言的同時,也要注意規范學生的呼吸方法。此外,呼吸不僅是一種形式,它還是一種可被我們感知、想象的物質,為了讓呼吸有效地塑造不同的形象,筆者以邁克爾·契訶夫的想象為起點,更進一步地探索出“氣”在身體之內的多元可塑性與可變的張力。
綜上所述,筆者從文化自信激發出本文研究的根本宗旨,通過設置不同呼吸類型,進而觀察“提沉”的內部、外部的變化與異同,旨在使學生體悟正確訓練方式的同時,也試圖找回中國傳統舞蹈身體的訓練之根,與審美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