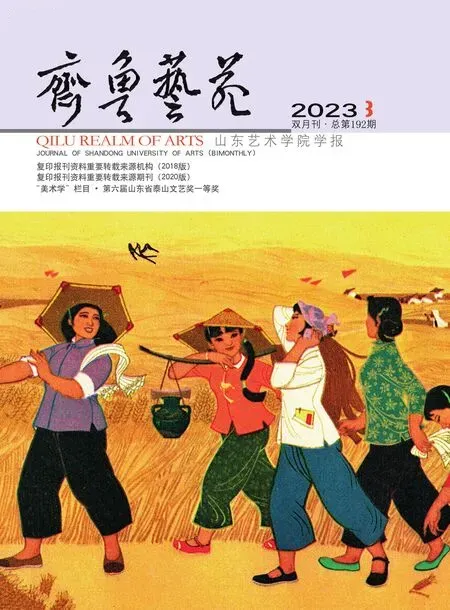中華非物質音樂文化遺產的保護光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中國傳統音樂精要集梳
劉小凡,王 珉
(1.曼谷吞武里大學,泰國 曼谷 10170;2.廈門大學,福建 廈門 361005)
聯合國在1945年成立“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簡稱“教科文組織”,并于2008年設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簡稱“非遺”。該組織以認定某個地區的文化傳承彰顯重要意義的行為或者表現為綱領指向,將其向世界公布,此名錄還收錄世界各地悠久歷史承載的傳統音樂項目。教科文組織“非遺”項目分為3類: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優秀保護實踐名冊。據央視網報道,截至2022年11月,中國有43項被列入此名錄,數量居各國之首。(1)參見:央視網新聞頻道. “中國傳統制茶技藝及其相關習俗”申遺成功[N/OL].(2022-11-30)[2022-12-06].http://news.cctv.com/2022/11/30/ARTIWkYu0EGzXrO5PHhfNSXx221130.shtml。其中,34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當中,與音樂表演藝術相關的有12項,題材、體裁各異,有數千年歷史的古老樂器和傳承數百年的戲曲和器樂表演,如古琴、藏戲、昆曲、京劇等,以及發源于福建泉州的古老樂種南音;有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歌舞和器樂表演,如侗族大歌、甘肅花兒等,還有匯集歌、詩、樂、舞、唱、奏于一身的新疆維吾爾族木卡姆;以及有著地方特色的西安鼓樂和朝鮮族農樂舞,和在廣闊地域流傳的中國皮影戲。在“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我國有7項在列,與音樂相關有2項。第3類“優秀保護實踐名冊”,我國占有1項,即“福建木偶戲后繼人才培養計劃”。(2)參見:環球網文旅頻道.我國已有43項“非遺”入選聯合國名錄名冊 居世界第一(附名單)[N/OL].(2022-11-30)[2022-12-06].https://3w.huanqiu.com/a/606a78/4Ag3eYufqdC。
幾千年來,中華民族蘊藏深厚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其中音樂表演藝術遺產令人矚目,它不同于文物類的物質文化遺產,不含固態物質媒介可長期留存在歷史長河中,而是納入活態化傳承路徑,使蘊含其中的民族音樂精髓得以蔓衍,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統音樂歷久彌新。
1.代表作名錄項目
筆者以上述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傳統音樂為例,列舉其中3項加以討論。
(1)古琴藝術。有著3000余年歷史的中國傳統撥弦樂器古琴,是當今世界起源最早、技術最成熟、音樂理論最完善,而且至今仍在演奏的音樂藝術。有關古琴的最早文字記載見于春秋時期《詩經》。古琴經歷了商周時期的產生和發展,在秦漢時期得到擴展,至公元2世紀的漢末魏初,古琴構造已趨于成形。進入唐朝(618—907),古琴形制已完全定型,與當今的古琴構造相差無幾,而且有大量漢唐以來豐富而成熟的古琴重要理論文獻傳世至今。如現存有古琴文化中最古老的樂曲《廣陵散》(圖1)、最古老的樂譜《碣石調·幽蘭》和最古老的琴歌《古怨》。2003年教科文組織把古琴藝術列入世界第二批“非遺”代表作,之后,我國相關政府部門和國家藝術基金在不同程度對古琴藝術的傳承、宣傳、發展等項目進行扶持和參與,較之20年前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古琴藝術受到一定的關注,但是其生存狀況卻不容樂觀,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其一度出現傳承斷層現象,面對技藝處于瀕臨失傳的境地,挽救古琴藝術刻不容緩,中國新聞網曾在2007年對此報道,“建國后第一批古琴名家,如今已屈指可數,古琴藝術正面臨著人去藝亡的危機”[1]。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代表作名錄對我國古琴的調查報告(期限至2024年新報告發布之前)(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官網規定:締約國每6年提交一次《公約》執行情況報告。新一輪報告將于2024年12月15日發布。參見:UNESCO. Guqin and its music[EB/OL].[2022-12-07].https://ich.unesco.org/en/RL/guqin-and-its-music-00061。:“如今,受過良好訓練的古琴演奏者不足1000人,幸存的大師可能不超過50人。最初的幾千首曲目已經急劇減少到今天定期演出的僅有100首左右”。[2]

圖1 青島嶗山太清宮道教懷常道長演奏古琴曲《廣陵散》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古琴文化受到冷落而逐漸滑入邊緣文化之列,有諸多原因,歸納為3點。其一,從社會層面,信息時代注重大眾傳播媒介的發達時效性,是最快最便捷且是最全獲取文化信息的渠道,它依賴于廣播、電視、報刊或是網絡,然而縱有這些發達渠道卻很少有對古琴藝術的介紹和傳播,人們接受傳統文化熏陶日漸減少,大眾階層對古老的古琴文化的知曉度比較低,影響了它的傳播和普及;其二,學校教育方面(特別在高校),現代音樂教育的審美標準大都以西方音樂體系為基礎,課堂上多依附于鋼琴、五線譜教學方式為主,中國傳統音樂的教學在萎縮,古琴文化也就更難在此環境中獲得立足之地;其三,從專業人才層面來看,目前各家琴派的傳人寥寥可數,即便在專業音樂團體,真正專職演奏古琴的人才也是鳳毛麟角。而最具專業水平的高等音樂院校,從事古琴教學和研究的教師,他們當中多數也是在從事其他專項教學之余附帶地搞搞古琴教學和研究而已。
(2)南音。融匯唱、奏于一體的南音表演藝術,流傳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植根于閩南大地的南音,主要集中在以泉州一帶為發源地的福建東南部,包括廈門、漳州和晉江,也在我國臺灣及東南亞的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閩南人(華裔)聚居諸地廣為流行。2006年,南音被國務院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于2009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代表作名錄。被譽為“中國古代音樂活化石”的南音,2023年又登上央視總臺春節晚會大舞臺,彰顯了這一傳統音樂千年傳承的魅力。南音有7件主奏樂器:南琶(南音琵琶)、洞簫、三弦、二弦、拍板、噯仔和南音竹笛(傳統上稱品簫)。以南琶為例,它與唐朝琵琶樣式基本一致,其形制特征表現在樂器頭部向后彎曲,大腹琴體面板兩側各有鳳眼,四相九品。之所以叫做南音琵琶,是因演奏福建南音而得此名。南琶和古代不同時期的琵琶,如唐朝敦煌壁畫上的樂伎橫抱琵琶造型(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南壁中的琵琶圖像)、唐宋時期的《宮樂圖》,以及五代《韓熙載夜宴圖》中女子橫抱琵琶的彈奏姿態,還有保留至今福建泉州開元寺內的木雕飛天樂伎,在樂器形制、演奏姿態等方面極為相似,仍保持較早時期的琵琶形制和橫抱演奏方式。筆者也以文獻研究和田野調查的實例,對上文南音琵琶與唐朝琵琶存有密切的淵源關系提供一份驗證(圖2—圖4)。

圖2—圖4 圖2:早年中國考古隊從唐朝墓穴挖掘彩繪陶制四個女樂俑之一,現藏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3]。女樂俑橫抱琵琶的姿態、右手持大型撥子撥奏琴弦的手姿,與當代南音琵琶樂器形制和演奏形態極為相似;圖3:木雕飛天樂伎橫抱琵琶,出自始建于唐朝的泉州開元寺甘露戒壇殿,數十米高的殿堂房梁上面安置24尊手持樂器的飛天樂伎木雕,此圖為其中一尊(王珉攝,2009年1月8日);圖4:臺灣南音名家卓圣翔(1945— )橫抱“南琶”演奏南音(王珉攝于廈門翔安“歐厝南音泥土計劃”,2021年3月6日)。
(3)甘肅“花兒”。“花兒”主要在大西北甘肅、青海、寧夏三大省區流傳,在新疆、陜西和四川局部地區也有流傳。2009年9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收錄“甘肅花兒”為代表作名錄的官網認證詞中提到:“在甘肅、青海以及整個中國中北部地區,九個不同的民族共同擁有一種被稱為‘花兒’的音樂傳統。……無論是在田野干活的農民情不自禁放聲歌唱,還是四處巡演,或者是在這些省份每年舉辦的100多個更正式的傳統花兒節演唱,‘花兒’都是在社會環境和跨民族文化交流中表達個人情感的重要載體,也是一種流行的農村娛樂表演。”[4]在我國,研究“花兒”之先行者當屬地質學家袁復禮(1893—1987),他于1925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學《歌謠周刊》發表了《甘肅的歌謠“話兒”》,這一期同時還刊登了他采集的34首“甘肅歌謠”,其中有山歌“花兒”30首,秧歌小調4首。確切地講,“花兒”的核心體裁是山歌,甘肅渝中人張亞雄(1910—1990)是用樂譜記錄“花兒”山歌第一人,民國年間他編著的《花兒集》于1940年由重慶“青年書店”出版,1948年蘭州再版,1986年北京第三版(4)參見:張亞雄編.花兒集[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86。,其中收錄4首用簡譜記錄的“花兒”曲令。關于“花兒”之稱謂,早在明朝初年(1368年前后)就已在甘肅一帶流傳。如今當地歌手依舊承襲古老的民間“花兒”的叫法,其實原本只稱“花”,后來“花”字兒化音了,便產生文字記錄的“花兒”一詞,所以學界也常以口語相傳的“花兒”稱謂取代之。因地域得名的“洮岷花兒”,是甘肅“花兒”的發端,尤以甘肅南部的岷縣、臨夏一帶山區更具特色,600多年來傳唱于岷山洮水之間。近年來學界對“洮岷花兒”的研究在不斷深入,而且當地政府和民間組織也定期舉辦漫山遍野的“花兒會”和賽歌會(圖5),呈現出一派熱潮景象。

圖5 兩名甘肅“花兒”女歌手在對歌“洮岷花兒”
花兒作為一種世代沿襲的民俗文化活動,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文化大繁榮的同時,也受到現代文明的強烈沖擊,活態化的“洮岷花兒”生態文化環境正發生異化,表現在生態空間、“花兒”歌手的延續、“花兒”的傳播和受眾面等方面遇到空前的現實困境,面臨自“花兒”產生以來的第一次真正的危機。例如,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花兒會,原本賴以生存的原生態人文環境因過度地受到商業文化影響,削弱了“花兒”的音樂屬性,花兒會出現一種怪相,有“洮岷花兒”歌手擯棄原聲唱法,效仿西洋唱法和流行音樂風格,演唱貌似“花兒”的流行歌曲,而且還頻頻出現在電視轉播節目中,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歌風正侵蝕著“洮岷花兒”樸實無華的原生態演唱特征。甘肅“花兒”是西北人民積淀智慧的結晶,其中“洮岷花兒”獨樹一幟,為此,杜絕社會上出現商業為主、花兒演唱為輔這種本末倒置的花兒會現象,恢復花兒會的原本面貌,制止流行音樂歌手的歌風滲透本土“花兒”音樂土壤,是有效保障“花兒”藝術永續發展的必要手段。
2.急需保護的“非遺”項目
早在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便設立了“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5)參見:中國政府網.中國3個項目被列入聯合國“急需保護的非遺名錄”[N/OL].(2010-11-16)[2022-12-07]. http://www.gov.cn/govweb/jrzg/2010-11/16/content_1746193.htm。,在2024年新一輪報告發布之前,我國有7項收錄其中,音樂項目新疆維吾爾族麥西熱甫(2010)、赫哲族說唱藝術伊瑪堪(2011)赫然在目。學者張一凡指出:“今日赫哲文化依然保持的傳統文化的因素,是恢復它為活態保存的基礎”。[5]被譽為赫哲族百科全書的伊瑪堪,以傳承人為主體,以口頭說唱為傳播載體,在當地族群生產生活過程中代代相傳,真實映照了它的鄉土特色,讓我們今天仍能有幸看到這種口傳藝術的活態化傳承模式。伊瑪堪的活態傳承路徑來自3個方面:家族傳承、師徒傳承、民間歌手之間的互傳。“赫哲”用作族稱最早出現于康熙二年(1663)。1930年,當時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家凌純聲(1902—1981)親赴中國最東部依蘭、撫遠一帶做田野調查,并于1934年出版《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在第一章第6節“現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提出“赫哲族”為正式族稱,并沿用至今。(6)參見: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赫哲族人居住地域廣闊,分布于我國東北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江的三江流域,是中國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21》,中國境內赫哲族的人口數為5373人,其中男性2558人,女性2815人。(7)參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 202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21。赫哲族只有本民族語言而沒有本民族文字,也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沒有屬于自己獨具樂器的民族。伊瑪堪說唱藝術最遲不晚于20世紀初就已形成成熟的演唱風格,其精妙之處在于沒有任何樂器伴奏而采用徒口清唱,辨認它的音樂特征,只能從其世代口頭傳承的藝術話語中加以領悟。伊瑪堪為“無伴奏”一個人說唱表演,唱段形式講究節奏押頭韻,采用葉韻(xié yùn)和散文體互為合轍押韻的語言結構,擅長用情緒多變的不同唱腔來展現說唱中的人物各異,講述部落征戰、生活民俗以及赫哲族英雄除暴安良、降妖伏魔的英雄主義氣概。表演者既保留世代延續的傳統說唱形式和內容,也展示了個人臨場即興發揮的表演技能。依據赫哲族人的傳統,伊瑪堪有“大唱”和“小唱”之分,前者以說為主,表演赫哲族人創世傳說的英雄人物莫日根,描述莫日根的各種經歷;后者以唱為主,描述短篇抒情性內容的故事情節。伊瑪堪說唱藝術篇幅宏大,根據學界已采錄的資料,將它們記錄至現代文字來表述,每一部都在幾萬字至十幾萬字,優秀的伊瑪堪藝人可以連續說唱一二十天,以口傳藝術創作如此浩瀚篇幅,令人嘆為觀止。有學者曾對赫哲族聚居地黑龍江省同江市街津口鄉的伊瑪堪音樂做過調查,在20世紀30年代,該地區有相當一部分赫哲族藝人能用赫哲族語說唱伊瑪堪,到1980年代,仍能看到一些民間藝人在完整地說唱伊瑪堪,而在2012年的考察過程中,發現“隨著會唱‘伊瑪堪’的老藝人的相繼辭世,目前很難再找出一個能地道、完整地講唱傳統‘伊瑪堪’的藝人”[6]。
赫哲族人以百年智慧和情感傳承積淀的說唱藝術伊瑪堪,在傳承赫哲族語言、信仰、民俗和習慣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卻面臨失傳的窘境,究其原因涉及很多方面,筆者提出其中兩點,需引起人們重視。其一,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變遷,赫哲族人的生產生活以及文化背景正逐漸與其他民族相融合,現代生活方式滲透到赫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對生活的向往實現了從物質到精神的升級,經世代傳承的說唱藝術伊瑪堪其原有的娛樂功能、凝聚功能和習俗功能,在多數赫哲人心目中的自豪感趨于弱化,多數人已不懂赫哲語,導致對伊瑪堪知之甚少;其二,被譽為“赫哲族百科全書”的伊瑪堪,是獨有的口耳相授的民間說唱,它具有原生性、本土性、即興性的內在特質,而今伊瑪堪卻失去了其賴以生存傳承的文化生態土壤,蛻變成為學者學術研究的對象,而且在政府助推與資本運作的模式中,許多地區利用商業手段包裝宣傳伊瑪堪,傳統質樸的伊瑪堪蛻變為旅游產業,出現在舞臺上、商業街、觀光場所,一味地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在本質上顛覆了伊瑪堪原有的音樂相貌。這也就不難理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何把伊瑪堪列入“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我國政府為此也向教科文組織履約承諾工作,加強對赫哲族伊瑪堪民族傳統藝術的搶救保護,還原伊瑪堪的真實面貌,目前,僅在上述赫哲族主要聚居地之一的同江市,當地政府就已經建立起國家、省、市、縣四級對“非遺”項目伊瑪堪急需保護的傳承體系。
3.優秀保護實踐項目
目前,全球收錄“優秀保護實踐名冊”有33項,涉及31個國家。(8)UNESCO. Browse the Lis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Register of good safeguarding practices[EB/OL].[2022-12-07].https://ich.unesco.org/en/lists.我國“福建木偶戲后繼人才培養計劃”于2012年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優秀保護實踐名冊”,(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2012年12月公布此消息,根據當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會會議批準的年月,入選全球“優秀保護實踐名冊”項目有10項。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福建木偶戲人才培養計劃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冊[EB/OL].(2012-12-06)[2022-12-07].http://www.scio.gov.cn/zhzc/35353/35354/Document/1503813/1503813.htm。實現了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此項目名冊零的突破。鑒于福建地區獨特的人文環境,賦予了木偶戲鮮明的音樂特征,從而打上了地域烙印并持續繼以傳播,至今仍在當地傳統音樂中產生重要影響。換言之,地域認同是指一種傳統音樂在認定的地域環境中與社會環境交融,通過順向推導所生成的認知方式,而逆向推導,其邏輯關系不存在。以福建木偶戲為例,它實為匯集泉州提線木偶戲、漳州布袋木偶戲和晉江布袋木偶戲的合稱,在地域文化交融中又各自獨立。雖然三個戲種不一,呈現的木偶造型豐富多樣,但福建木偶戲展現的偶頭雕刻藝術,在繼承唐宋雕刻和繪畫風格,注重偶頭人物性格的表情刻畫,為這三個木偶戲種所共有,即夸張變形的偶頭輪廓,粉彩描繪的清晰線條(圖6)。

圖6 福建木偶戲偶頭雕刻大師江東林(1978— )作品,后排左起是東漢末年名將典韋、孫悟空、大頭,前排左為花臉武生,右為南宋初年奸臣秦檜(王珉攝于福州市三坊七巷“福建非物質文化遺產博覽苑”,2021年7月17日)。
作為福建木偶戲構架之一的泉州提線木偶戲有著上千年傳承歷史,它源于秦漢時期,在唐朝中期隨中原漢人遷徙入閩。公元10世紀提線木偶戲首先在泉州、漳州及周邊地區興起,歷經后續朝代和民國,至今從未間斷。經年代的積累,演員表演的傳統戲曲匯集了豐富的語言特色,有著鮮明的地域認同感,表現在唱腔有閩調、京調、畬歌,道白有閩南話、畬語、浙南腔等。在國內眾多木偶戲戲種中,唯有泉州提線木偶仍保留自己的劇種唱腔,行腔曲牌多達近300支,傳承保存下來的傳統戲曲劇目有700多部。與我國多數傳統木偶戲表演相比,提線木偶演員雙手操控桿的手法技巧難度最高,全靠精致準確的抽線操縱技術,來把控支配人體不同動作的若干提線組。在樂隊伴奏下,演員配合木偶角色動作連說帶唱,一身多能,眼花繚亂的木偶特技動作,在演員手下被演繹得出神入化、栩栩如生。提線木偶的高度在60—70厘米之間,普通木偶配置8—16條提線,復雜的木偶頭像內設置的提線最多的有30多條(圖7)。雕刻木偶頭的精湛刀功決定著木偶道具的精美程度,而木偶頭最重要的表現部位是木偶臉的雕刻造型,工匠根據木偶角色的外形、性格、身份、經歷和氣質,涂上相應的色彩,擬人化的木偶神態深深融入到木偶角色的神髓之中。
福建木偶戲另外兩個構架元素包括漳州布袋木偶戲和晉江布袋木偶戲,觀其布袋木偶戲的外表,除了戲偶頭、戲偶手掌和足部為雕刻而成,偶身的軀干和四肢都以布料縫制的服裝取代之,正因為這類戲偶外表在民間被描述為“用布料縫制的袋子偶”,因此有了布袋戲之通稱(圖8)。雖然漳州和晉江兩地的布袋木偶戲同根同源,但在木偶戲歷史文脈的傳播過程中,它們在各自特定區域環境中打上了不同的地域烙印,形成各具特色的布袋戲風格。在古代,民間藝人表演的各類木偶戲統稱傀儡戲,布袋木偶戲是傀儡戲之一,因此布袋木偶戲自古又稱手袋傀儡戲、手操傀儡戲。南宋時期的漳州手袋傀儡戲備受百姓歡迎,當時履職漳州知州(10)“知州”為中國古代官名。宋朝由朝廷委派朝臣到州一級履職的地方行政長官,稱“權知某軍州事”,簡稱知州。的朱熹(1130—1200),頒布了10條“勸諭禁戲”,其中第10條規定:“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財物,裝弄傀儡。”[7](P301)布袋木偶戲始于何時,尚缺少明確的歷史文獻證明,但從朱熹的勸勉曉喻,可以看出在南宋時期,布袋木偶戲在漳州一帶已相當盛行。在漳州,藝人稱布袋木偶戲“掌中戲”“指花戲”,演員將手套入戲偶的服裝中操偶表演,是對手掌和五指靈活操偶技法的考驗。近代閩南布袋戲以漳州最具代表性,表演風格類似京劇,在音樂唱腔和扮演做派上依循京戲套路,唱的是北調,如昆腔、京調等,戲班做派突出京班特色,以武打戲、鬼怪戲和滑稽戲表演戲曲情節居多,注重表演動作節奏明快迅捷,因而被稱為北派戲。它被譽為南派布袋木偶戲風行于晉江、泉州一帶,唐朝開元八年(720)晉江屬于泉州府晉江縣,現為由泉州市代管的下轄縣級市。晉江布袋戲實指泉州地區掌中木偶戲,五代時期(907—960)在“晉—泉”地區流行。晉江布袋木偶戲依附于當地戲曲聲腔劇種,用泉腔演唱,在閩南俗稱“掌中傀儡”,戲曲界稱其傀儡調,其中許多唱腔移植自泉州提線木偶和梨園戲的傳統劇目,并吸收了泉州南音曲牌精華。晉江南派布袋木偶戲精于運用語言藝術,“泉腔泉調”的地域文化特征明顯,表演中注重方言說白,素有“千斤道白四兩曲”的說法。

圖8 漳州木偶劇團演員鄭玨表演布袋戲
作為木偶戲大省的福建,木偶戲種類繁多且分布地域廣,自古享有“木偶之鄉”的美譽。“文革”十年浩劫,傳統戲曲淪為“封資修”遭到封殺,古老戲種日漸式微,各地盛行的布袋木偶戲也未幸免,布袋戲藝人被遣散,后繼乏人。“文革”之后,各地木偶戲雖然重返舞臺,但受到現代文明的沖擊,其中布袋木偶戲也沒有像以前那樣火爆,至今在各地依然是不溫不火。在民間,布袋木偶戲一直是自發性娛樂表演,供自身或周圍人觀賞的戲曲生態形式,多數藝人出自農家,他們亦農亦藝,農忙種地,農閑表演。在城市,現代影視、動漫游戲、互聯網等新興文化對布袋木偶戲市場造成的沖擊不容忽視,僅泉州一地,“1990年泉州尚存有60多個民間布袋戲劇團,而如今僅剩不到20個,布袋戲的保護和傳承工作日益緊迫”[8]。當今無論“城”“鄉”,布袋木偶戲曲的傳承光大和演出場所,這兩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戰表現在,前者面臨藝人日趨老齡化后繼乏人,傳承堪憂;后者是觀眾流失,尤其年輕觀眾越來越少。要扭轉這種局面,政府的決策對推動木偶戲曲的傳承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2022年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廳、福建省藝術館、福建省劇協木偶藝術專業委員會,聯手下屬市級有關單位,共同企劃出臺了“福建木偶戲后繼人才培養計劃”課題研究,這對扶持發展福建木偶戲和非遺保護政策構筑了根本性保障。
綜上所述,我國傳統音樂門類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中已占有一定比重,為世界音樂文化多樣性貢獻了“中國色彩”。在筆者看來,中國有著遼闊的地域空間,民族眾多,原生態的民間音樂和豐富的傳統音樂數不勝數,以上對“非遺”榜上有名的民間和傳統音樂項目的解讀,僅僅是幾個例子而已,還有無數優秀的傳統音樂戲種、樂種和樂器,雖然并不在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之列,但它們是我國各民族音樂文化積淀的一項重要標志。然而我國許多具有地域性、傳承性和民族性特征的音樂藝術形態,因種種原因,其賴以生存的土壤正日益散失,處于瀕臨失傳的危險境地。譬如有些地區民間音樂家年事已高,依靠口傳心授傳承的特色音樂后繼乏人;一些地方戲曲劇團因缺乏資金支持,微薄的薪水讓藝術家很難維持現代社會的生活成本,心緒浮躁無心工作,導致許多傳統地方戲種陷入難以為繼的窘境。新華社記者周瑋報道,1983年全國共有374個戲曲劇種,到2012年已經減少到286個,減幅為23.5%,其中74個劇種只有1個職業劇團或民間班社,處境岌岌可危,面臨“團散劇亡”的困境。[9]
進入21世紀,隨著城市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自身的吸引力和便利的生活條件讓鄉鎮勞動人口也向城市遷移,在這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轉型時代,民間傳統音樂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都在發生著變化,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面對正在失傳、斷代的諸多民間傳統音樂,地方政府出臺相應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本土音樂進行有序保護。國家部委為此也實施了一系列繼承傳統、挖掘優秀音樂遺產的拯救工作。財政部在2010年下撥600萬元用于“中國民族音樂發展和扶持工程”。(11)中國政協網.3981號提案復文[EB/OL].(2012-02-24)[2022-12-09].http://www.cppcc.gov.cn/zxww/2012/02/24/ARTI1330050198605249.shtml。2013年,文化部出臺“實施地方戲曲劇種保護與扶持計劃”。(12)參見:中國政府網.地方戲曲處境堪憂 74個劇種面臨“團散劇亡”[N/OL].(2013-07-24)[2022-12-09].http://www.gov.cn/govweb/jrzg/2013-07/24/content_2454619.htm。在過去的2020年,許多地區包括貴州、湖北、廣東、云南、福建、內蒙古、青海、新疆、上海、北京、澳門等等,對民間傳統音樂“非遺”項目展開搶救保護工作。(13)參見:李宏鋒,馮卓慧等.2020年度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報告[J].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2021,(3)。貴州省組織專家評審會,對本省安順地戲、苗族蘆笙制作、侗族大歌、布依族八音坐唱和盤歌的傳承人給予扶持,對實際困難予以解決;湖北省人民政府在2020年1月公布了第六批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傳統音樂黃岡“羅田民歌”和苗族“宣恩花鑼鼓”入選;同年4月,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公布了第六批省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傳承人名單,有9名民間音樂家入選,他們為傳播廣東音樂、潮州音樂、梅州客家山歌、排瑤民歌等本土音樂做出了突出貢獻。學術界也在關注傳統音樂類“非遺”保護工作,產出的一批卓有成見研究文章,進一步深化“非遺”項目的搶救保護,為政府提供了有價值的學術參考資源,在此不一一列舉。正如這份報告所言:“綜觀2020年度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各項工作在既有成果基礎上繼續發展,……傳統音樂類項目展演豐富多彩、傳統音樂遺產保護研究不斷深化等特點。[10]國家新聞出版署2022年度 “中華民族音樂傳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項目”申報工作中,也再次強調闡發民族音樂文化精髓、保護民族音樂珍貴資源的重要性。(14)參見: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新聞出版署關于開展中華民族音樂傳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項目2022年度申報工作的通知[EB/OL].(2022-07-29)[2022-12-09].https://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79/104741.shtml。當前,各地區 “非遺” 傳播和保護發展狀況不一,政府、學界和民間三者須形成合力,瀕危民間傳統音樂搶救性挖掘和保護工作仍任重而道遠。只有把搶救性保護工作做實、做好,才能迎來更大機會,借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非遺” 平臺,讓更多優秀的中國民間傳統音樂映入世界公眾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