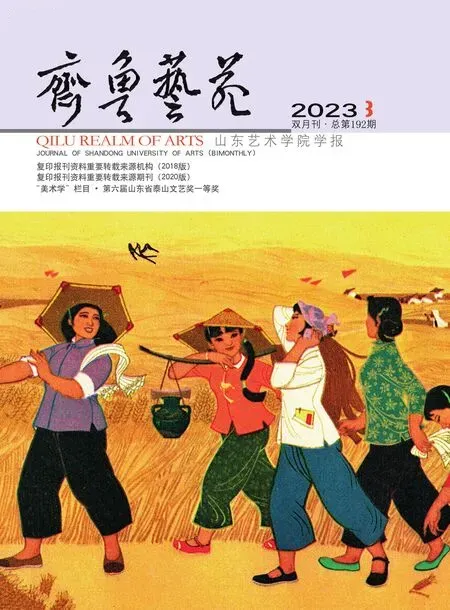揚琴藝術教學在魯南五大調中的傳承與創新
成慧青,徐振清
(山東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韓國湖西大學,忠清道 牙山)
一、揚琴藝術與魯南五大調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統音樂類——魯南五大調是流行在魯南、魯東南一帶的民間大型演唱曲種。主要盛傳地在今臨沂市郯城縣馬頭鎮和日照市等地。距今已有近300年的歷史,2008年被列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雖然稱它為民歌,但與其他民歌體裁,諸如小調、山歌、號子等差別很大,在唱詞和曲腔方面有著自身鮮明的特點,它屬于曲牌體民歌,這是它重要的標志。五大調包括淮調、滿江紅、玲玲調、大寄生草和大調五種曲牌,故稱五大調。
五大調之“大”,也是與其他民歌相比較而言,這五種曲牌,都有不同的演唱形式,如“輕板”“疊板”“帶把的”。在演唱時還夾唱其他民歌、小調,如疊斷橋、剪靛花、小郎調、鳳陽歌等等。它的曲腔結構復雜,一首曲目就要演唱幾分鐘、十幾分鐘,而且彎腔多,有長達二十拍的大拖腔。五大調優美動聽,演唱難度大,所以在郯城縣馬頭鎮一帶的五大調藝人把它稱為“雅調”“細歌”。魯南五大調是有伴奏的民歌,在長期的演唱過程中,形成了諸如“過板”“腰板”“起板”“煞板”“茂調大變腔”“茂調小變腔”等一系列演唱術語。五大調的曲體結構和演唱形式是與歷史上唐宗大曲、元曲、諸宮調以至明清時代俗曲一脈相承的,就全國范圍來看,現有的民歌像這樣的演唱是少見的。現在可以看到的有些曲牌體音樂如揚州清曲、四川清音也有相似之處,但說唱性很強,篇幅也是相對較短小的。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山東省群眾藝術館專門派人對魯南五大調進行了搜集和搶救性整理,在臨沂、日照等地走村串戶,與老藝人座談討論、錄音整理了一批珍貴的樂譜和文字材料,才使我們在今天還能完整地欣賞五大調的風采。魯南五大調保留了它獨有的原始民歌風貌,是山東民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是山東民間藝術的瑰寶,不僅有較強的藝術價值,更彰顯了其彌足珍貴的歷史研究價值和現實傳承意義。它優美細膩、淡雅抒情的曲調,備受音樂界青睞,對于研究民間音樂的發生和沿革以及豐富中國當代音樂,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揚琴,源自西亞波斯、亞述等地,在西亞和東歐十分流行,在匈牙利它是重要的民族樂器。自明朝后期傳入我國,距今約有400年的歷史。最早出現在廣州一帶,從南向北傳播普及,在19世紀末傳入山東魯西南一帶。而根據資料,把揚琴應用于曲藝和戲曲的伴奏乃是近現代的事,也不過百余年。新中國成立后,揚琴藝術的發展很快,揚琴藝術的教育教學也漸成體系,并以自身的優勢登上民族樂隊的領軍地位。把揚琴用于魯南五大調的伴奏是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的,至今已有50多年。
起初,五大調演唱者看到山東琴書藝人使用揚琴伴奏,感覺悅耳動聽,就試著把揚琴用作伴奏樂器。在郯城縣馬頭鎮演唱五大調的伴奏樂器是多樣的,很具包容性,它包括吹管類、敲擊類、弓弦類、彈撥類等等。五大調的伴奏很具特色,比如在演唱中使用瓷碟、酒盅、瓷碗,敲擊花樣繁多,如自制的錢琴、大小花鞭,在其他演唱中比較罕見。魯南五大調的主弦樂器是三弦,在演唱時三弦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有特殊的定弦方法:“合、四、工”即“5、6、3”。雖然揚琴進入樂隊但仍處于輔助的地位,有無皆可。隨著魯南五大調演唱形式的發展,從坐唱到站唱,從庭院式的家庭文化娛樂活動到搬上大舞臺,服裝、道具、燈光、舞蹈等舞臺元素的加入,魯南五大調的伴奏樂隊也發生了質和量的變化,揚琴以優美雋永的音色,和諧格致的氣派,以及文雅端莊的造型,逐漸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它貫穿五大調的始終,表現在唱腔過門的演奏、隨腔伴奏、接腔送韻等方面,在五大調的藝術表現中處于組織者的地位,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揚琴藝術的特點
揚琴是一種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擊弦樂器。它以音域寬廣、音色優美、表現力豐富而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中國式音樂會大揚琴,音域可達5個八度,為揚琴中最寬的音域。
揚琴是中國民族樂隊中必不可少的樂器,無論用于獨奏、伴奏還是合奏,其特點都可以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揚琴的音色豐富多彩,低音區發音朦朧、雄厚而深沉;中音區柔和、純凈而透明;高音區清脆、明亮;最高音區則比較尖銳、立體感強。演奏旋律時主要使用中音區和高音區,較少接觸到最高音區。低音區少事旋律,多用作和聲的襯托,音樂渾厚圓潤。同時,揚琴的半音齊全,在演奏時可以靈活轉換調式,演奏手法規律化。
揚琴演奏技巧的基本訓練是學習揚琴重要基礎。揚琴的演奏技巧多樣,有:單竹類、齊竹類、輪竹類、顫竹類、揉弦類、撥弦類、抓弦類、點弦類及裝飾音類等等。它是揚琴傳統常規及創新技巧的全面匯總和系統分類,是現代揚琴演奏藝術的總體概括。[1]各種技巧的實踐方法、理論及運用都是建立在基本訓練之上。因此,我們著重探究一下揚琴演奏技巧的基本訓練方法。首先必須遵循揚琴基礎教學的基本規律,教學方法要有針對性和可行性,特別要重視對基礎演奏技巧的訓練及揚琴教學的基本科學理念。揚琴演奏是須心神專注的運動,我們的學生在有些時候無法領會演奏中的寓意,總是古板地、慣性地演奏樂曲,不僅嚴重背離了演奏的客觀規律,也增加了自身的心理負擔。因此,要教會學生演奏時要輕松自如,如手腕盡量放松,雙臂在腕力的作用下自然下垂去有彈性地擊弦等等。由此使學生充分掌握和理解手腕力量的使用等原理。同時在教學中我們要注意樂感的培養,樂感簡單來講就是對音樂的感受力、想象力和表現力。揚琴演奏最終的目的就是要用琴聲來表達音樂。因此樂感的培養在揚琴教學中就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實際的揚琴教學中,我們總是在強調演奏要領,例如手形是否正確、手腕放松等等,但在強調基本要領的同時忽略了音樂的本質(表現力),遏制了學生樂感的發展,所以我們要教會學生能夠運用正確的科學方法進行練習,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及大量的演奏實踐,能夠熟練地運用各種演奏技巧將音樂的涵義充分地表現出來。另外,因為每個學生的接受能力、領悟能力存在差異,揚琴教學同樣也要做到因材施教,各有側重。
三、揚琴藝術教學在魯南五大調中的傳承與創新
將魯南五大調的傳承與創新納入揚琴藝術教學實踐,這是一個嶄新的課題。這一課題的確立和教學程序的啟動必將對年輕一代的成長產生積極的影響。首先,通過這一課題的學習,可以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創新的重要社會意義在思想層面的認識,從而培養和造就一批有揚琴藝術才能并熱心參與魯南五大調傳承和創新的生力軍,挑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重任。通過理論學習和技能訓練提高個人音樂素養,對于將來步入社會干事創業、樹德立行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揚琴藝術教學有著自身的專業特點、運轉規律和行業規范。但與其他學科的教學目的殊途同歸,即是傳遞知識、培養人才,在人的社會進化過程中使受教育者有一技之長,可以謀生,益于社會。學校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手段,把魯南五大調納入揚琴藝術教育,把傳承與創新作為教學目的,方向是正確的,課題是可行的,教學是大有希望的。
(一)牢固基礎、提高技能
理論知識的學習和基本技能的訓練是教學的重要內容,只有具備堅實的理論基礎知識和運用自如的操演技藝,五大調的傳承與創新才能成為可能。理論知識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總結,它可以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揚琴藝術教學不僅要踏踏實實的學好近現代西方音樂理論知識,更要深入的學習和研究我國傳統宮調理論,這正是打開魯南五大調音樂藝術之門的鑰匙。充分利用揚琴藝術的優勢深入開掘魯南五大調的音樂內涵,在教學中,解決好“普及”與提高二者之間的矛盾。大量的民間藝術都為群眾喜聞樂見,這就是傳承和普及意識,而在此基礎上使之發揚光大,就是創新,就是提高意識。具有駕馭音樂藝術的能力,把傳統文化的精髓吃透,才能在教學實踐中出成果,出成績,出精品。
(二)正確把握傳承與創新二者之間的關系
傳承和創新二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傳承決定了創新的本質因素,這正如人類的繁衍,人類的血緣關系就是人類的生命傳承。而創新就是發展,創新為傳承注入活力,傳承是土壤,創新是花果,實際上,傳承與創新就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
傳承在先。傳承二字雖然“傳”在前,事實上應該是先“承”而后“傳”。“承”就是繼承,則所謂“承前”方可“啟后”。這就要求我們在教學實踐中首先把優秀的傳統文化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厚積而薄發,才可以把技藝傳給后人。將魯南五大調納入揚琴藝術教學,這給正常的教學提出一個超出了原有教程的新的領域。對于魯南五大調的音樂研究,甚至古詩詞以至戲曲等藝術形式都有涉及,教材的編寫必然覆蓋五大調的歷史淵源、音樂藝術特色、唱詞的文學賞析、五大調流行嬗變和發展狀況,要據此提出發展創新的方向、目標及實施方案。其中,五大調音樂的開掘是重點,重中之重是揚琴藝術教學以自身優勢的能動性推動魯南五大調的傳承與創新實踐的真正落實。
針對中國民樂合奏作品,特別是據民歌改編的樂隊作品,及民樂隊伴奏的民歌,在樂隊寫作方式和演奏技巧應用上,或多或少存在著滯后,從現代人的聽覺系統出發,音響上略顯蒼白、單薄、陳舊。其中以大齊奏手段為主的民樂隊寫作方式,同樣出現多數改編作品中。由此產生的主次不清晰,音色不凸顯等問題,大大降低了民樂隊和作品本身的藝術表現力。在傳統的五大調作品中,則基本采用了齊奏。
作為郯城人和一名揚琴演奏者,筆者從所參加的魯南五大調演奏活動中,深刻體會到其中樂隊使用的尷尬現狀和揚琴技巧落后等問題。對于揚琴在樂隊中的演奏,要求奏者具備一定的演奏水平與合奏經驗,同時也應注重演奏的靈活性和多樣性,甚至要求演奏者掌握一定的和聲知識和即興演奏技巧。在近代作曲家的大型民樂隊作品中,對揚琴的音色要求和樂隊整體掌控能力則更是對揚琴演奏家的試金石,如《鳳點頭》(許昌俊)、《春秋》(唐建平)等。
創新比傳承要有難度。但也并非高不可攀。事實已經證明,揚琴藝術在魯南五大調的音樂活動中,創新是可行的。為對傳統民樂合奏曲目進行繼承與改良,充分發揮揚琴的音色和演奏技術,傳承民族音樂文化,由山東藝術學院成慧青(教授)、魯南五大調傳承人楊新儒先生、徐振清(碩士研究生),將《日照滿江紅》這一魯南五大調傳統曲牌,改編為具有新時代技術內涵與民族精神的民族管弦樂作品。2017年4月,山東藝術學院徐振清揚琴藝術碩士畢業獨奏音樂會上,一曲大寄生草《齊風魯韻情未了》和滿江紅《好一朵玫瑰花》兩首魯南五大調揚琴藝術演奏曲均獲成功,被專家學者認可。雖不能說十全十美,但也足以說明揚琴藝術教學在魯南五大調中的傳承和創新是可行的,這一大膽嘗試已經把揚琴藝術教學與魯南五大調的傳承與創新有機的聯結起來,當然,把魯南五大調的傳承與創新納入揚琴藝術教學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新的音樂元素會不斷加入,一些新穎的演唱、演奏、作曲技法會被采用,魯南五大調會更加豐富多彩。
揚琴在魯南五大調的樂隊伴奏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在樂曲演唱前,揚琴演奏者的手勢要給予示意,有帶入引導的作用。在樂曲的開始,會加入揚琴的獨奏,雖較短,但起到引子的關鍵作用。在整個樂曲的演唱中,揚琴是隨著樂曲伴奏的,根據演唱者情緒的起伏,演奏者也要適當調整演奏力度,音色似珠落玉盤,晶瑩剔透,做到“彈唱合一”,多數五大調樂曲中,揚琴采用輪竹及雙音和弦的演奏較多,輪音猶如涓涓細流,潺潺不止,使音樂細膩婉轉,簡短的彈輪密集緊湊,使之輕巧明快,加上演奏中經常出現雙音及前十六后八的節奏型,更是顯得音樂俏皮可愛同時又溫柔怡人。樂曲的結尾,通常是漸弱漸慢,和演唱者保持同樣的節拍,娓娓道來,待人聲結束,收尾,具有托腔送韻的效果。
(三)調動多種積極的教學手段
自古以來,教學有法,但無定法,因材施教,因人而宜。將魯南五大調納入揚琴藝術教學本身就是一件新的事物,要把這項教學工作做好,除了常規教學,還需要將教學活動、教學內容多元化,開拓學生視野,激發青年人的“悟性”和“靈性”。正如智者所言,人世間有兩本書,一本是有字的,一本是無字的,有些東西可教可學,有些東西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它要在人們的感知體驗中去“悟化”。在揚琴藝術的教學中,有計劃、有目的地舉辦一些活動,如:古今中外經典樂曲的賞析,各類樂器的體驗,如打擊樂器與擊弦樂器、弓弦樂器與彈撥樂器、鍵盤樂器與吹管樂器等等,還可以挑選一些古詩詞舉行讀、誦、吟、唱的比賽活動,在多元的藝術元素熏陶下,有可能點燃創作靈感的火花,啟迪年輕一代的藝術構想。
結語
綜上所述,揚琴藝術教學在魯南五大調中的傳承與創新這一課題是可行的,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創新與當代文藝人才培養相結合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教學思想的體現,這一課題的實施,必將對教育、教學、教研工作和學術研究活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對教育和培養新時代音樂藝術人才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