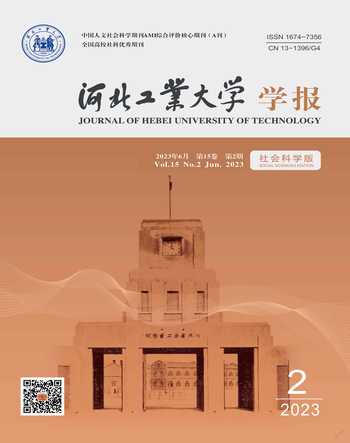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制度完善
張瑞雪 柯陽友
摘 要: 隨著我國公益訴訟進程的推進,產生了一種新的訴訟類型——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此類訴訟具有保護范圍廣泛、訴訟進程高效等程序特點,在訴訟中適用調解制度比其他類型的訴訟更加契合恢復性司法理念與實體正義的實現。通過對全國調解結案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歸納分析,可以看到調解制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沒有系統完備的法律規定,各地方法院僅處于探索模式,在適用范圍、階段、公告等具體程序方面難以形成統一的規范。因此,為了統一案件處理程序,更好地發揮調解在案件適用中的優勢,應當進一步擴大適用調解的案件范圍、允許在刑事訴訟的任一程序階段進行調解、保留對調解內容的公告程序,以實現對調解適用情況的監督和統一。
關鍵詞:公益訴訟;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調解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5.1;D925.2? ? ? ?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7356(2023)-02-0071-08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8年3月1日公布,2020年12月29日修正)第20條規定: “人民檢察院對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犯罪行為提起刑事公訴時,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由人民法院同一審判組織審理。”這一規定使檢察機關能夠作為一方訴訟主體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1],自2018年3月2日施行以來,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審理數量逐年增加,但其法律依據僅限于專門性的文件和一些原則性規定,立法處于空白狀態,并無統一標準。從理論研究中也可以窺見一斑,關于是否應當沿用民事公益訴訟的相關制度問題,高星閣博士強調要注重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本質特征,認為在證明標準、保全程序方面可以參照民事公訴的規定,但檢察機關不應當是補充性的起訴主體而應當處于主導性地位[2];湯維建教授則認為要想繼續發揮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復合訴訟的制度優勢就不應當忽視立法的空白問題,其主張通過修改《刑事訴訟法》將此類案件上升為立法的高度進而更好地發揮其制度優勢[3];而關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其他訴訟的關系,莊瑋教授認為應當破除重刑輕民的理念,堅持“先民后刑”的程序更能突顯其特殊的制度優勢[4];蔡虹教授則獨樹一幟地提出了將刑事附帶民事公私益訴訟合并審理的制度,并認為應當通過具體的法律規范加以確立[5]。
可見,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具有獨立的訴訟地位,既不同于普通民事公訴又不完全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具體類型。在民事公益訴訟中,雖然大多數學者認為基于公益訴訟的特殊性不得適用調解制度,但是司法解釋還是賦予了雙方當事人適用調解的權利,并通過30天的公告程序和人民法院的審查來加以約束[6]。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作為刑事程序中適用調解制度的先鋒者,也有許多值得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借鑒的地方,但由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這兩類訴訟既存在競合又具有明顯的差異,對于調解制度的適用并不能完全遵循某一類訴訟而模仿設置,其適用調解具有自身的正當性基礎。
一、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基礎
(一)新型案件性質的需要
關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這一新型的實踐創新到底是什么性質的訴訟,學者們大概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把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視為刑事領域的一種特殊形式,堅持此類訴訟的本質為刑事訴訟性質[7]。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是從程序的視角出發,強調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程序附屬性,卻忽略了其并非僅僅是搭刑事程序的“便車”,作為社會公益領域中的特殊訴訟形式,其訴訟結果、訴訟過程都與私益訴訟不同。第二種觀點認為,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是公益訴訟的一個子類別、新種類,其審理內容仍然沒有超出民事公益訴訟的范疇[8]。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是基于實體內容,認為這類訴訟的實質在于審理公益的內容,這類訴訟之所以稱之為新型的訴訟就在于其是在刑事程序中運作的,并且檢察機關在這一訴訟程序中具有雙重身份。我們認為,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是一種同時蘊含了程序色彩和實體意義、刑事過程與民事內容的特殊訴訟形態,它是在司法實踐中為保護公共利益和提高訴訟效率的需要應運而生的,在這一訴訟運行過程中,既要堅持刑事訴訟的平穩運行,又要注重對公益訴訟部分的特殊處理,以便更好地發揮其制度優勢,保護公共利益。
1.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同為刑事程序附帶解決民事問題的訴訟形式,其在程序運行、制度設計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最高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中明確規定了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適用調解的相關規定①,據此,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司法實踐過程中,主張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為刑事領域的特別訴訟形式的辦案人員,往往直接將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關于調解的規定完全搬到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但往往會產生“水土不服”的尷尬現象,仔細對比兩類訴訟的區別,會發現調解的適用存在以下差別之處。
一是保護范圍不同。《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可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保護范圍只限于對犯罪造成的財產損害,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所保護的法益范圍卻遠不止當下物質損失,還包括未來可能發生的預期危害,這種抽象的預期危害并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保護范圍之內。同時,它所保護的公共利益也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內涵,即針對因犯罪行為而遭受損失的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仍然是傳統的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的保護范疇,而難以確定的公共利益或者非國家、集體財產則需要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保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與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就像刑事程序中的兩駕馬車,這兩種附帶性訴訟程序的配合設置,使一切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的損害都能夠得到及時維護。由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保護范圍的特殊性,使得調解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比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中具有更加廣闊的發展土壤。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的被害人往往對被告人刑事處罰結果具有更高的期待,對于調解的積極性不高;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不存在特定的被害人,修復受損法益是案件較為關鍵的訴訟結果,因此,調解制度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比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具有更高的適用可能性。
二是起訴主體不同。私益訴訟的原告一般為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提起訴訟的人是檢察機關。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公訴人,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是否具有與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權限,其作為與案件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共利益代表人與刑事被告人所達成的調解協議是否真實、是否合理合法[9],檢察官是否有合法身份作為調解的一方當事人?這些都是對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在能否適用調解上的疑問。我們認為,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的代表人可以針對公共利益與刑事被告人達成調解協議,理由有三:一是由于其保護的法益是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受損害的結果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發現的,如果限制檢察機關對公共利益的處分權,很多案件在當下并沒有直接受損失的利害關系人,缺乏適格原告提起訴訟,受損害的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難以恢復平衡,有違恢復性司法理念;二是從實證研究來看,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一般都會適配刑事程序中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檢察機關作為唯一的起訴主體與刑事被告人達成調解協議,有利于把握調解對于認罪認罰從寬量刑的影響程度,其認定結果也更專業、權威并且節約了司法資源,使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訴訟特質得到了最大化的發揮[10];三是檢察機關作為起訴主體提起訴訟遭到反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其不是利益相關人,另外一方面是由于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是公訴人的地位,可能會使公訴機關與刑事被告人由于刑事地位的不平等而影響公益訴訟部分調解的自愿性和真實性。但其實通過調解結案是最好地避免地位上的懸殊的方式,自愿、平等是調解的天然優勢,通過平等協商的方式解決公益部分,可以緩解刑事被告人的壓力,減少地位上的落差,有利于實質公平的實現[11]。值得注意的是,檢察機關雖然應當被賦予參與調解的權利,但其畢竟不是直接的利益相關人,因此,在檢察機關參與調解的過程中,不應當賦予完全的對于調解事項的處分權。
2.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民事公益訴訟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民事公益訴訟是在不同訴訟程序中保護公共利益的兩種訴訟形式,因此,民事公益訴訟關于調解的某些特殊規定可以適用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但并不完全適用。首先,由于兩類訴訟均保護公共利益, 《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對于民事公益訴訟調解內容的公告限制程序也可以適用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②,這在2019年11月25日兩高聯合發布的《訴前公告程序問題的批復》中也得到了印證③;其次,公告期滿后,經審查不違反社會公益的,法院必須制作調解書的規定,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無須履行。原因有二:其一是民事公益訴訟是完全且典型的公益訴訟形式,案件的結果會得到普遍關注,因此,案件是如何處理的、執行的情況如何都應當予以公布,接受大家的監督;其二是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大部分案件都屬于犯罪情節較輕、社會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刑事被告人為就公益部分達成調解協議可能會做出一定的讓步,對一定的事實進行承認,而對于刑事部分的事實是屬于被告人的隱私,全部公布可能會有損被告人權益保護原則,也可能使被告人進行調解時有所顧忌而影響調解制度的適用。
(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法理基礎
作為保護公共利益應運而生的一種新型的訴訟形式,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自身便具有適用調解制度的以下三個方面的法理基礎。
1. 恢復性司法理念
恢復性司法理念是指運用一種非對抗的方式解決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沖突,通過犯罪主體主動承擔法律責任,修復受侵害的法益,彌補被害人一方的損失,使社會秩序回歸平衡狀態的一種司法理念[12]。恢復性司法理念興盛于20世紀70年代,是西方國家在人權理念不斷深化,對被害人權益保護的呼聲不斷高漲的背景下產生的,我國雖然沒有完全引入恢復性司法理念,但刑事附帶民事私益訴訟調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恢復性司法理念進行了符合我國國情和司法實際的創造性轉化,通過被告人與被害人的平等協商,使被害人的損失得以彌補,修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雖然沒有明確具體的受害人一方,但其造成的損害需要恢復的緊迫性更強,例如在生態環境案件中,如果對遭受損害的生態不及時修復則會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失衡,這是利用多少民事賠償或刑事懲罰都難以彌補的損害[13]。因此,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適用調解制度更符合恢復性司法理念的要求。在司法實踐中,我國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多以損害賠償和恢復原狀為訴求,而調解制度能夠更快地實現這一目的,減少過程中耗費的時間成本,將調解制度應用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是其作為公益訴訟的實質要求,是恢復性司法理念在新領域的運用,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和實現社會正義。
2. 實體正義理念
由恢復性司法理念的視角出發,即便是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因犯罪行為被判處了刑罰,但是,由于我國大部分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是在損害生態、保護資源、食品、藥品等領域,侵犯的法益主要是公共利益或者是不能準確劃定的大多數人的普遍利益,因此對刑事被告人判處刑事責任僅僅是國家公權力對其破壞社會秩序的一種懲罰與教育,并不能彌補因犯罪行為而對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害,刑事被告人因受到刑事處罰而失去自由的同時,生態環境或者公共利益仍舊處于受損害的狀態,公共利益未能得到救濟,社會秩序未能恢復平衡,這與恢復性司法理念是背道而馳的[14]。程序正義是指訴訟程序方面體現的正義,實體正義是指案件實體的結局處理所體現的正義,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各自有其獨立的內涵和標準。由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多為破壞環境資源保護領域或者食品、藥品安全領域犯罪,涉及的利益群體廣泛,是人民群眾關注的社會焦點,而通過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設立調解制度,在法庭的主持審理下,刑事被告人與公共利益代表人經過協商,就因犯罪行為而給社會或他人造成的損害積極承擔賠償損失、賠禮道歉或者恢復原狀等責任,有利于及時處理因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對公共利益的損害,使公共利益得到及時的維護。同時刑事被告人也會在協商過程中了解相關法律規定,受到了法制教育,主動認罪認罰,積極悔過,不僅及時彌補了因犯罪行為造成的損失,恢復社會利益的平衡,還因具有認罪態度良好、社會危險性降低等從輕量刑情節獲得從寬量刑,實現了對刑事被告人的實體正義,滿足刑事被告人及其近親屬的期待,緩和了社會矛盾[15]。
3. 糾紛一次性解決理念
糾紛一次性解決的司法理念是隨著訴訟爆炸、案多人少的司法背景應運而生的,糾紛一次性解決首先出現于新舊訴訟標的爭論中,隨后逐漸從法律含義擴展到生活內涵[16]。糾紛一次性解決理念以迅速高效地完成案件審理為價值目標,這與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訴訟目標不謀而合,如何能夠使雙方當事人都能夠認可裁判結果而服判息訴,是提高訴訟效率的關鍵[17]。因此,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善用調解制度解決案件糾紛是糾紛一次性解決理念的必然要求。通過調解使刑事被告人與檢察機關盡早達成一個合理合法的賠償數額,對受損害的公共利益進行修補,通過一次審判做到糾紛的全盤、徹底解決,既減輕訴訟當事人的壓力,減少尋求權益保護的成本,又有利于法律秩序的平穩運行,實現國家法治的統一[18]。
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調解制度適用的實證分析
為了更好地把握調解制度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的應用,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刑事一審、刑事案由、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調解為核心詞進行了搜索,同時又以同一時間段內相同的審級和案由而剔除調解這一限定詞進行了檢索,發現從2018年3月1日到2022年4月1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呈現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共8 421件,其中適用調解結案的僅有35件,調解制度的適用率僅為0.4%,可能有的法院制作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調解書沒有上網而顯示調解制度的適用率低。但仍然可以看出,各地法院對于此類訴訟是否能夠適用調解制度,如何適用調解制度的做法不一。通過檢索發現,僅有遼寧、黑龍江、上海、江蘇、安徽、福建、河南、湖北、廣西、貴州、云南等11個省份對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了調解制度④,而且以云南和福建為較多,同時各地方法院對調解制度的適用還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具體狀況及特點如下:
(一)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制度的案件類型
通過表1可見,適用調解制度的案件類型主要集中在污染環境罪和盜伐林木罪中。首先,這類犯罪一般都是對環境造成破壞,并且一般的犯罪人是因法治意識和環保意識淡薄而觸犯刑律,在對其定罪時一般都會積極賠償,認罪態度良好,因此,一般都能夠通過達成調解協議而終結案件。其次,這兩類犯罪的處罰方式都較為明晰確定,一般的責任承擔方式為恢復原狀或者賠償損失,這類責任承擔方式的可調解范圍確定,檢察機關的處分權限較為寬松、自由,適用調解也不會出現違反法律規定的情形,既符合法定程序又節約了司法資源,調解就成了檢察機關青睞的一種結案方式;而在非法收購、出售珍貴野生動物罪或者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責任承擔方式多為懲罰性賠償性質,調解內容難以確定,檢察機關在調解中也難以準確把握對調解內容的處分權限,故而使調解在這類案件中的使用率并不高。可見,由于立法規定的缺位,我國對于調解制度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領域的運用還是局限于傳統的公益訴訟領域,或者說是責任承擔方式和調解內容具體、確定,能夠清晰把握調解權限大小的案件領域,范圍并未擴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五件侵犯個人信息罪⑤也同樣適用了調解制度,這拓展了調解制度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適用領域,是一次大膽的嘗試。
(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公告程序
雖然司法解釋規定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嚴格履行訴前公告程序,但在訴訟進程中有關調解的內容是否全部需要公告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在檢索到的35個適用調解制度的案件中,履行訴前公告程序的案件僅有12件,占34%;沒有履行訴前公告程序的案件23件,占66%。在司法解釋出臺之前對于公告程序的漠視原因有多個方面,其中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是最重要的原因,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訴訟效率的追求是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其認為履行公告程序便會對刑事部分的訴訟進程造成拖延,進而導致了公告程序的低使用率。但正如司法解釋所傳達的態度一樣,不管是什么樣的原因,缺乏必要的公告程序只會使調解結果失去公眾信任度,使調解程序缺乏客觀的監督機制。
(三)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調解的達成階段
運用調解制度,是公訴機關為盡早解決民事部分的問題而采取的一種方式。而調解協議何時達成,達成調解是否需要由法院主持等問題卻在適用中存在不同情形,在檢索到的適用調解的35個案件中,15個案件在訴訟中經法院主持下達成了調解協議,占43%;20個案件在審判之前檢察機關和被告人便自行達成了調解協議,占57%。可見,調解大多在審前階段就已達成,這也與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追求訴訟效率的目標相契合。在庭審前就公益部分達成調解協議,使得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失去了對公益部分的附帶性,轉變為普通的刑事案件等待解決,大大減緩了辦案壓力和案件的復雜程度,是對司法機關的有效減負。
從上述三個方面可以看出,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調解的適用范圍相對較小,對于是否訴前公告以及調解協議達成后是否需要向社會公眾予以公告等問題的做法不一致,但值得肯定的是,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由于調解制度的適用,被告人主動賠償造成的損失并悔罪、認罪,與刑事訴訟法中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產生了良好的聯動效應,對犯罪人的量刑產生了積極效果。因此,完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適用范圍、案件類型、訴前公告等內容,是對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調解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有利于調解制度的更好利用,也是使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發揮最大司法效益和社會效果的良好助推器。
三、完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調解制度的建議
實踐中,雖然有法院適用調解制度,但各法院的理解和適用差異較大,調解制度在此類訴訟中的具體適用模式還屬于初期發展階段,適用程序和適用方式并不統一,導致同案不同判,不利于司法的統一和法治社會的建設[19]。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通過調解結案能夠更早更快地實現保護公共利益與恢復社會公共秩序的訴訟目的,有必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完善調解制度的適用:
(一)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案件范圍
從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適用調解不僅能夠盡快實現對公共利益的保護,而且對于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會具有正向的效用。但由于公訴機關并非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直接利益主體,其是否有權力對公共利益進行處分是我們值得考慮的。由于我國司法解釋已經賦予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權限,雖然通過設置三十日的公告期來限制和監督調解的內容,但這也為檢察機關對公共利益的處置權提供了法律依據,并且從統計數據和多地的辦案經驗來看,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沒有采用附帶民事訴訟的法律框架,而是以民事公益訴訟為主體,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其法律缺陷[20]。因此,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法律規定順理成章地成了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理論證成;此外,擴大調解制度適用的案件范圍也是現實所需。調解制度的適用不應局限于實踐中的環境污染、生態損害領域的公益訴訟,還應當擴大到個人信息保護領域(上海市已經審理了對個人信息保護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案例)、英烈保護等眾多領域;公益訴訟案件追求對受損利益的及時恢復,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適用調解制度,通過檢察機關代表公共利益受損害的一方與刑事被告人達成協議,通過修復原狀、損害賠償、賠禮道歉等方式恢復公共利益的原始狀態,實現糾紛的一次性解決,也就實現了公益訴訟的核心目標。
(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調解的適用階段
效率是現代司法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因此,應當嘗試在訴訟的任何階段都予以適用調解制度,在審查起訴階段達成調解協議的,在提起刑事公訴時僅需將調解協議的內容和結果連同案卷材料一起送交法院即可,并不會影響刑事案件的判決,對于公共利益的保護也是一種及時、有效的處理方式。
一方面,調解制度能夠被廣泛運用到司法實踐中就是因為其有利于及時解決糾紛,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但是,如果在訴訟過程中為了達成令雙方都滿意的調解協議可能會出現久調不判的現象,這樣不僅沒有使受到損害的公共利益得到修復,而且還會使刑事被告人受到了更長時間的羈押,對雙方都產生了不應有的損害[21]。因此,對于通過調解能夠得以解決的案件,不需要一定進入審判程序,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能夠自行與被告人進行調解的案件便可以自行簽訂調解協議并予以履行。
另一方面,在審判階段就公益訴訟部分達成調解協議,也能更好地與刑事訴訟中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相銜接。從實踐來看,凡是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會在刑事訴訟部分配合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由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其程序的附帶性,因此,在檢察機關與刑事被告人就公共利益損害事項達成調解協議時,刑事被告人往往已經受到了普法教育,意識到了自己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并愿意通過調解積極賠償、悔罪認罰,因此,這也就符合了刑事訴訟中的認罪認罰從寬的構成要件,在審查起訴階段達成調解協議也就是刑事訴訟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過程。但并不是所有的公益訴訟部分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都必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由于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需要考慮刑事被告人的悔罪態度等多重因素,因此,并不是全部達成調解的案件都能夠得到從寬處理,履行調解協議與刑事部分得到從寬處理是相伴相隨的關系,要避免出現用民事賠償換取刑事責任的情形,滋生腐敗,縱容犯罪[22]。
(三)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調解內容的公告
關于調解制度的適用是否需要公告的問題,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其一,檢察機關在起訴前是否需要公告,以確保是否有其他適格原告起訴。我們認為,雖然2019年11月25日兩高聯合發布的《訴前公告程序問題的批復》將檢察機關履行訴前公告程序進行了統一,但若對履行公告程序的時間不做準確理解,只是簡單的履行司法解釋的規定的話,由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履行訴前公告程序必然會等待公告期滿后再提起訴訟,公告期間若對刑事被告人進行羈押,會造成羈押時間過長,同時,也會影響刑事案件的審理進程,有悖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與實體權益的原則。因此,考慮到刑事程序包括了偵查、審查起訴和提起公訴等不同階段的特點,可以寬泛地來理解履行訴前公告的時間,將公告開始的時間擴大到刑事部分開庭之前各個程序階段,沒必要等到提起公訴和附帶公訴前再履行公告程序,只要保證刑事部分與民事公益部分能夠由同一審判組織在同一時間審理即可[23]。這樣既達到了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節約司法資源、提高效率的訴訟目的,又不會損害其他主體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權益。
其二,檢察機關在與刑事被告人達成內容完備的調解協議以后,調解協議的內容是否需要公告的問題。我們認為,這一階段的公告是必要的。首先,因為公益訴訟與普通的私益訴訟的區別在于保護的是公共利益,而檢察機關雖然依據法律具有對公共利益的處分權限,但由于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與案件的最終結果并不具有直接的實質性利益關系,其行使處分權具有一定的利他性,可能導致調解積極性不高,損害公共利益等情況[24]。因此,在檢察機關與刑事被告人達成調解協議后,將調解協議的內容進行公告,接受社會和人民的監督,保障調解協議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這也有利于司法公正以及對司法權威的維護;其次,對于有些調解協議的內容進行公告后可能損害刑事被告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權益的或者雖然達成了調解協議但并沒有制作調解書的,在實踐的運行過程中,賠禮道歉等非物質性責任承擔方式較為常見,并將賠禮道歉的內容在相應范圍的社會公眾平臺進行刊登或者發布,同時也可以對環境修復后的情況及修復過程在受損害的地域范圍的公共網絡媒體平臺上進行公告。故而,雖然通過賠禮道歉等非物質性責任承擔方式進行公開案件情況,沒有履行法律意義上的強制公告程序,但由于公告的本質就是為了實現社會的監督以及普法宣傳教育,眾多法院的這種做法同樣也滿足了社會大眾的監督要求。
(四)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調解對刑事量刑的影響
在刑事訴訟案件中最終的量刑和處罰是刑事被告人最為關心的問題,也是整個案件的核心問題。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也同樣如此,本著恢復性司法理念和實體正義的原則,一般于訴訟前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檢察機關也都會做出認罪認罰從寬的認定并制作量刑建議書一并移送法院;在訴訟中經法院主持達成調解協議的案件,雖不再制作量刑建議書,但法院在最后的判決論述時也會將達成調解協議、刑事被告人認罪態度良好作為從輕處罰的情節予以展現。
值得注意的是,在通過調解審結案件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的量刑情節均表述為從輕處罰,《刑法》第六十二條的內容為:刑法中的從重處罰、從輕處罰,是指在法定刑的限度內判處刑罰。由此可以看出,從輕處罰包含三層含義:其一是從輕處罰必須是在法定刑范圍內從輕,如果超出了法定刑范圍,則是“減輕”而不是“從輕”了[25];其二是從輕處罰的情節包括法定從輕和酌定從輕,而從調解制度的具體運用中來看,案件的從輕處罰表述一般為“社會危害程度較輕,未造成危害后果或后果較輕,積極采取措施減輕或減輕危害后果,積極主動地對經濟損害進行補償、偶犯、初犯、主觀惡性較小”等,很顯然,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適用調解的從輕處罰情節是以酌定從輕為依據的;其三是從輕要適度,從輕并不是都以較低的刑罰處罰,而是要結合犯罪情形以本應當判處的刑罰根據主觀惡性和對公共利益造成的損害,在法定刑內進行小幅度的從輕,并不是所有的調解都必然帶來從輕的結果。因此,經過調解后的案件的從輕處罰,既發揮了調解制度的教育、感化、矯治功能,有利于被告人的悔悟、重返社會生活,符合恢復性司法理念,也體現了調解制度的適用并沒有對刑事量刑產生過大的約束,恰恰是對刑事量刑的有益補充。
四、結語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在實踐中已經蓬勃發展多年,往往是實踐先行發展試用,理論研究在進行分析、探索。調解制度的適用便是如此,本文在理清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民事公益訴訟三類訴訟的關系的基礎上,通過實踐的分析歸納,認為調解制度不僅應當適用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而且還應當擴大適用的案件范圍,對于一些責任承擔方式較為抽象的案件也可以探索適用調解結案;調解應當鼓勵在庭審前自行達成、法院予以確認的模式,但也不否認在庭審中就公益部分達成調解協議的權利;對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公告程序應當做雙重理解,訴前公告可以不再履行,但達成調解協議后的內容則必須公告,以實現對調解的必要監督;在量刑方面,要與刑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現更好銜接,同時注意調解并不完全等同于認罪認罰的原則。關于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調解制度的具體內容的完善,可以為實踐中更好地運用調解制度解決公益訴訟案件提供參考,有利于保護公共利益和恢復社會秩序,也有利于公益訴訟理論體系和制度建構的完備。
注釋:
① 《最高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偵查、審查起訴期間,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提出賠償要求,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調解,當事人雙方已經達成協議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又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證據證明調解違反自愿、合法原則的除外。
② 《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二百八十七條規定,對公益訴訟案件,當事人可以和解,人民法院可以調解。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或者調解協議后,人民法院應當將調解或者和解協議進行公告。公告期間不得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滿后,人民法院經審查,和解或者調解協議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出具調解書;和解或者調解協議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的,不予出具調解書,繼續對案件進行審理并依法作出裁判。
③? 2019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人民檢察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應否履行訴前公告程序問題的批復》中規定:“人民檢察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應履行訴前公告程序。對于未履行訴前公告程序的,人民法院應當進行釋明,告知人民檢察院公告后再行提起訴訟。因人民檢察院履行訴前公告程序,可能影響相關刑事案件審理期限的,人民檢察院可以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訴訟。”
④? 其中云南省8件,福建省6件,上海市、安徽省各5件,江蘇省4件,其余省市均只檢索到1件。
⑤? 這五個案件均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具體參見中國裁判文書網(2021)滬0116刑初741號、 (2021)滬0116刑初743號、(2021)滬0116刑初739號、(2021)滬0116刑初742號、(2021)滬0116刑初703號。
[參考文獻]
[1]? 傅賢國. 刑事附帶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認識誤區及其克服[J]. 河北法學,2022,40(3):58-71.
[2]? 高星閣. 論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程序實現[J]. 新疆社會科學,2021(3):91-101,167.
[3]? 湯維建.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研究[J]. 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2022,37(1):28-43.
[4]? 莊瑋.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J]. 中國應用法學,2021(4): 196-211.
[5]? 蔡虹,王瑞祺. 刑事附帶民事公私益訴訟并審的程序展開[J]. 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40(1):152-162.
[6]? 柯陽友. 民事公益訴訟重要疑難問題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170-173.
[7]? 姜保忠,姜新平. 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問題研究——基于150份法院裁判文書的分析[J].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9, 34(2):79-87.
[8]? 蘇和生,沈定成.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本質厘清、功能定位與障礙消除[J]. 學術探索,2020(9):74-83.
[9]? 盧晶. 新時代刑事附帶民事檢察公益訴訟實踐面向研究[J]. 中國檢察官,2020(7):62-65.
[10]? 周新.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研究[J]. 中國刑事法雜志,2021(3):123-140.
[11]? 周儀娟. 我國網絡著作權侵權糾紛在線調解機制研究[J]. 河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1(3):35-41,48.
[12]? 扈會寶. 恢復性司法理念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及對策[N]. 法制生活報,2020-10-12(3).
[13]? 蔡曄. 恢復性司法理念在刑事附帶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的運用[J]. 環境資源法論叢,2021,13(1):255-265.
[14]? 龍婧婧. 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探索與發展[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9,34(2):88-94.
[15]? 趙貝貝. 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問題研究[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16(12):84-87.
[16]? 任重. 民事糾紛一次性解決的限度[J]. 政法論壇,2021,39(3): 94-103.
[17]? 石曉波,梅傲寒. 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檢視與完善[J]. 政法論叢,2019(6):27-36.
[18]?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孫國鳴,黃海濤,等. 關于建立民事審判“糾紛一次性解決機制”的調研報告[J]. 法律適用,2013(1):98-104.
[19]? 楊雅妮.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訴前程序研究[J]. 青海社會科學,2019(6):180-187.
[20]? 謝小劍.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創新與實踐突圍——以207份裁判文書為樣本[J]. 中國刑事法雜志,2019(5):92-111.
[21]? 毋愛斌. 檢察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諸問題[J].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53(4):29-31,24,126.
[22]? 宋高初. 論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前置問題[J]. 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9(3):19-24.
[23]? 顧順生,朱文鑫.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訴前公告程序的可操作性須增強[J]. 人民檢察,2019(23):71-72.
[24]? 田雯娟. 刑事附帶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實踐與反思[J]. 蘭州學刊,2019(9):110-125.
[25]? 方熙紅. 簡論刑法上的“從輕處罰”[J]. 人民檢察,2006(19):47-49.
The Perfect System of Applying Mediation to Criminal Incid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Zhang Ruixue, Ke Yangyou
(Law school,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rocess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a new type of litigation has emerged - criminal incid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uch litigation has proced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wide range of protection and an efficient litigation proces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diation system in litigation is more agree with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ubstantive justice than other types of litigation. Through the inductive analysis of criminal incid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concluded through national medi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ediation system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legal provisions, the local courts are only in the exploration mod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unified norm in terms of specific procedures such as scope of application, stage, and announce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ify the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cases and give better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medi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cases, the scope of cases in which mediation is applied should be further expanded, mediation should be allowed at any stage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the announcement procedure for the content of mediation should be retained, so as to achieve supervis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mediation.
Key word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riminal incid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mediation system
收稿日期:2022-06-21
基金項目: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HB20FX008)
作者簡介:張瑞雪(1998—),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訴訟法、證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