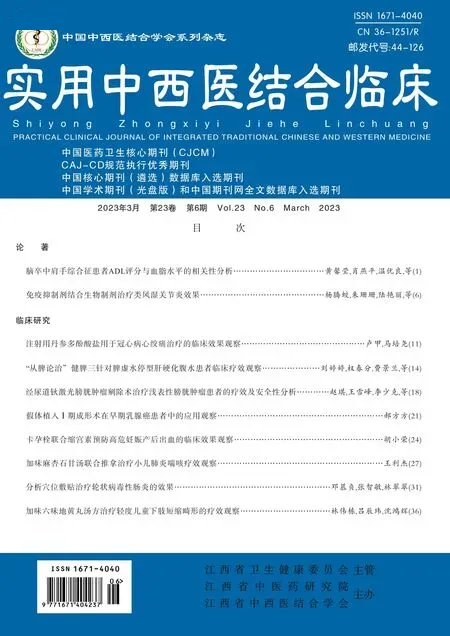普瑞巴林聯合神經阻滯在神經病理性疼痛患者中的應用效果觀察
郭玉龍
(河南省靈寶市第一人民醫院疼痛科 靈寶 472500)
神經病理性疼痛屬慢性疼痛,由軀體損傷或疾病引起,也可繼發于外周性疾病或損傷[1]。神經病理性疼痛可分為外周性和中樞性兩種,該病的診斷主要依靠病史采集、查體及電生理檢查。神經病理性疼痛的原因包括代謝性、營養性、病毒、神經毒性、神經遞質功能障礙等,主要臨床表現為自發性疼痛、痛覺過敏、感覺異常等,疼痛程度較為劇烈,加之該病難以治愈、病程長、易反復發作,患者極易出現失眠、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降低其生活質量[2~3]。現階段,神經病理性疼痛的治療常采用抗抑郁、抗癲癇及阿片類鎮痛藥,普瑞巴林作為近年在美國和歐洲大量應用于治療中樞、外周神經病理性疼痛的一線藥物,屬新型γ-氨基丁酸(GABA)受體阻滯劑,可減少去甲腎上腺素、P 物質、谷氨酸鹽等興奮性遞質的釋放,抑制神經元異常,緩解疼痛癥狀[4]。神經阻滯是一種在神經元干上使用相應藥物,暫時阻斷、干擾神經放電和傳導的治療方法,可阻斷神經疼痛的傳導,達到止痛目的[5]。本研究分析普瑞巴林聯合神經阻滯治療神經病理性疼痛的應用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按隨機數字表法將2020 年7 月至2022 年7 月醫院收治的80 例神經病理性疼痛患者分為對照組和研究組,各40 例。對照組年齡31~65歲,平均(46.84±9.61)歲;男16 例,女24 例;病程3~9 個月,平均(5.32±1.94)個月;周圍神經病理性疼痛21 例,中樞神經病例性疼痛19 例。研究組年齡32~68 歲,平均(47.21±8.59)歲;男18 例,女22 例;病程2~9 個月,平均(5.36±1.98)個月;周圍神經病理性疼痛23 例,中樞神經病理性疼痛17 例。兩組一般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
1.2 入組標準 納入標準:符合《神經病理性疼痛診療專家共識》[6]中相關診斷標準;患者依從性較好,且簽署知情同意書;臨床病歷齊全。排除標準:合并惡性腫瘤;伴有其他神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合并嚴重肝腎功能異常、凝血功能異常、感染性疾病、內科基礎疾病;無法配合完成本研究;對本研究藥物存在特異質反應。
1.3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常規予以神經營養藥物治療。口服維生素B1 片(國藥準字H14021291),10 mg/次,3 次/d;甲鈷胺片(國藥準字H20052325)口服,0.5 mg/次,3 次/d。對照組在常規治療基礎上口服普瑞巴林膠囊(國藥準字H20223712)治療,75 mg/次,2 次/d。研究在對照組基礎上聯合神經根阻滯治療,據患者疼部位在B 超掃描下確定受累神經根具體位置并實施穿刺,之后在神經根周圍注射10 mg 醋酸曲安奈德注射液(國藥準字H20033524)+10 ml 鹽酸利多卡因注射液(國藥準字H43021930),1次/周。兩組均持續治療4 周。
1.4 觀察指標 (1)臨床療效。治療后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下降>3 分,睡眠正常為顯效;治療后VAS 評分下降1~3 分,睡眠基本正常為有效;治療后VAS 評分下降<1 分,睡眠情況與治療前相同為無效。總有效=顯效+有效。(2)疼痛程度。治療前后采用VAS 進行評估,0 分為無疼痛,10 分為極度疼痛,分數越高疼痛程度越嚴重。(3)睡眠質量。治療前后采用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SQI)評估睡眠質量,包含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障礙等7 個部分,每個部分按0~3 分4 級計分,總分為21 分,分數與睡眠質量成反比。(4)焦慮情緒。治療前后采用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評估焦慮情緒,包含緊張、害怕、認識功能等14 個項目,所有項目采用0~4分5 級評分法,評分>7 分認為病人存在焦慮癥狀,分數與焦慮程度成正比。(5)抑郁情緒.治療前后采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評估抑郁情緒,該量表包含17 項,共68 分,分數與抑郁程度成正比。(6)致炎因子。治療前后采集患者空腹靜脈血3 ml,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白細胞介素-18(IL-18)、核轉錄因子-κB(NF-κB)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7)不良反應。記錄患者出現嘔吐、頭暈、嗜睡等不良反應情況。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2.0 統計學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療效對比 研究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對比[例(%)]
2.2 兩組VAS 評分、PSQI 評分對比 治療后研究組VAS 評分、PSQI 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VAS 評分、PSQI 評分對比(分,±s)

表2 兩組VAS 評分、PSQI 評分對比(分,±s)
?
2.3 兩組HAMA、HAMD 評分對比 治療后研究組HAMA 評分、HAMD 評分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3。
表3 兩組HAMA、HAMD 評分對比(分,±s)

表3 兩組HAMA、HAMD 評分對比(分,±s)
?
2.4 兩組致炎因子水平對比 治療后研究組TNF-α、IL-6、IL-18、NF-κB 水平低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兩組致炎因子水平對比(±s)

表4 兩組致炎因子水平對比(±s)
?
2.5 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對比 兩組不良反應總發生率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對比[例(%)]
3 討論
神經病理性疼痛是神經科常見癥狀之一,發病率約為1%,由于病因多種多樣、發病機制復雜,屬難治性疾病,可分為原發性和繼發性兩類[7]。神經病理性疼痛發病機制與中樞神經損傷或疾病誘發的中樞敏化、神經興奮性增高導致的神經遞質過度釋放有關,常見病因包括神經損傷、感染、代謝紊亂、梗死等,患者主要表現為鈍痛、灼痛、搏動性疼痛,該病顯著特點為損傷治愈后疼痛仍然存在,可持續數周、數月,甚至數年,易造成患者出現一定的焦慮及抑郁情緒,負面心理狀態可加劇患者疼痛感,造成惡性循環[8~9]。相關研究表明,焦慮及抑郁程度與主觀疼痛程度成正相關,嚴重影響患者身心健康[10]。目前,臨床并無明確治療神經病理性疼痛的方法,其治療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病情可能出現反復,需要長期治療,一般多采用阿片類藥物、抗抑郁藥物等,但上述藥物不良反應較多,且阿片類藥物成癮性較大[11]。
神經病理性疼痛外周機制包括細胞膜興奮性增高和周圍神經的高致敏性。相關研究表明,突觸前神經末梢有大量的離子通道,包括鈣離子通道、鈉離子通道、鉀離子通道等,其中鈣離子通道在神經遞質釋放的過程中尤為重要,參與神經遞質釋放的每個步驟[12]。歐洲神經學會聯盟、國際疼痛協會(IASP)等均推薦普瑞巴林為治療神經病理性疼痛的一線藥物,在英國卓越臨床研究院指南中,普瑞巴林是唯一被推薦用于治療中樞神經和外周性神經性病理性疼痛的藥物。普瑞巴林是一種新型鈣離子通道調節劑,具有親脂性,能夠通過血腦屏障,抑制神經系統電壓依賴性鈣離子通道的亞基α2-δ 蛋白,減少谷氨酸、去甲腎上腺素和P 物質釋放,抑制交感神經及腎上腺興奮,同時抑制興奮信號在中樞的傳導,緩解疼痛,一定程度上減輕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此外,普瑞巴林可直接作用于前觸前2-δ 亞單位,抑制神經元興奮性,并不對正常神經功能產生影響,僅抑制疼痛信號產生;另外,該藥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服用1 h 后就可達到血藥濃度峰值,生物利用度≥90%,且不與血漿蛋白結合,藥物的吸收受食物影響較小,98%的普瑞巴林可經腎臟排出體外,具較高的安全性[13~14]。
有研究表明,神經病理性疼痛的發生和發展與致炎因子的表達關系密切[15]。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治療后VAS 評分、PSQI 評分、HAMA 評分、HAMD 評分和致炎因子水平均低于對照組(P<0.05),且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神經病理性疼痛患者應用普瑞巴林聯合神經阻滯治療可緩解患者疼痛癥狀和負性情緒,提升睡眠質量,用藥安全。部分患者原發性疼痛的病因可能已去除,但惡性循環仍殘留,導致周圍或中樞神經系統的敏感化局部疼痛經感覺神經傳入脊髓,通過脊髓的反射,引起交感興奮,使血管收縮,缺氧,代謝異常,局部的病損不易修復,同時產生致痛物質,使疼痛加重,形成惡性循環。近年來,B 超技術開始應用于神經組織的定位與引導,其可為神經阻滯的穿刺和給藥提供實時影像,直視穿刺針的路徑,避免了傳統盲探法穿刺造成的神經和血管損傷;此外,B 超引導下進行神經阻滯治療,可直觀分辨出神經和周圍組織,將藥物準確注入病灶部位,起效快,可觸及傳入感受器產生異位電活動,降低周圍或中樞神經系統的敏感化,松弛肌肉,改善血液循環,使局部血流增加,減輕神經水腫,營養神經,有效地阻斷疼痛的惡性循環[16]。慢性疼痛會引起患者心理障礙,情緒不穩,煩躁,苦悶,加重患者局部疼痛,神經阻滯治療可使患者疼痛立即消除或明顯減輕,使其心情愉快,從而增加治病的信心和康復速度。但神經阻滯的藥物選擇必須要考慮不良反應、聯合用藥的利弊、藥物的作用機制與治療目的,做好充分的病情評估,把握神經阻滯的適應證,熟悉阻滯部位的解剖結構、阻滯用藥的作用機制,規范穿刺及操作技術,準確地進行神經阻滯效果評價,了解其可能發生的并發癥及預防措施。
綜上所述,普瑞巴林聯合神經阻滯治療神經病理性疼痛效果顯著,有助于緩解疼痛,改善患者抑郁、焦慮情緒和睡眠質量,且不良反應較少,臨床應用安全有效,值得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