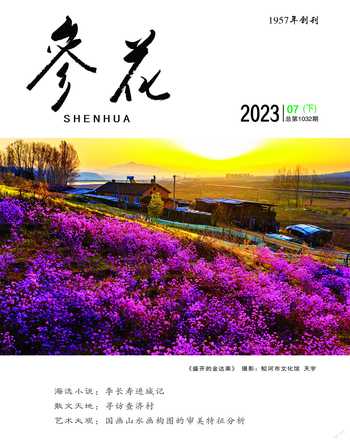探析徐渭書畫中表現主義之淵藪
徐渭是明朝書法、繪畫、劍術、詩歌、戲曲、文章皆通的一代奇才,他于書法中宣泄情感之所向,花鳥間吐露內心之所感,他所開創的大寫意畫派對后世花鳥畫的發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創作的雜劇、戲曲也別出新意,不落俗套。筆者將對徐渭在書畫中所透露出的表現主義進行客觀研究,望能從中窺探文長先生的美學思想。
一、師承關系
徐渭出生于浙江紹興,受當地名家楊珂、陳鶴的感染,擅長楷體和草體,草體學書于懷素,楷體屬晉人一脈。楊珂長于草書,且喜作“狂書”,屬恣心所欲一路,徐渭深受其教化。亦曾言小楷學于鐘、王,以徐渭留給我們的風格印象來看,師法鐘、王一脈似乎讓人有些不解,但是仔細想來,無論是徐渭欣賞的“宋四家”,還是甚為稱贊的倪瓚都是無法跨越鐘、王兩道門檻的,鐘、王對徐渭影響之大是無法估量的。徐渭欣賞蘇、黃、米、蔡,他的行、草書學黃庭堅、米芾面目較多,常采用米芾八面出鋒的方法,與此同時又摻以黃庭堅的筆意,盤旋環繞,欹正互參,粗細變化自如,盡顯妍態。無論是章法還是結體,都可以看出受米、黃二人影響較大。但仔細對比,徐渭的書法相比米芾,更為剛毅蒼勁,較之黃庭堅,更顯縱情瀟灑。大草受懷素、張長史、祝枝山影響頗深。[1]
二、書法中的表現主義——以《杜甫懷西郭茅舍詩軸》為例
《杜甫懷西郭茅舍詩軸》初看點畫縱橫狼藉,章法疏疏密密,再觀水墨濃淡摻雜,流暢自然,變化豐富,整篇氣勢磅礴,猶如黃河之水傾瀉而下,奔騰入海。[2]例如第一句中的“淡”字被夸張拉長,第二句中的“高”字被省略,瞬間落筆的點畫是書者情緒迸發的表現,情到深處,全然忘記語句是否通順,字形結構是否合理。第三行中間部分“不勞鐘鼓”的“鐘”字右面部分與第二行“階面青苔”的“階”字左面部分拉扯十分膠著,而“鐘”字本身左右兩部分卻離得極遠,從“鐘”開始一直到“浣”,六個左右結構的字連在一起,這樣一個組合與前后兩行的間隔又離得很近,這也體現出徐渭對于空間張合的掌控能力。該詩軸絕非二王一路的中和淡雅,亦不是張旭、懷素的狂放自由,其中字結構被破壞,有的長拉,有的勾連,字的可識性降低,局部的精致被弱化,作品旨在創造一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這是一種無聲勝有聲地宣泄。其書法用筆之狂逸,風格之奇肆,是同時代的書者絕無僅有的。出鋒或澀筆的加入,更增添了用筆的豐富性,使得作品的層次感更強烈,視覺效果更加震撼。徐渭能做到點畫狼藉而又散而不亂,足以反映出他對駕馭整篇作品的技術之精湛。
徐渭欣賞祝枝山和王維的作品和人品,追求“自然”“游戲人生”的態度,認為強加修飾的作品往往有矯揉造作之嫌,信手拈來,率意而為方是佳品。書法在古代還是作為教化世人的一種實用性需要而存在的,但到了徐渭這里,實用性大大降低,無法再用行或列來欣賞它,前人也有突破行列之間規則的嘗試,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像徐渭這般徹底的打破,以至于我們對于其作品的識讀變得很難。所以欣賞徐渭的作品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個部位,應該就其所給出的空間看整體感覺,把他的作品當成一幅圖來進行欣賞。例如多個點畫并列的情況,可識讀性會變得困難,我們可以把它們當作是用傳統筆法所書寫出來的一種抽象性的圖案,那這便是超越藝術之外的藝術。徐渭在《杜甫懷西郭茅舍詩軸》為我們所創設的情境中,一點一線都無法置換,一氣呵成的狀態下完成的點、線、面、空間布局,所有的一切都是剛剛好,是凌駕于技法之上的直指神采氣韻的一幅作品。徐渭在經過傳統積累、技法磨煉和人生百態的錘煉下,能夠將用筆的方圓虛實、抑揚頓挫很好地表達出來,夸張筆根與筆尖的使用,利用提按頓挫,呈現出菱形或者三角形的銳利線形,與之互補的是作品中常常加入篆籀之氣的渾厚筆畫,形成鮮明對比。基于對傳統和技法的掌握,所以徐渭在書寫創作的時候才會更加隨心所欲地將筆鋒使轉、跳宕,從而表現出濃淡、干濕、長短、欹正、疾徐的效果。
三、繪畫中的表現主義——以《墨葡萄》為例
“以神寫意”擺脫了局限于物象的創作觀念,而追求利用筆墨宣泄情感的方式。徐渭的大寫意畫法與以往的追求形神兼備的畫法相抵牾,將“神韻”提到了絕對高度,注重突出事物內在特質,不再一味追尋惟妙惟肖地重現事物本身,而是更加注重主觀情感的表達。徐渭本身極強的個性,加之能靈活運用潑墨、破墨等表現手法,以書入畫的創作理念也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生機和視點。筆下之畫縱橫奔放,不求形似,但又意蘊橫生。《墨葡萄》作為徐渭大寫意風格的代表性畫作,其藤條橫掃三分之二的畫面,低垂錯落,斜伸而下,枝干、樹葉、葡萄都是寥寥幾筆,潑墨暈染,真正應了那逸筆草草之意,墨色變化豐富,層次分明,營造出風中飄飄然的枝條動感給人以空靈之美。畫中留有大量空白,中間大面積留白呈斜勢的倒三角形,右下角小面積留白,右上角留白與題畫詩相對應,這種布白結構會使畫面更加富有靈氣,整體和局部配合得相得益彰,既區分明顯,又暗生情愫,使得畫面整體感很強。這種奇妙的構圖,用“密不透風”來形容很是恰當,右側葉子和葡萄緊密集中可以例證這一點,而這種構圖用“疏可走馬”來比喻也不為過,左側的葉子疏朗靈動,中間留大面積空白,這種大開大合的張力控制是十分考驗功力的。徐渭的用筆看似似斷似續,其實內部之間互相咬合。用墨方面乍看隨意涂抹,實則每團墨色之間循序漸進,妙趣縈繞。雖不是形似,但徐渭著重借水墨葡萄抒發自己的內在感受,又將大寫意畫的表現力提到了一個更高層次的格局。徐渭的寫意畫,兼收各家之長,大膽創新,以書入畫,不落前人窠臼,代之以水墨縱情暈染,相互滲透。古代繪畫,常常是詩書畫印應有盡有。徐渭常常用畫筆直接即興題跋,《墨葡萄》中的題畫詩:“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字里行間狂放不羈,欹斜跌宕,磊落不平之氣悄然于紙上,前兩句交代創作時間是晚年,末兩句我們可以感受到他滿腹才華,卻無人賞識的幽怨與無奈之情。[3]
像徐渭這樣的文人畫家,文學功底深厚,而題畫詩也是畫畫的一種延伸,可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和思想高度,文學性的象征和書畫的結合將一個物象的世界與畫家的精神世界融為一體。徐渭曾在《答許口北》中指出:“試取所選之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群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由此看來,徐渭所追求的正是一種隨心肆意,使人醍醐灌頂的藝術理想。寫意畫可以讓作者的情緒一吐為快,故直到今日,我們還依舊可以感受到徐渭當時的情緒起伏狀態。[4]
四、徐渭書畫中的表現主義對后世的影響
徐渭是中國藝術史上的一代奇才,他的美學思想可以說十分具有前瞻性。不必說對朱耷、石濤、鄭板橋等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一直到現在人們都受益匪淺。徐渭強調:“心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一味地去模仿古人,只會“隨人作計終后人”,要帶有想法地去臨摹,去思考,不局限于一家的風格,寬泛地去探索各家背后的藝術淵源,最終達到能對多種線條、風格融會貫通的目的。繪畫重“神”,不求形似不是說可以隨意涂抹,只是基于對事物外象的了解,人們就會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它的“神韻”,這時候是不受外物所牽絆的。應學習傳統,化融古法,但又不囿于前人,應以古法助我,隨學隨化。
徐渭跌宕起伏的一生給人們留下了許多精彩的作品,書法線條或溫潤流暢,或蒼勁粗獷,或古拙老辣,或率意放達。線條是徐渭書法藝術的生命,在徐渭的筆下,線條被賦予了感情,擁有了多種表現方式。如《秋興》詩八首,初始風格溫潤儒雅,隨著書寫節奏加快,情緒越來越激昂,書至高潮處,跳宕感呼之欲出。再如大幅作品《七言律詩》,我們可以深刻地被其所體現出的茂密古樸、大氣恢宏的書法風格所震撼,作品乍看狼藉一片,然仔細觀摩,愈見其精到之處,全篇氣勢磅礴,有攝人心魄的效果。這樣的風格面目一掃書壇時習,對晚明書風熏沐良久。徐渭從不因襲固守,運筆方式也與前人相異,結字章法追求險中求勝,局部動蕩不影響整體平衡,真正達到了書者精微布置而又了無布置之痕。徐渭對字的結構進行變形改造這一創舉對后來的傅山、鄭板橋有極大的影響。徐渭行草書摻以章草筆意,與他學習索靖是分不開的,這種獨辟蹊徑的方法,為鄭板橋、黃道周等人指明了前路。徐渭開創的“大寫意”畫派,為文人畫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康莊大道,明末清初的朱耷更是將它推向了登峰造極的藝術境界。
繪畫作品《雜花圖卷》,畫中有荷花、牡丹、石榴等十三種花卉,十余米長,氣勢奔放、酣暢淋漓、一揮而就。這種體制經朱耷、石濤、鄭板橋、李鱓、李方膺等人的豐富和發展,演變成了近代大寫意畫派。又如《榴實圖》,本是畫史上不被人提及的山石榴,經過徐渭畫筆的勾勒、渲染,便向世人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也仿佛其自身命運的真實寫照。
如果說對于傳統或古法的研究是基于理性下的徐渭,那么滿紙揮灑,天馬行空就是基于非理性之下的徐渭了,但總的來說徐渭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結合體更為全面客觀。他的狂并不是狂妄放縱之狂,更多的是身處亂世浮沉中不知何以為家的自我麻痹,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傲姿態,抑或是入世不達的憤懣,塵世難托的遺憾。徐渭的藝術作品帶給我們的審美感受不再是傳統的賞心悅目,而是一種讓人難以抗拒地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一種力量,能直擊人的心靈從而引發思考,這是徐渭創造的一種新的審美趣味,具有推進和啟蒙的意義。給明代以降、清代、近現代的藝術大家們如朱耷、湯顯祖、石濤、鄭板橋、齊白石等人的美學思想注入了營養和活力。在他故去后的二十年,袁宏道四處搜集徐渭的作品文稿,對其進行研究并且宣揚其藝術主張,后來著成了《徐文長傳》,一直流傳至今。書中袁宏道評價道:“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也。”這句話很中肯地評價了徐渭的藝術成就和豁達豪邁的性格。
徐渭的“本色”觀貫穿于他藝術生涯的始終,不斷影響著后來者,對當代的書法藝術理論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西廂序》云:“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猶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書評中婢作夫人終覺羞澀之謂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帶,反掩其素之謂也。故余于此本中賤相色,貴本色,眾人嘖嘖者,我呴呴也。豈惟劇者,凡作者莫不如此。”這里所說的“本色”與“相色”,“正身”與“替身”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徐渭以“相色”和“替身”作婢,形容他們如婢作夫人般濃妝艷抹,矯揉造作。徐渭驅散了“文必秦漢”的偽復古陰霾,開啟了明代藝術新風尚。[5]正如袁宏道所說:“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藝術是順情而至,有感而發,我們要善于把握住瞬時的情感,利用筆墨將真情流露于紙上,這樣就會進入徐渭所言:“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東風吹著便成春”的境界了。在今后的創作當中,人們也應當扎實自己的學識修養,豐富作品的思想性,找到屬于自己的自在境地。
五、結語
總而言之,徐渭尚個性、重情感的美學思想對中國藝術史以及近現代的歷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表現主義書風在晚明愈演愈烈,使得書法漸漸脫離了實用性的目的,進而成為書家表達個人情感的手段,正所謂藝術來源于生活,藝術美化生活。正是因為這些人對傳統的繼承與反叛,才開辟了新的書風。徐渭深知將創新建立在傳統之上才是有源之泉,抒發真我才能獨出新意,藝術之路才會更長,這也為后世帶來了振聾發聵的啟迪。
參考文獻:
[1]王鏞.中國書法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徐渭.徐渭畫集[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
[3]敬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二卷)[M].濟南:齊魯書社,1989.
[4]秦炳娟.徐渭書法風格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5.
(作者簡介:徐麗麗,女,吉林藝術學院美術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書法美學)
(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