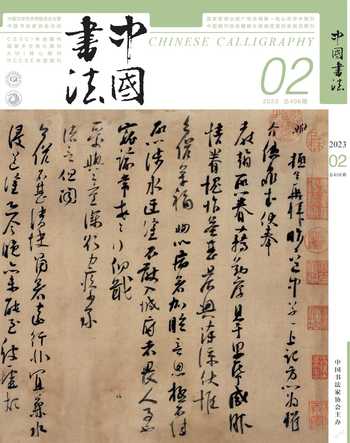傳統學問 現代眼光
王東民



摘 要:李健的書學以傳統金石學為基礎,延續了李瑞清據實物材料立論、以視覺特征為關注點的立場,且追蹤文字、考古的學術前沿,及時化用于書學研究中。在此基礎上,李健建構了『方筆圓筆』『三紀』『宗匠論』等開創性的書法史學理論,對傳統書學有進一步的拓寬與深化。
關鍵詞:金石學 方筆圓筆論 宗匠論
近些年來,李健研究者多從其著述體例的超前性等入手,對于李健書學的基礎、成因及理論的開創性還缺少相對詳細的分析。李健成長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及新的學術范式確立的時代背景下,其書學兼具傳統學問與現代學術眼光的雙重特征,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
李健書學與金石學傳統
李健以書法創作、研究與教育立足,離不開一門重要的傳統學問—金石學。李健成長于金石學氛圍濃厚的清末民初,家學亦重金石碑帖鑒藏,培養了李健對金石拓本濃厚的品賞興趣與卓越的評鑒能力。
李健在金石拓本的賞鑒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在《中國書法史·序例》中,李健云:『本篇固已搜羅孤本佳拓,煊赫海內,且于著錄有數之本列之。』[1]可見其寓目的金石拓本品質之高、數量之大。在長期的鑒藏生涯中,李健也收藏了不少珍貴的拓本。據其自言,所藏宋拓本有《唐云麾將軍李秀碑》《唐虞恭公碑》《唐李元靖先生碑》等數種,后兩種還曾在民國時期影印發行。此外,還有《玉枕蘭亭》等等。不僅如此,李健還能夠使用當時已出版的大量珂羅版字帖,以擴大目鑒的范圍。
李健的書學著述與傳統金石學著述有著極高的相似度。以《中國書法史》為例,從名稱和體例上看,這部書確實頗具現代面目。然而,其中的《甲骨紀》《金文紀》《石刻紀》,除了前后的小序和總結性的論說之外,主干內容由一篇篇獨立的作品與題跋性的文字構成,這與傳統題跋類金石著作的形式極為相近,不過其文字在前,拓本列于后。文字部分的內容比較靈活,并不固定,有繁有略,一般有題名、時間。有的篇目會涉及文字或史實的考釋,或關于某些問題的爭論,或涉及書法的品評。大量的篇目并不涉及書法的討論,簡略者僅存其題名及拓本圖像。從征引文獻來看,在《石刻紀》的較長篇幅中,李健引證文獻基本上是宋元明清時代的金石學著作,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趙函《石墨雋華》、王昶《金石萃編》等。
對于李健的主要書學著述,如《中國書法史》,既應該看到其形態、體例之『新』,也不應忽略其與傳統學問之間的承續關系。金石學是李健學問的根柢所在,其書學著述也可視為金石學傳統在二十世紀結出的一顆果實。
現代眼光:視覺本位與學術前沿
據學者的觀察,『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國學界,新的學術范式已經確立,基本學科及重要命題已經勘定』。[2]
李健主要的書學論著,恰在這之后產生。李健在書學研究中立足于古代實物材料銘文視覺的本位,及時追蹤文字學、考古學的前沿成果,顯示出學術范式變革下一位書學家的現代眼光。
立足視覺材料本位雖然金石學有悠久的傳統,金石學家也始終面對實物材料拓本,然多關注其所錄之文,用以補經證史;或著力于拓本的版本對校,以區分優劣。至于聚焦拓本所承載的視覺特征,以之為本來分析書法用筆、結字、布白特征的源流變遷的歷史并不長。清代翁方綱、阮元開其端,李瑞清是較早的全面實踐者。李健承其衣缽,嘗試完全立足視覺材料的本位來建構書法史。其立足視覺材料本位的態度,呈現出如下三點:
其一,材料真偽的鑒別。李瑞清最早將甲骨文、金文納入中國書法史敘述的框架中,既不采納那些流傳已久的如『倉頡造字』等傳記傳說,又摒除了一些疑為偽作的材料,如岣嶁禹碑、紅崖古刻等。繼承了其叔父的學術眼光,李健的書法史敘述確切地自殷商甲骨文開始,而非從『倉頡造字』等傳統傳記的說法開始。李健認為,『禹碑偽作耳,紅崖又不足信,惟近出土之甲骨文實為殷墟契文,灼然可見殷人書法。』[3]對于不明來源,從視覺特征看又難以置信的書跡,李健則不予采用,例如《淳化閣帖》收錄的倉頡、夏禹書。[4]
其二,原本與摹本的區分。原本與摹本既關涉不同的作者,也往往隸屬于不同的時代,輾轉傳摹的書跡無法準確傳達原物時代風格的信息。李健指出,『幸傳古文者,不過寫法,猶千百而存十一耳。而傳摹輾轉,雕版反覆,如《說文解字》中所引古籀文,訛舛滋多,安所得睹書契之筆法哉!大幸殷書契文字,出于河南安陽小屯。』[5]其三,版本的考究。即便拓本皆出于原物,由于金石銘文存在銹壞及剝蝕的問題,拓制的時間、精粗不同,原作風格的呈現也會有很大的差異。哪些拓本能夠更加貼近書跡原作的風采,須作審慎的判斷。對于較早出土的石刻,如在宋代之前就已出土,以宋拓為貴;宋代以后出土的,一般重其出土時的初拓本。李瑞清對拓本版本的選擇就極為嚴苛,他說:『帖非宋拓初本,無從得其筆法,故不如碑之易得也。』[6]對于拓本不存、僅存摹本的金石銘文,李健則僅存其目。如『望』銘文,因無打本(即拓本),僅有摹本,『不能見筆法,故闕之。』[7]另外,拓本的圖像完整度、品相直接關涉風格的研究。只有字畫明晰者,才能見其書之筆法;漫漶者,則棄其圖像。因拓本漫漶僅列其目而不取其作品圖像,在李健的《中國書法史》中是一個通例,如漢代摩崖《楊淮表記》,北周《延壽公碑》,唐《姜行本碑》等。
追蹤學術前沿二十世紀上半葉,大量的金石、考古要籍出版,提供了更多商周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書法資源。然而,及時追蹤這些學術前沿,將之運用到早期書法史研究的學者并不多見,李健是較早的實踐者。李健的書學研究不僅受益于金石學傳統中的拓本鑒賞,又能夠及時追蹤學術前沿,對新近產生的學術專著進行消化運用。如甲骨文書法的研究,李健不僅承續李瑞清觀點,將中國書法史的研究溯源至殷墟甲骨文,且對甲骨文的收藏、學術史了然于胸。從劉鐵云《鐵云藏龜》至商承祚《殷墟文字類編》、陳邦懷《殷墟書契考釋小箋》、容庚《甲骨文字之發現與研究》、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等十數人的甲骨文整理與研究著作,李健都下了較多的功夫。他稱贊諸人著述:『莫不據以證經文、訂史誤,而斟正《說文》,古文復明于世,厥功偉矣!而海內承學之士,得以窺見殷代古文書契焉。』然而,李健大量閱讀這些甲骨文整理與研究著作,其目標是指向書學研究的:『余綜覽諸家所纂,擇其尤與書法有關者,著之于篇。』[8]李健《中國書法史》中的《甲骨紀》就超越了個人目鑒的有限拓本材料范圍,而以當時各家已經編纂的數十種甲骨文著作為基礎。從材料的占有上來看,無疑更為全面系統,在很多問題的論述上廣征博引,與上述學者進行對話。
又如金文書法的研究。李瑞清根據他收藏或經眼的各種拓本或宋代以來的金石學書籍,對商周金文劃分流派,李健在金文書法研究中則主要參閱二十世紀以后的金文著述。雖然金文著錄從北宋就已開始,然李健極少引證二十世紀之前的。其原因,一方面,這些金文著錄所用材料大部分為摹本而非原拓;另一方面,二十世紀以后的金文考證取得的成果已足資參考。李健指出,宋代以來的很多金文研究著述皆系鉤摹,『于筆法失之八九』,清代吳大澂等人的金文著述『以打本影印出之,而后金文書法乃可規見其筆道。』繼而,他對所著《中國書法史》中的《金文紀》的研究資料選擇作出說明,他之所以選擇鄒安的《周金文存》和郭沫若《周金文大系》兩種金文著作為金文書法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緣由在于:『一則選拓精,一則統系碻,可謂金文之偉著,而為篆書之津逮。本篇金文紀則取資于二書者為多,取其為拓本影印,存筆法之真也。』[9]李健的書學研究基礎相對于其叔父李瑞清有了本質的變化。李瑞清書學論述多是以題跋的方式存在,其產生一般基于本人或友人的金石拓本收藏,雖數量不少,然所見資料存在不少的偶然性。李健從事《中國書法史》研究著述的時候,甲骨、金文等出土材料的整理與研究,比李瑞清在世時又有了極大的推進。李健的書法史研究以出土文物的最新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選取了其中最為精湛、前沿的集大成式的成果,顯示出其現代性的學術眼光。
開創性的書學理論
李健對實物材料視覺特征敏銳的洞察力,離不開傳統金石學的涵養,也直接受到其叔父李瑞清的影響。
李瑞清對李健更重要的影響則體現在觀察實物材料的史學態度。李瑞清治學崇尚今文經學,意不在精細的訓詁考證,而強調上下貫通的闡釋,注重以歷史變易的眼光來觀察和闡釋研究對象,由此而提出了重要的書學理論。其最著者為『求篆于金,求分于石』。李健則建構了『方筆圓筆』『三紀』『宗匠論』等開創性的書學理論,是在李瑞清基礎上的延續與深化。
求篆于金,求分于石李瑞清《玉梅花盦書斷》云:『余嘗曰求分于石,求篆于金,蓋石中不能盡篆之妙。篆書惟鼎彝中門徑至廣,漢以來至今無人求之,留此以為吾輩新辟之國, 余為冒險家, 探得大洲, 貢之學者耳。』[10]李瑞清『求篆于金』的理論創建至少基于三個清晰的認知。
其一,對中國歷代書法資源的通盤考量及兩周金文書法特征的認知。在金石考古研究發展的基礎上,李瑞清對中國歷史上各時代可資取法的書法資源有了一個整體的認知和通盤的考察。篆書產生及使用的年代久遠,早期石刻篆書或真偽存疑,或篇幅簡短,或風化剝蝕而難以見其筆法,故而『石中不能盡篆之妙』。對于大篆的取法來說,兩周青銅器銘文能夠提供廣闊的門徑。李健在《中國書法史》中記李瑞清言:『三代鼎彝,筆法咸備,兩漢以還,承其統緒,以展各派,其源莫不出于周金也。章耶,草耶,分耶,隸耶,體制則變,而筆法悉詔于周篆。故言金文筆法,政如言學派者之于周秦諸子,百家九流矣。』[11]其二,對歷代篆書家取法情況的認知。秦漢以降,清代之前,在篆書上取得成就者,除了唐代李陽冰外,寥寥無幾。清代篆書家如王澍、鄧石如、楊沂孫等,或學李陽冰,或學漢碑額,皆限于石刻,能夠提供豐富取法資源的兩周金文,則問津者絕少。
其三,對自身所處時代及面臨機遇的認知。基于對歷代書法取法資源、篆書學者取法現狀的清晰認知,李瑞清認識到自己面臨的機遇,正是對兩周金文大篆的探索實踐,這一被他視為門徑至廣的篆書取法資源,以往的篆書學者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其機遇也并不僅僅在于對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取法,且以之為中國書法的源頭,對其與后來書體、風格的貫通性闡釋有重要的意義。
[篆隸宗]與[方筆圓筆]論
承續『求篆于金,求分于石』,『篆隸宗』論也是李瑞清書學的一個重要理論發明。李瑞清《陶齋尚書藏瘞鶴銘跋》中云:『瑞清生平論書分三大派:《鶴銘》為篆宗,《爨寶子》為隸宗,《鄭文公》為篆隸合宗。』[12]所謂『篆宗』,即以篆書為宗,『隸宗』即以隸書為宗,『篆隸合宗』則是融裁篆、隸兩者。李瑞清的『篆隸宗』論以宏闊的視野打通篆書與北碑的內在關聯,其北碑實踐正是由大篆的導入而獲得一種創造性轉化的臨摹方式,生發新的風格面貌。
李健則將『篆隸宗』論進行了化用,擴展至『二王』傳統的觀察,建構了新的書法史解釋框架。李健曾多次以『篆隸宗』論解釋『二王』,如《書通》中言:『王氏父子草書不同派,右軍草書作方折,隸宗也;大令草書作圓轉,篆宗也。至智永、孫虔禮,右軍派也。
張伯高、僧懷素,大令派也。而其通規,則注意在系連處皆有筆,不得忽略也。』[13]李健《中國書法史》中則不僅涉及『二王』草書,還論及真行書:『右軍草書,隸宗也,其筆方折;大令草書,篆宗也,其筆圓轉。右軍真行,篆宗也,其體長,其勢縱,《黃庭》《蘭亭》等是也;大令真行,隸宗也,其體方扁,其勢橫,《洛神》《白騎》等帖是也。』[14]指出王羲之楷書、行書體長勢縱,宗于篆,草書以方折為主,宗于隸;王獻之則完全反之,楷書、行書體方扁、勢橫,宗于隸,草書以圓轉之筆為主而宗于篆。以此為框架,則不僅可分析『二王』書法本身的風格特征,亦可對『二王』傳統下千余年的書法傳統進行觀察,解析其風格的傳承脈絡。
李健以『方筆圓筆』論建構了中國書法筆法史的主體框架,『方筆圓筆』論也可視作『篆隸宗』論的拓展。李健在《中國書法史》中對兩周金文書法發展大勢的敘述即以『方筆圓筆』論為框架。依此,西周從武王至穆王時期為『方筆』主導,自穆王至幽王時期則以『圓筆』為主導。因青銅器銘文量多且多有紀年,李健以其對銘文視覺特征的敏銳洞察力,將『方筆』『圓筆』主導的歷程定位到多種具有代表性的青銅器銘文。
在論文《書通》中,李健對『方筆圓筆』有總結性的論述:『古今筆法,萬變而靡窮,而扼要者大別為二。解此二法,即可觸類旁通,變化無盡矣。二者何?一為圓筆,一為方筆是也。何謂圓筆?謂筆毫落紙所顯出之形為圓形是也。何謂方筆?謂筆落紙上所顯出之形為方形是也。』[15]雖然李健之前有書學理論家使用過方筆、圓筆的概念,然而以方筆、圓筆來貫通整個書法史的筆法論框架,并對其作出分析性的解釋,則是李健的一大理論開創。
『三紀』書法史框架與『宗匠論』
李健的中國書法史『三紀』—『甲骨紀』對應殷商時代,『金文紀』對應兩周以至于秦,『石刻紀』始于秦,既包括秦、漢、魏晉南北朝以至于隋唐時期的大量石刻銘文書法,又繼以五代以后的法帖。『三紀』從作品實物及其視覺特征出發,基本涵蓋了從殷商至清代的中國書法發展脈絡,是一種開創性的中國書法史敘述架構。
在『三紀』中,『甲骨紀』與『金文紀』涉及的大量書跡并不知其書者姓名。在專門的書法論文《書通》中,李健又建構了『宗匠論』,列出秦代至清代的十一位宗匠:秦李斯,漢蔡邕,魏鍾繇,晉右軍父子,六朝北魏鄭道昭,南梁陶弘景,唐顏真卿,元趙孟頫,明董其昌,清李瑞清。
[16]魏書寬較早關注到李健的『宗匠論』,對其理論內涵作細致分析,指出李健『宗匠』確立的標準—取法、風格獨樹一幟與技法純熟,以及對后世的影響等三個方面。
[17]筆者以為,『宗匠論』雖然完整地表述于論文《書通》中,但在《中國書法史》的《石刻紀》中已經有了大體的形狀,對于『三紀』是一個有益的補充。如果『三紀』注重于作品和風格發展的歷史,『宗匠論』則是一部『有名的藝術史』,強調了各時代風格演進脈絡中宗師—也即『人』的作用。
李健確立的第一位宗匠為秦代李斯,然而此前西周的作品,雖不知其作者名,李健也建構了兩大『宗』:以《大盂鼎》為『方筆之宗』,以《毛公鼎》為『圓筆之宗』。
[18]因此,這兩件重要的西周作品—大盂鼎、毛公鼎,與秦代之后的十一位宗匠,又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中國書法史敘述框架。『三紀』與『宗匠論』都是宏觀的中國書法史敘述框架,其側重不同,如果說前者側重于時代風格,后者則側重于大師風格。
結語李健的書學研究發源于傳統的金石學,而金石學家一般喜鑒藏拓本,與實物材料打交道。然而,與錄文、考證經史為主要目的的金石學家不同,李健延續了李瑞清據實物材料立論、以視覺特征為關注點的立場,且追蹤文字、考古的學術前沿,及時化用于書學研究中。傳統學問與現代學術眼光在李健的書學研究中集于一身。
李瑞清的書學研究受春秋公羊學的影響,注重宏觀的闡釋建構,『求篆于金,求分于石』及『篆隸宗』論就是在此宏觀視野下的重要理論創構。李健則循此有了更多的原創性理論—『方筆圓筆』論從筆法論的角度貫通中國書法史縱向的源流脈絡分析框架,『三紀』(甲骨紀、金文紀、石刻紀)以統一的實物拓本材料構建中國書法史的研究、取法『資源庫』,同時提供了一個時代風格的框架;『宗匠論』則從兩周至清代紛繁復雜的風格流派中遴選出一個大師風格序列,藉此則可以明確中國書法各時代的藝術高度。
注釋:
[1]李健.中國書法史·序例[M]//李健書學文存(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6.
[2]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8.
[3][4][5][7][8][9][11][18]李健.中國書法史[M]//李健書學文存(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4,4,117,169,118-119,4-5,248,246-247.
[6][10]李瑞清.玉梅花盦書斷[M]//段曉華點校.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158,158-159.
[12]李瑞清.陶齋尚書藏瘞鶴銘跋[M]//段曉華點校.清道人遺集.合肥:黃山書社,2011:73.
[13][15][16]李健.書通[M]//李健書學文存(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405,404,403-404.
[14]李健.中國書法史[M]//李健書學文存(二).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422.
[17]魏書寬.李健書學研究[D].首都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34-37.
作者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藝術學院
本專題責編:范國新 熊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