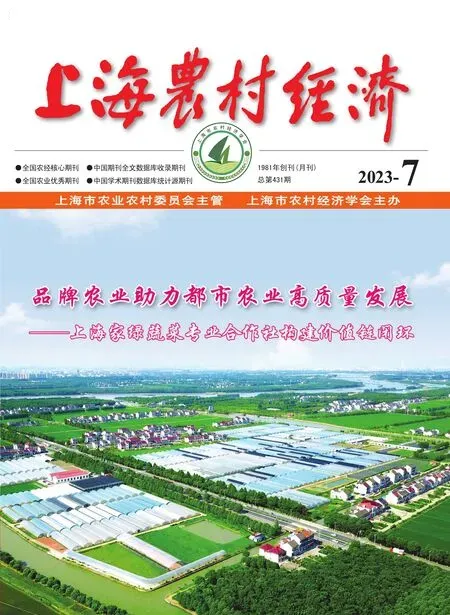一九八五那年去深圳
——為了春天的紀念
■ 張金泉
那年,日歷正翻在1985,深圳特區成立第五年,我任昆岡鄉黨委書記一年零三個月。彼時南方改革發展如火如荼,我們這里好像還不那么熱烈。鄉黨委決定由我帶隊,到南方去吸收“新鮮”空氣。我和工業公司經理朱衛民、農業公司經理朱方文、駐滬辦事處主任郁唐生和飛達經編廠廠長江利明一行,于是年4月4日踏上了南下廣州、深圳的考察之路。
想那年我已40多歲了,乘火車棚車來回江蘇丹陽倒有好多回,坐飛機還是大姑娘上轎——第一次。在虹橋機場洗手間,見那水龍頭旋轉把手是個亮晶晶圓形東西,對于用慣了丁字形旋轉鐵質水龍頭的我來說的確犯了難,不知怎么使用,不敢亂動,后看到別人使用才算開了竅。一個剛從田埂上走出來的人,在上海機場就遇到這種事,心想到南方廣州、深圳不知會怎樣。
不出所料,到了廣州、深圳果然一切感覺都很新鮮,如劉姥姥跌進大觀園一般。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滿街跑的出租車和帶有空調的小型公共汽車。當時我坐在公共汽車上還不知道車頂兩邊那些個圓的東西是空調的出風口而不敢撥動吹風。當我看到這么多車子滿街跑,就聯想到我們昆岡為了弄輛面包車,想方設法沒有門路,甚至還給上海市原副市長宋日昌寫信,后來花了六千元錢弄了輛淘汰下來的舊面包車,終因辦不了牌照而只能停在鄉政府機關的院子里,后來還被批評為“瞎弄”。
當時,在廣州一碗面條賣5毛錢,稀飯二三毛錢一碗。對于上海當時陽春面8分一碗、稀飯幾分錢一碗的價格來說,反差實在太大了,吃粥、吃面條也感到太貴。在深圳,當時吃一頓中飯一般需5元。想我們當時在鄉食堂一頓飯只要幾毛錢,連吃飯也有點舍不得了。面對這種高消費,我們只好多吃面條少吃飯,硬挺著過去。
深圳的飯館稱為飯莊。招牌上寫的生猛海鮮不知為何物。更為稀奇的是飯莊、酒莊門口站著穿旗袍的小姐,我們不知她們是什么人,見門口和里面又裝修、擺飾得富麗堂皇,有點嚇絲絲,不敢走近,更不敢走到飯莊的里面去看看。所以那次去深圳,大的飯莊里我們一次都沒去吃,都是在小飯攤解決的。到了香蜜湖度假區,更是眼界大開,好多東西從沒看到過,一片繁榮景象,相當好奇。那時朱方文穿軍大衣,我穿中山裝,他們三人著西裝,但料作比較蹩腳不挺括。人們哪知我們是從上海來的,反正當地人一看就知道我們是從外地來的。由于香蜜湖度假區的門票價格很貴,有些設施我們也不知怎么個玩法,所以我們只是在外面兜兜轉轉,所有游樂設施都未去玩過。
我們去深圳時帶了當時昆岡鄉幾家鄉辦廠生產的皮鞋、男女手套、裝飾用的經編織物以及帆布樣品,想放在深圳市場去試試水。當時我縣九亭鄉已在深圳的上埗區上埗村巴登89號設立了辦事處。我估計因為租金的問題,地方比較偏僻,是昔日農村破舊的地方。他們派有朱朋仁等三四名同志在哪里工作。1985年4月10日,我們花了好大一會工夫,終于找到這個地方。在那里,我們遇到當時九亭鄉鄉長王順榮,老鄉在深圳相見,不亦樂乎。我們所以去哪里,一是去參觀學習,因為昆岡也想在深圳設辦事處,二是把我們帶去的工業產品請他們幫助出樣試銷。九亭鄉當時的黨委書記許文華思想是很開放的,不但鄉辦工業發展走在全縣前列,在市場展拓、產品營銷等方面也是比較超前的。深圳的那個上海九亭辦事處不僅為松江第一,就是當時全上海郊區也沒幾家。我記得南匯的橫沔已在那里安營扎寨,不僅建立了辦事處,又設立了產品展示廳,我們參觀后覺得這是“走出去”發展經濟的明智之舉。
那次去深圳,我們還去深圳的蛇口工業區轉了一圈,見那里正在劈山造地,大興土木,井架林立,塔吊遮天。當我們登上那艘在蛇口、被稱為“海上世界”的旅游船時又是驚嘆了一番。一條船上,吃喝玩樂什么都有,人頭攢動,好不熱鬧,這第三產業的興旺景象深深地吸引著我們,弄得我們心里也是癢癢的。因為我們昆岡當時也成立了旅游發展公司,買了一條曾是水利用的小輪船,想用于開辟水上游玩線路。到蛇口一看,小巫見到了大巫,不可相比。暗想唯有埋頭苦干,努力追趕才是。
當時,去南方考察的人已不少,深圳無機場,在廣州又買不到直接飛上海的機票。因此,我們于4月14日乘飛機到杭州,又轉乘出租汽車于下半夜到達昆岡設在上海徐匯區宜山路的駐滬辦事處,吃過宵夜,將就休息。15日上午回到松江,考察圓滿結束。
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經45年了,離我們那次去深圳考察也已有38年。當年我們去深圳考察的五人中有兩位已遠行而去。想想過去,看看今朝,思潮如涌,夜不能寐,除了感慨還是感慨,除了感嘆還要感嘆!真是春天故事開新天,引來春色滿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