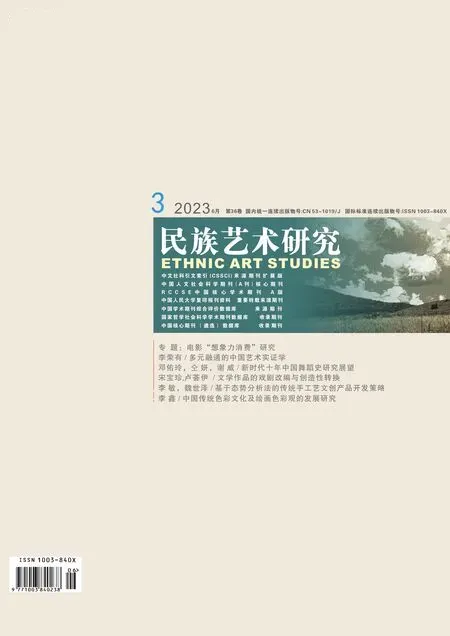東南亞勉瑤民間禮俗音樂文化考察研究
趙書峰,房 珩
勉瑤是一個世界性分布的離散族群,現主要分布于中國的湖南、廣東、廣西等地以及老撾、越南、泰國、美國等海外國家。本文結合海外音樂民族志理論,主要關注東南亞老撾勉瑤傳統音樂的發展與變遷研究。眾所周知,關于東南亞勉瑤文化的研究,主要以日本民族學、民俗學界為代表,如: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日本民俗學家白鳥芳郎的《東南亞山地民族志》①白鳥芳郎.東南亞山地民族志[M].黃來鈞,譯.昆明:云南省歷史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1980.、吉野晃的《泰國北部優勉(瑤)親屬組織與祖先祭祀的社會人類學研究》②吉野晃.泰國北部優勉(瑤)親屬組織與祖先祭祀的社會人類學研究[D/OL].東京:日本東京都立大學,2007.為代表,主要關注泰北勉瑤的經濟生活、物質生活、社會結構以及勉瑤民間儀禮中的“家先單” “祭祀制度” “婚俗儀式”等民俗事象并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廣西民族學院赴泰國瑤族考察組所編著《泰國瑤族考察》③廣西民族學院赴泰國考察組.泰國瑤族考察[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一書,系統介紹泰國瑤族社會的政治、經濟、教育、歷史、婚姻、喪葬、宗教信仰、文化藝術等內容,是一本初步介紹泰國瑤族社會歷史文化的著作。玉時階的3篇論文《泰國瑤族的“招郎入贅”》④玉時階.泰國瑤族的“招郎入贅”[J].世界民族,1998(4):77-80.《泰國瑤族的喪葬習俗》⑤玉時階.泰國瑤族的喪葬習俗[J].世界民族,1996(4):48-52.《泰國瑤族的歷史和文化》⑥玉時階.泰國瑤族的歷史和文化[J].民族論壇,1993(1):85-89.針對泰國瑤族的人生禮儀、社會歷史等內容進行了初步考察。筆者的3篇論文《跨界族群與音樂認同——老撾優勉瑤婚俗儀式音樂的身份問題研究》⑦趙書峰.跨界族群與音樂認同——老撾優勉瑤婚俗儀式音樂的身份問題研究[J].中國音樂,2021(3):71-79.《中、老瑤族婚俗樂舞的風格與形態描述》⑧趙書峰.中、老瑤族婚俗樂舞的風格與形態描述[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20,34(4):73-88.《老撾優勉瑤婚俗音樂田野考察與初步研究》①趙書峰.老撾優勉瑤婚俗音樂田野考察與初步研究[J].中國音樂學,2020(1):90-100.主要針對老撾優勉瑤族婚俗進行初步考察。張應華的《“一帶一路”向度中跨界族群音樂課程思維研究——以東南亞苗瑤族群為例》②張應華.“一帶一路”向度中跨界族群音樂課程思維研究——以東南亞苗瑤族群為例[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22(3):60-74.,主要從“一帶一路”跨文化認同與跨文化共建的特定語境中,去探析其課程策略的觀念與內涵。綜上所述,關于東南亞優勉瑤文化研究多集中于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領域,多是對其人口、經濟與社會生活狀況、族群遷徙、民俗禮儀等給予的初步記錄與描述。
當下,中國民族音樂學界關于東南亞老撾勉瑤傳統音樂的研究基本是微觀個案的考察,在宏觀視域下展開的比較研究成果略顯單薄,尤其缺少基于海外民族志書寫維度去審視東南亞勉瑤傳統音樂的發展變遷研究,為此本文結合老撾勉瑤民間禮俗音樂與唱本的田野考察,展開與中國勉瑤音樂的比較分析研究,進而觀照東南亞勉瑤音樂的變遷與在地化過程。
一、老撾勉瑤田野點考察概況
2023年2月湖南師范大學 “海外音樂民族志”研究團隊成員趙書峰、房珩、符安可、徐瑞一行4人對老撾勉瑤民間禮俗唱本展開了為期16天的田野工作。主要針對老撾首都萬象 (Vientiane)、博利坎賽(Bolikhamxay)、川壙 (Xiangkhouang)、華潘 (Houaphanh)、瑯勃拉邦 (LuangPrabang)、沙耶武里 (Kaign Abouli)等地的苗瑤族群傳統音樂展開田野調查 (見表1),通過表1考察點信息內容可以看出老撾勉瑤除了以瑯南塔、博膠省為主要聚居地之外,在華潘、瑯勃拉邦、沙耶武里分布也較多,其中與越南接壤的華潘省的勉瑤族群分布點更為集中。勉瑤人口比重占老撾總人口的9%,主要分布于海拔較高的地方,以呈沿道路兩旁分布的條狀以及沿山脈分布的網狀為主。老撾勉瑤村寨主要以盤姓、趙姓、鄧姓居多,這與國內廣東、廣西、湖南的勉瑤村寨姓氏情況相同,每個村寨至少都會有一個師公,來主持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民俗儀式。團隊成員考察期間通過對各個瑤寨師公保存下來的祖墳書/圖進行整理得知,中國勉瑤至老撾的遷徙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從中國云南到老撾;一條從中國到越南再到老撾。不同的遷徙路線會對老撾勉瑤族群居住點的分布以及儀式用樂與文化傳承和保存產生一定的影響。

表1 老撾勉瑤田野考察點信息介紹
二、老撾勉瑤語言的文化變遷
2023年2月17日,為了開展中國勉瑤與老撾勉瑤語言的比較研究,筆者安排華潘省MeuangSon(縣)banwa(村)勉瑤 [som[51]tho?55]先生與湖南藍山縣瑤族趙金付師公通過微信視頻通話的形式進行跨國對話交流,通過觀察二者的溝通過程看出,他們彼此之間存在某些語言互相聽不懂的情況,雖同屬勉瑤,但其語言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筆者通過國際音標的記寫更加直觀地感受到中國與老撾勉瑤在日常交流的語言方面存在的差異性與共性特征(見表2)。

表2 中國勉瑤與老撾勉瑤語言的差異性與共性比較
雖然中國、老撾勉瑤的語言同屬于漢藏語系苗瑤語族瑤語支,但二者之間已經出現在一些日常交流用語方面的不同。索緒爾認為“語言在任何時候都絕不會離開社會現實而存在,因為它是一種符號現象,它的社會性就是它的內在特征之一。”①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全新譯本)[M].劉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94.可以看出,在老撾語的影響下勉瑤的歌唱語言逐漸在經歷“在地化”的過程中發生了日常交流語言涵化的現象,但其主體基本未變,仍在勉語體系的元音系統及音節結構里。瑤族在與老撾本族人交往的過程中,為了拉近與對方的距離,會有意無意地對原語言進行再創造,這樣創造出來的語言得到族群的認可后并流傳開來,從而產生一種在原語言基礎上的新的語言規則,這樣的現象即稱之為言語趨同現象。“言語趨同指在言語交際過程中交際一方改變自己原有的言語習慣或語體以更接近說話對象的言語或語體。它可表現在發音、語速、停頓、語碼等方面。一般來說言語趨同追求的是獲得對方的贊同、接受、喜歡或好感增進理解和交際效果以及相互間的吸引力等。應該指出它們往往是相互作用同時存在。言語趨異指交際中的一方使自己的言語或語體變得與說話對象的言語或語體不同。言語趨異主要是為了保持說話人自己的社會身份特征和群體特征。”①劉正光.言語適應理論研究述評[J].語言文字應用,2001(2):58.語言被人們賦予了不同的功能性,經書里的語言文字所承載著的是勉瑤族群的歷史記憶,為了加固歷史族群記憶,就會以文字經書的形式將其傳承下來,強調族群身份認同。勉瑤經書中使用的文字為漢字,筆者發現部分勉語,在不同的語境中,其發音是不一樣的,比如“酒”字,以文字形式出現在經書上時,誦讀發音為[?j?u55]和國內誦讀發音相同,當作為日常交流用語時這個字的發音為[tj?u55];又如“魚”字,當以文字形式出現在經書上時,誦讀發音為[n(i)?u55]和國內誦讀發音相同,當作為日常交流用語時這個字的發音為 [piau55],這就體現了語言在不同語境中的語音的差異性。語言與音樂是緊密相連的,民間禮俗唱本中的文字誦讀發音與演唱時的發音基本相同,僅僅只是文字時值長短與音調的變化,如 “茶”這個字,其經書誦讀發音與演唱時的發音都為 [tsa],只是誦讀時音調為 [tsa51],而演唱時在原有文字發音基礎之上賦予音符旋律性的發展進行,所以正是由于老撾勉瑤語言的涵化現象給其民間禮俗唱本的音樂變遷奠定了重要基礎。
三、老撾勉瑤民間禮俗唱本的初步分析與比較研究
(一)經書中出現漢字勉語發音被老撾拼音替代的現象
老撾民間禮俗唱本書寫符號的變遷表現為傳統的用勉語歌唱語言表述漢字書寫的唱詞發音被老撾語拼音替代。筆者在考察過的11個勉瑤村落中,發現其中有4個瑤寨存在用老撾拼音來記錄漢字瑤話發音形式的現象,如圖1所示華潘省桑怒市Sop Bao縣Ban Phieng home的趙延保師公所用經書,左側記寫的是漢字右側記寫的是老撾語拼音。筆者將勉瑤經書唱本中同一段文字的瑤語發音(見表3)和老撾語拼音發音(見表4)以國際音標的形式進行對比分析。

圖1 華潘省桑怒市Sop Bao縣Ban Phieng home的趙延保師公所用經書②房珩2023年2月拍攝于華潘省Ban Phieng home。

表3①記寫時間:2023年3月25日;記寫人:房珩;誦讀者:趙延保。 勉瑤經書唱本部分瑤語發音國際音標記寫

表4②記寫時間:2023年3月25日;記寫人:房珩;誦讀者:趙延保。 勉瑤經書唱本部分老撾拼音發音國際音標記寫
通過國際音標的記寫可以看出老撾拼音記寫漢字勉語發音和未被老撾拼音記寫的漢字勉語發音是一樣的,老撾部分勉瑤師公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傳承自身文化,而這樣的方式也逐漸被流傳開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識讀漢字能力的傳承在老撾是非常艱難的,因為年輕一輩多以老撾語的識讀為主。這種用老撾拼音記錄漢字的形式,無疑是讓勉瑤文化得以傳承下來的一個有效途徑,通過固化集體記憶的形式來加強族群認同。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文字經書唱本看作為也是集體記憶的一種,其有著超脫于文字本身的意義。筆者認為勉瑤語言在老撾呈現出二次翻譯的現象,瑤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其所使用的文字(漢字)是對瑤語翻譯的書面呈現,這是第一次翻譯;老撾漢字勉語發音被譯為老撾語,這是第二次翻譯。兩次語言轉換實際上就是兩次文化的轉換,在轉換過程中瑤語原生性文化與譯文文化的性質與內容在語言符號系統中句法的 (syntactic)、語義的(semantic)和語用的(pragmatic)的關系會出現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現象。“符號學理論超越語言分析的框框把翻譯活動當作社會文化現象來研究,即從文化對比角度出發,對原語和譯語進行語際的和語用的調整,全盤把握原文信息動態反應追求非一字一句地機械對應,保證原文和譯文在不同文化中最大限度地達到交際功能的一致或對等。”③孟建鋼.文化·翻譯·語用等值——兼談符號學理論在翻譯中的運用[J].中國科技翻譯,2000(1):3.第一次翻譯呈現出的文字語言具有表征儀式行為的意義,那么第二次翻譯,僅僅只是標記拼音,并不能表達瑤語漢字所指代的含義,失去了文本在儀式中的活態實踐與應用目的。綜上所述,標記漢字讀音,能做到的僅僅只是讓傳承人知道漢字唱詞如何讀與唱,但是其深層意涵以及上下句唱詞串聯起來的語境意義表達是老撾拼音標記無法實現的。
(二)老撾勉瑤民俗儀式的用樂考察
老撾勉瑤的音樂在當地主流文化(老龍族文化)與跨文化互動影響下, “在地化”現象在當地民俗儀式中體現頗為明顯。比如:在勉瑤民俗儀式中會使用老龍族音樂,又或者在當地“掛燈”儀式和喪葬儀式會同時舉行,這種文化涵化現象并不是一個短期的過程,而是一個長期嬗變的過程。筆者以老撾勉瑤遷徙的路線作為切入點,利用祖墳書的民間歷史記憶材料進行梳理,對東南亞勉瑤不同田野點的民間禮俗唱本從音樂到唱詞文本結構、唱本文字發音的書寫符號的異同展開比較分析。以“掛燈”儀式中《引師男跳鬼歌》(譜例1)、《掛燈》(譜例2)為分析個案。
譜例1①記譜時間:2023年3月25日;地點:瑯勃拉邦省瑯勃拉邦市。:

譜例2①記譜時間:2023年3月25日;地點:華潘桑怒孟埃(Meuang Et)南恩(Ban Nan En)。:

《引師男跳鬼歌》其旋律由“do mi sol”三個音構成,節奏為3/4拍和4/4拍交替出現,曲子為do調式,旋律以同度、三度進行,有時會有個別音出現五度跳進的情況,由譜例可以看出每一句的倒數第二個字,大都存在一字多音的情況,且都為三度的音程跳進。整體的旋律發展手法較為單一,由一個基本音調進行反復、變化,整體旋律做平穩進行。《掛燈》旋律由“do mi sol”三個音構成,整體旋律以 “do mi”兩個音為主,“sol”音在整段的旋律中只出現了一次,其節奏為6/8拍和2/4拍交替進行,整首曲子旋律音程為三度音程和同度音程構成,旋律線為直線和上下不超過三度的曲線進行,除了個別字,其余多為一字一音,節奏型以八分音符、四分音符、四分附點音符為主。
總之,老撾勉瑤的“掛燈”音樂有以下特點:第一,以五聲調式為主,旋律由“do mi sol”三個音構成,每句結束的落音為“do”和“mi”,旋律發展手法較為單一,由一個基本音調進行反復、變化,整體旋律做平穩進行;第二,其旋律音程跳進多為三度和同度音程進行,旋律線以直線或者浮動不大上下波動的曲線為主;第三,節奏型較為單一,主要以八分音符、四分音符為主,整體節奏、強弱規律基本相同;第四,在演唱中沒有出現加入襯詞的現象,基本為一字對應一音的形式進行演唱。
老撾勉瑤和中國瑤族的“掛燈”儀式都是瑤族男子身份認同的象征體現。此次采錄到的老撾勉瑤“掛燈”儀式的演唱是脫離儀式進行的,具體的儀式內容和流程無法與國內勉瑤“掛燈”儀式建立比較研究,這也是此次考察的遺憾之一,單從音樂形態分析來說,與國內瑤族音樂的旋律進行和節奏基本保持一致,都是由“do mi sol”三個音構成,旋律平穩進行,由一個基本音調進行反復、變化,整體旋律做平穩進行,整體節奏基本相同,節奏型較單一。唱本的內容與唱詞結構與國內瑤族“掛燈”差異性不大,襯詞在掛燈儀式中出現頻率較少,主要以“啊”“吶”結尾居多。
(三)經書唱本流失現象下的傳承問題思考
“還盤王愿”是瑤族祭祀先祖盤瓠的傳統民俗儀式。據《搜神記》記載: “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①干寶.搜神記[M].賈二強,校點.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97.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校注》:“瑤人每歲十月旦,舉峒祭都貝大王,于其廟前,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男女各群,聯袂而舞,謂之踏搖”②周去非.嶺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9:423.。通過這些史料可以看出瑤族盤王儀式有著悠久的歷史,起碼可以追溯至晉代,并流傳至今,在國內廣東、廣西、湖南等地廣為流傳。“還盤王愿”儀式不僅僅是一個民俗儀式,更是族群歷史記憶的象征,而盤瓠象征其族群的信仰。分布至世界各地的瑤族人民,通過舉行“還盤王愿”儀式,來加固群體歷史記憶,強調文化身份認同,分散至不同地區的勉瑤人民通過對祖先盤瓠的祭祀追溯,重塑族群的集體歷史記憶。“還盤王愿”儀式在老撾被稱為“奏鐺”(??u51ta?55),這種象征著族群信仰的儀式,在老撾已經很少做了。其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沒人會做,第二就是沒有足夠的經費和時間去做。在老撾一路考察了11個瑤寨,只有2個村寨的師公會唱《盤王大歌》,有的村寨里的師公即便有歌本,也不會唱了,那么這樣流傳下來的經書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只是一堆文字記錄的死本,只有把靜態的經書文字放置于活態的儀式中,才能起到經書文本與 “神靈”“家先”的溝通作用。與中國勉瑤相比,老撾勉瑤的民間禮俗唱本保存問題呈現出典型的區域化差異的情況,即與越南交界處的華潘省勉瑤的民間禮俗唱本保存較為完好,但是“還盤王愿”儀式(《盤王大歌》)已逐漸消失,相比之下老撾與泰國交界處的沙耶武里勉瑤的《盤王大歌》唱本保存較好,且有勉瑤大法師鄧貴鳳先生每三年在博膠省主持的大型集體“還盤王愿”儀式。老撾的“還盤王愿”儀式和國內傳統的“還盤王愿”儀式有一定的區別,在中國“還盤王愿”儀式的執儀者為師公和歌娘,他們在儀式中都會演唱《盤王大歌》,只是師公和歌娘演唱部分不同。在老撾的“還盤王愿”儀式中,執儀者只有師公,原本歌娘演唱的《流樂書》部分被師公取代,歌娘由原本的儀式執儀者的身份轉變成在儀式中師公演唱時跪拜的角色。儀式的舉行對于塑造和維持族群的共同記憶起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對勉瑤師公傳承人調查情況(表5)可以看出,在當下師公大多存在沒有傳承人的現象。

表5 老撾勉瑤師公傳承人調查情況表
在老撾勉瑤族群音樂文化傳承面臨著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語言問題。在老撾會識讀中文漢字的只有老一輩的師公,村子里年輕人的成長教育背景和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讀寫老撾文字,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不會讀寫中文在老撾勉瑤族群就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因為經書中所使用的文字為漢字,這就使得儀式中經書頌唱的傳承變得非常困難。第二,文化身份認同問題。在老撾勉瑤年輕一輩很少有自發性地想要學習本民族的音樂文化,而對于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傳承工作,只有村里的師公會有意識地自發性的為了強調歷史共同記憶,去主動協調 “文化傳承”和“文化適應”之間的關系。第三,經濟問題。因為老撾的瑤族生存條件比較差,所以也會面臨著沒有經費置辦儀式的現象,沒有人愿意出錢出力請師公做儀式,久而久之,就會出現傳統民俗儀式流失的現象。
四、老撾勉瑤傳統音樂的“在地化”原因探究
老撾勉瑤音樂文化呈現出“在地化”的樣貌特征。所謂傳統音樂文化的 “在地化”研究,是指由國家的“大傳統” (主文化)在流動與傳播背景下,與地方 “小傳統”(亞文化)文化互動與交融后,形成的一種新的具有區域與地方化的歷史話語建構。①趙書峰.湘中民間儀式音聲的“在地化”與互文性研究[J].民族藝術研究,2019(3):94.老撾勉瑤“在地化”現象主要原因分為以下幾點:其一,由于老撾勉瑤村寨分布較為分散,呈道路兩旁分布或沿山脈聚集居多,部分與老龍族雜居,雙方在雜居生活的過程中,二者的生活方式、語言、音樂、文化、思想觀念等等都會相互影響;其二,勉瑤頻繁的遷徙,在音樂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與其傳播地域國家的語言、文化發生互動交融現象,進而形成語言的“涵化”過程;其三,全球化背景下自媒體技術的高速發展,給勉瑤文化的傳播提供了異常便利的交流平臺。比如:老撾勉瑤會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臺上推廣自己的文化,促進了勉瑤傳統文化的全球化傳播與文化變遷。總之,老撾勉瑤音樂的“在地化”現象是其傳統文化發展與傳承的需要,也是面臨新的文化傳播語境中,保存與延續自我文化的一種有效的發展策略。老撾勉瑤語言的涵化現象與其民間禮俗音聲表達符號的變遷彰顯了勉瑤族群文化認同與其所處的主流文化認同之間的理解與包容。
結 語
海外田野考察要求學者應具有“雙重語言能力”,它是與當地人建立良好關系的鑰匙,是獲得大量海外一手資料的基礎。由于團隊成員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使我們此次的田野考察留有遺憾。此次我們對老撾11個瑤寨的村落信息以及他們的音樂文化進行了初步的考察,本文把其放置于老撾的經濟、政治、主流文化語境中去闡釋,從文化變遷的視角分析老撾勉瑤的語言、民俗儀式與音樂文化,審思勉瑤音樂變遷下的文化傳承和傳播問題,初步建立中、老勉瑤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筆者認為,其一,老撾勉瑤民間禮俗唱本保存較為豐富,但是因其儀式傳承語境與傳承環鏈出現問題,導致其儀式唱本的用樂語境漸趨消失,只有神圣性較強的“掛燈” “喪葬”儀式音樂保存較好;其二,老撾勉瑤唱本漢語書寫的傳承語境受到老撾語的影響,導致其唱本語言音聲符號書寫被老撾拼音取代,形成了勉瑤音樂符號書寫的“在地化”現象;其三,老撾勉瑤遷徙路線的不同也造成了其民間禮俗唱本書寫的差異性問題。總之,海外音樂民族志田野工作應建立一種跨文化間比較思維,即從東南亞視野回看中國勉瑤音樂的發展與變遷。通過儀式唱本、民間口述文本的分析比較來觀照中國與東南亞勉瑤民間禮俗唱本的唱詞結構、語音學、音樂形態共性與差異性。老撾勉瑤音樂的變遷問題要用辯證的眼光去看待,要去關注到隱藏在文化變遷下的文化傳承問題,我們要把老撾勉瑤音樂置于整個中國與東南亞勉瑤文化圈審視其音樂的傳播與變遷的歷史軌跡。同時從東南亞勉瑤民間禮俗音樂與中國勉瑤音樂的相似性看出,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東南亞國家的文化傳播與在地化現象,也是從全球視角、世界社會的構建過程中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間的互鑒的結局。因此開展海外音樂民族志研究有助于整體觀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融與互動過程,借以觀照勉瑤音樂的世界性建構與文化傳播。總之,通過對民間禮俗唱本與儀式樂舞的比較研究以此觀照東南亞勉瑤與中國勉瑤音樂之間的淵源關系,以及全球化語境中導致的老撾勉瑤音樂文化變遷問題。勉瑤在經歷跨文化、跨區域、跨國境的長期遷徙過程中,其音樂的變遷就是為適應東南亞國家“大傳統”文化語境或主流文化認同而自愿選擇的一種生存策略,由此造成勉瑤民間禮俗唱本的音聲形態的“在地化”與儀式用樂語境的變遷。此次東南亞老撾勉瑤音樂的田野初步考察研究,我們獲得了大量的民間禮俗唱本方面的一手資料,為團隊成員“東南亞勉瑤音樂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也從宏觀維度認識到“世界性社會”語境中東南亞勉瑤音樂文化的發展與傳承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