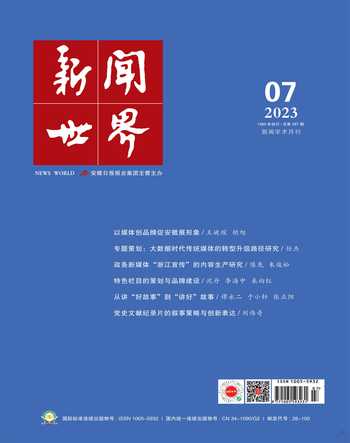紀錄片“過去時”的表現手法及問題規避
張魁
【摘? ?要】紀錄片是一種非虛構的影視藝術體裁,其重要價值之一就是對當下“現在進行時”的記錄,為后人留下珍貴的影像資料。然而在很多電視紀錄片或紀錄電影中,難以避免會涉及“過去時”的內容,這部分內容該使用什么樣的手法進行表現,一直以來都是業界比較關注的話題,本文對此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紀錄片;過去時;再現;表現手法;問題規避
在紀錄片拍攝實踐過程中,導演經常會遇到一個問題,片中某一板塊的內容很精彩,甚至是關鍵故事或信息,但已經發生過了,那么這一部分內容該使用何種手法來表現呢?
其實,從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北方的納努克》開始,關于紀錄片如何表現“過去時”的思考一直都沒有停止。隨著科技的進步,更多技術手段的融入,“過去時”的表現方式也更加多樣化。
紀錄片“過去時”表現方式的設計和選擇,主要基于彌補視覺表現盲區、讓故事更具完整性、滿足受眾的視覺需求、讓紀錄片更有可看性等幾個方面進行考量。
一、紀錄片“過去時”的表現手法
(一)再現
真實再現是紀錄片領域使用較為頻繁的“過去時”表現方式,是紀錄片情景再現的表現方式之一,它是指“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以扮演、搬演的方式通過聲音與畫面設計,表現客觀世界已經發生或人物心理的一種制作技法”[1]。這種表現方式在很多類型的紀錄片中都有所使用,尤其在歷史文化類紀錄片中使用更為頻繁,把歷史搬上熒幕其實是影視劇最擅長的內容,而歷史文化類紀錄片是非虛構的影視藝術形式,將非虛構內容和影視劇的表現方式相結合,是紀錄片作為視覺藝術最為直接的方式之一。
《美國:我們的故事》《故宮》《中國文房四寶》《河西走廊》《中國》等很多國內外經典的歷史人文類紀錄片,都是采取演員扮演的方式進行視覺敘事。這種方式可以有效彌補紀錄片敘事過程中影像難以表現的不足,可以讓紀錄片的視覺表達更明了、生動。
《北方的納努克》被公認為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該片以愛斯基摩人中最出色的獵手“納努克”為主角,展現了他們捉魚、獵捕海象、建造冰屋的場景,以及中間遇到的故事。但這部片子同樣也使用了情景再現的表現方式,比如影片拍攝時愛斯基摩人捕海象已經不用魚叉,而是用步槍。為了拍到更為原始的場景,導演要求納努克用他爸爸的方式獵捕海象。
這里面的情景再現是被記錄對象自己完成“過去時”的搬演。這種方式我們目前在拍攝實踐過程中也會在片中局部用到。比如在拍攝類似的工程類紀錄片《鶴舞長江》《總師傳奇》以及筆者正在拍攝的反映引江濟淮工程的紀錄片《千里江入淮》的過程中,往往攝制組介入拍攝時工程已經在施工了,甚至快要結束了,但片中還需反映工程規劃、勘測、設計階段的內容,此時最有效和直接的辦法就是請“原班人馬”根據回憶和適當的情景設計,重新搬演一遍,以實現紀錄片內容、信息、故事的完整性。
意向性再現是情景再現的另一種表現方式,雖然它也包含真實再現的扮演、搬演成分,但會刻意回避扮演、搬演者的正面鏡頭,主要突出故事氛圍的營造、局部細節的刻畫。這種再現方式成本較低,虛實結合,并且能夠很好地表達意境。
在筆者參與導演的紀錄片《八月桂花遍地開》第四集中,就多次使用了意向性再現的方法。其中有一段涉及徐海東將軍和夫人周少蘭的解說詞是這樣的:“敵人被擊退了,重傷的徐海東經過緊急搶救,雖然止住了血,可喉腔被異物堵塞,呼吸困難,生命垂危。這時,17 歲的女護士周少蘭,用嘴將堵在徐海東喉嚨中的血塊,一口一口地吸出來,徐海東得救了。”這個故事出自多位老將軍的回憶錄,但當時沒有留下任何影像資料,如何進行影像表現成了難題。為此,我們找到了類似紅二十五軍長征中居住過的土坯房和土炕,從文物收藏者手中借來了同時代的軍用醫藥箱和同時代當地居民使用的油燈、茶碗,借助燭光、燈影、土墻、炭火和演員模糊的動作完成了這段故事講述,收到了較好的表達效果。
(二)聲像資料整合
法國人尼埃普斯拍攝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張照片《窗外》,此后,人類逐漸完善了掌握真實影像的能力。從照片到電影膠片影像,利用真實的影像也成為紀錄片創作過程中最好的“過去時”表現方式之一。通過分層技術、AI技術,能夠讓單張或一組照片運動起來,實現視頻化效果。當然如果能收集到相關機構保存的紀實影像資料,效果會更好。一般情況下,視頻影像要好于組照影像,組照影像要好于單張照片。在紀錄片創作過程中,創作者往往會忽略另一種可以很好表現“過去時”的資料,那就是聲音資料。
1877年,美國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臺留聲機。這臺“會說話的機器”轟動了世界,正式開啟了人類錄音的歷史,此后錄音技術的不斷進步,也給人類留下了豐富的聲音檔案。
筆者參與創作的《八月桂花遍地開》《百年壯歌》等紀錄片中,涉及很多開國將軍和新中國發展過程中重要歷史事件的親歷者,經過調研發現,我們能發掘的人物影像資料非常有限,但不經意間卻發現了一些非常珍貴的聲音資料。比如在《八月桂花遍地開》第四集中涉及紅二十五軍長征中的庾家河戰斗,我們起初能夠找到的只有軍史文字資料,后來經過進一步調研,意外發現了一位曾經參加過戰斗的老紅軍夏德義的聲音資料:“我們這個部隊山上站崗的有少數人,還有一部分在做飯吃,結果,國民黨蔣介石的部隊就采取了突然襲擊的辦法,開頭上來的是一個連的兵力,接著以后就是一個營的兵力,陸陸續續又增加。”“紅軍戰士那是鐵打的兵,他只能前進不能后退的,就在那里和敵人展開了肉搏戰,一直打。堅持到最后的時候,我們這個排 28 個人,就剩下 3 個人。”這段錄音有細節有情緒,于是在創作過程中我們使用了真實的錄音加意向性空鏡頭、手繪動畫等手法表現這些“過去時”內容,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表達效果。
(三)文獻、回憶錄檔案
文獻、回憶錄檔案是紀錄片特別是涉及歷史內容的紀錄片創作中必須依靠的珍貴資料。不僅為導演創作文本提供依托,如果處理得當的話,也為紀錄片“過去時”的視覺表達提供影像支持。這種影像支持是多種多樣的,第一,可以直接對文獻、回憶錄檔案進行藝術化拍攝,這也是比較常用的方法;第二,對文獻、回憶錄資料進行動畫處理,優化視覺表達;第三,對文獻、回憶錄中涉及的片段進行角色配音加意向性再現或者動畫包裝相結合的表達方式。
在紀錄片《百年壯歌》中,涉及安徽第一個城市黨支部的內容。這里能拍攝的只有一個翻新的舊址,缺乏故事細節,枯燥無味。但在調研過程中,一段老房東的回憶文字引起了導演的注意——我還記得黨團組織和中央聯系的一些暗語,如“大學”指黨組織,“中學”指團組織。“總店”指中央,“分店”指地方組織,“民校”指國民黨。被捕叫“進醫院”,案情不大叫“傷風感冒”,案情較大叫“要動手術”,被殺叫“病故”,要上面派人來叫“請來結賬”。這段文字形象地向人們揭示了建黨早期從事地下工作的艱難,細節詳實,故事性強。于是導演就使用角色配音加信箋動畫包裝的方式對這段內容進行呈現,提升了片子的“鮮活度”。
(四)尋訪
用尋訪的方式表現“過去時”,能夠體現現實時空和歷史時空的交融,相比再現等表現手法更加具有紀錄片本真的“紀實味道”。尋訪人通過實地走訪、采訪,用對話或感受的方式從現實走進歷史,將過去發生的事情通過現實人物講述出來,是紀錄片“過去時”另一種最具“性價比”的表現方式。
在紀錄片《八月桂花遍地開》中,因為涉及的開國將軍的故事都發生在過去,因此各集導演都精心選擇了每一集或者是每一個大的故事板塊的尋訪人。在第四集《北上先鋒》中,導演選用了兩位尋訪者,一位是長征途中犧牲的紅軍的后代,一位是金寨干部學院的老師。其中一位尋訪者在尋訪到獨樹鎮戰斗遺址后,通過和當地黨史專家進行交流,巧妙地展現出紅二十五軍在這里發生的驚險的戰斗故事,同時發出感慨:“將有必死之心,士無貪生之念,只有這樣的隊伍才能經受住考驗,打不垮,沖不散。”這恰恰也正是導演想要表達的內容。通過尋訪者每到一地的所見、所聞、所感,可以沉浸式地展現革命先輩艱苦的戰斗歷程和豐富的內心世界。
(五)資料影像與實景或造景相結合
2009年,周兵導演的紀錄片《臺北故宮》中使用了歷史影像和造景相結合的情景設計,讓觀眾眼前一亮。為了表達故宮文物在抗戰時期的艱辛轉運,導演以真實影像為背景,以搭建的人造景觀和演員搬演再現作為前景,讓兩者有機結合起來進行敘事。
筆者在紀錄片《八月桂花遍地開》中也進行了類似的嘗試,其中有這么一段將軍回憶:“瓦解敵軍,優待俘虜也是我們宣傳隊的一項工作,在戰場上,每當我們對著東北軍的陣地唱《流亡三部曲》,他們陣地上就靜悄悄的,槍也不打了……”這段內容如果僅僅用將軍的回憶錄進行包裝處理,視覺上未免有些單調,后來,攝制組使用大功率的投影機,將電影《西安事變》中一段符合內容的片段投影到現實中陜北一處與此事相關的革命舊址的窯洞上,形成歷史和現實兩種時空的融合,作為“過去時”敘事的視覺呈現。
(六)動畫展現
動畫是一種老少皆宜、觀眾喜聞樂見的視覺藝術形式。將動畫運用到紀錄片中參與“過去時”的敘事也由來已久,甚至在歐美還有諸如《與恐龍同行》《宇宙大爆炸》《自閉心靈》等純動畫紀錄片。在文化歷史類紀錄片中,近些年中國的創作者也在大量使用動畫參與紀錄片“過去時”敘事,比如紀錄片《沖天》《劉銘傳在臺灣》等,動畫占比都比較高。由于多數畫面使用動畫表達,就給導演、撰稿在文本創作上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敘事自由度,讓紀錄片更加具有觀賞性。
(七)數字技術與實景結合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全息影像、虛擬現實等技術手段也陸續運用到紀錄片創作中。這里所說的數字技術與二維、三維動畫有明顯區別,它是指通過計算機創造的足以以假亂真的特效場景與真實影像相結合的技術手段,很多無法演繹出的場景,可以通過數字技術來完成,從而達到完整的情景效果。[2]
2006年上映的美國電影《總統之死》盡管不是紀錄片,但卻使用了紀錄影像和虛擬現實結合的拍攝手法。影片用電腦技術將布什的頭“嫁接”到演員身上,演出了布什被兩顆子彈射中腦袋的一幕。在這種技術的加持下,完全可以讓已故的人物“復活”,參與到紀錄片“過去時”的敘事當中,讓過去的人物和事件看得見,讓觀眾對故事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使“過去時”的內容更顯得像“進行時”。
二、紀錄片“過去時”表達過程中的問題規避
(一)避免細節違和
在紀錄片“過去時”的表達過程中,最容易出現問題的就是細節違和。真實是紀錄片的靈魂,無論是真實再現還是動畫表達,細節還原對創作者來說都是必須謹慎對待的。例如,在紀錄片《八月桂花遍地開》的創作過程中,有這么一個片段:
【解說】洪學智和藏族頭人巴登多吉的第一次見面,話題是從一個唱片機開始的。
【洪學智角色配音】我們有個唱片機,放了唱片,他覺得很奇怪,怎么響呢? 我就告訴他是怎么回事兒,他很開心。
這一段導演組選擇用動畫的方式進行敘事,那么在動畫中需要處理幾個細節,一是藏區的環境和藏民、軍隊的著裝,這個相對好處理,另一個是提到的唱片機。19世紀90年代唱片機進入中國,在隨后的發展中,唱片機的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那么在洪學智的回憶錄中提到的唱片機長什么樣?回憶錄中沒有記載。為此筆者專門前往大連旅順口區的留聲機博物館進行調研,經專家判斷,找到了符合20世紀30年代特征的留聲機作為樣本進行動畫創作,盡可能保證動畫表達的真實性。
(二)避免資料誤用
在紀錄片創作中,通常會涉及很多老的影像資料的使用,由于資料繁雜,傳播混亂,往往會出現用錯資料的情況。比如在涉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內容的紀錄片中,常常會看到一組國民黨軍警槍斃一排人員的鏡頭,這組鏡頭通常會被解說成國民黨鎮壓共產黨人,但經過考證發現,這組鏡頭其實是在槍斃土匪。
(三)避免違背紀錄片倫理
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和運用,以假亂真成為可能,這就涉及紀錄片倫理的討論。虛擬現實不是虛假事實,虛擬現實只是表現手段,如果使用不當,極易讓觀眾對一些編造的故事信以為真,特別是在短視頻快速傳播的今天,在視頻被斷章取義后加以傳播,可能會產生無法挽回的后果。因此無論是真實再現還是虛擬現實再現,目前最有效的倫理規避方法就是在畫面中標注清楚,讓觀眾自己去理解。此外在真實再現拍攝時,巧妙地使用一些手法,產生一些離間感,也是規避紀錄片再現“以假亂真”的有效方法。[3]
結語
紀錄片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其“過去時”的表現形式也是與其他視覺藝術形式不斷交流、不斷學習、不斷融合、不斷創新的過程,但事實真實、邏輯真實都是在創作過程中必須堅守的基本原則,唯有如此,才能保證“紀錄”的價值。
注釋:
[1]劉占國.基于“情景再現”的紀錄片創作探析[J].傳媒論壇,2020(10):145-146.
[2]李林濤.新媒體時代紀錄片創作的情景再現手法探討[J].傳播力研究,2020(13):88-89.
[3]任戌盈,楊夢圓 .真實與間離:紀錄片中的情景再現研究[J].新聞世界,2021(10)82-85.
(作者單位:安徽廣播電視臺紀錄片中心)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