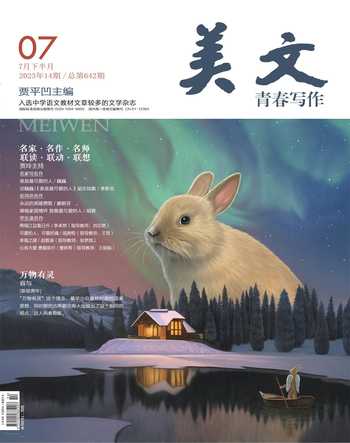山中記
陳雅芬
我剛來中大(香港中文大學簡稱)的時候,旁聽了一堂金融課。進去教室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小班課,總共不過15個人。剛上課教授問有誰是注冊了這門課?大半個教室舉手,只剩下我們這一角。教授走過來詢問得知,我們是交流生,還沒到注冊時間。他又問我們是哪里的交流生,我們回答,他感慨道:“我以為你們交流會想去更遠一點的地方。”
其實我想過去更遠一點的地方的。不過有很多原因。轉(zhuǎn)專業(yè)造成的學分問題,前置課程設(shè)計的問題,不過大抵真正阻力還有經(jīng)濟問題。
來中大是個不錯的旅程,在各種意義上。最直接的是它能讓我修3080,既投資分析與組合管理課程,是一切高階金融課的基礎(chǔ)課。我在本校欠了一節(jié)微積分課,這學期上不了了。當然來中大也有弊端,比如我上不了那節(jié)微積分課,因為這兒沒有課程設(shè)計相近的對應選擇。中大的3080相當和藹可親,這是對比出來的。朋友在怨聲載道本校3080的工作量時,我報以同情,深感慶幸。
另一點,課程時間設(shè)計。3學分的課要求一周上3個小時,不同于本校把課程都拆成一周兩節(jié)。我在中大的一半課是一次直接上完3小時,另一半是上兩小時再換一天上一小時。這樣的好處是,安排得好的話,我?guī)缀蹩梢悦刻於贾簧习胩煺n,剩下的半天能夠自由安排。在本校,我?guī)缀跻焯鞆脑缟系酵怼?/p>
我選滿18學分。不過體感來說,這學期在中大的18學分更舒適一點的。一方面是難度上沒有上學期高,另一方面是中大的考試時間安排比較巧妙。中大的專業(yè)比較多,開的課也多,累積下來考試時間很長。對于個體而言,可能每門課的考試時間離得很近,也可能離得很遠。我是后者,我選的課橫跨5個學系,于是我從10月底到11月中旬都在慢悠悠地考期中,再做兩個禮拜的Pre來到11月底,又慢悠悠地從11月底考到12月中旬后,有近一個月的期末考。比起本校那種一周考完四門的絕望期末,我更適合這種節(jié)奏。考完了一周能拿一整天出來放松,再花幾天準備新一周的考試。
除卻投資組合分析管理,18學分里另有3分是一門與我的專業(yè)和畢業(yè)要求全然無關(guān)的課,語言學系開的語義學。Tutorial的時候小組討論,一圈都是語言學專業(yè)的。我問周圍的同學,是否都是本專業(yè)的學生選擇這門課?她們說也不一定,可能有別的人文學科的同學來上。我說,可能我是這門課唯一的商科學生,她們大笑。這門課可以說是我這學期上得最輕松快樂的一門課。
剩下的,我修了一些什么課呢?經(jīng)濟學系開的公司金融基礎(chǔ)(因為我搶不到金融學系開的公司金融基礎(chǔ)課,只好退而求其次),數(shù)學系開的線性代數(shù)I(我上到一半才發(fā)現(xiàn)這個課并不能替代我本校的線性代數(shù)課),金融學系開的金融科技的目前發(fā)展,以及通識部門一個統(tǒng)計學講師教的風險管理與現(xiàn)代社會的視角(非常古怪的課名,也可能是我翻譯能力的不足)。上來上去,越發(fā)覺得我可能不適合學金融,也不喜歡。我對現(xiàn)實金融的認知是套利,對理論金融的印象是模型。可能并不正確吧,但這種誤解本身也說明了我沒有深入了解的興趣。去年的這個時候我覺得市場營銷的學習是無趣的,決定轉(zhuǎn)到金融專業(yè),現(xiàn)在我又覺得金融是無趣的。目前我不能再轉(zhuǎn)專業(yè)了,不然就得延畢一年了。也許這種心態(tài)是傲慢的。我一直愛講我不喜歡數(shù)學,不過這學期寫數(shù)學作業(yè)的時候,我偶爾覺得數(shù)學也比金融有趣一點。
我最后上了一開始旁聽的那門金融課,一門沒有多少人上、也算不上太學術(shù)的金融課(更像一個對現(xiàn)代金融科技的通識教育課)。授課老師具有非常豐富的業(yè)界經(jīng)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年輕時美國投行,后轉(zhuǎn)做大學講師,都是很不錯的職業(yè)。許多上這門課的同學也是真的對金融科技有興趣,畢竟這談不上是門專選課。也因此,在這門金融課,我深切感受到了真正喜好金融的人的思維方式。務實的、逐利的、自我的、進取的、侵略性的。這些其實都是這個行業(yè)的從事者的可佳品格。但或許于我而言,他們所從事的,有些虛無。反而研究兩個詞語是什么類型的反義詞這種事情,我覺得更有意思。
幾乎每個周末,我都會和舍友出門。有時候去沙田吃飯兼去大埔墟買菜,有時候去別的地方走走。
在中大的生活節(jié)奏一直都更放松。我來交流之前就是這個打算,要松弛一些,多休息一些,當這是一場為期四個月的長途旅行。
這段旅行的起點是中大本身。
從我書桌旁的窗戶看出去,能看見大半個中大,看見車船游弋、火樹銀花,看見無波水面如霧又如鏡的吐露港。中大在山上,而我在山頂,所以滿窗風景。
中大在山上,倚著一座山建了錯錯落落的樓,修了回環(huán)往復的路。我不喜歡登山,但山很美。我喜歡沿著山徑往下走,被風吹。往誠明徑向上走有點累,但漫天的綠和側(cè)身可見的水,讓這段行程也美。抬頭是綠意,低頭,在葉子與枝條之間,能見吐露港的鏡面。身處自然里,人很容易沉入靜謐。以前覺得小校園很好,怎么走都很方便,我不會迷路。但在山中的大校園也很好很好,我愿意迷一迷路。所謂一步一景,在中大是如此的。
喜歡是喜歡一些瞬間,而瞬間寄托在空間。講講我在中大喜歡的一些空間吧。
我住在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前,有一陣子立了塊黑板,定時有人抄一首詩。某一天夜晚,那首詩叫作“在別處生活”,作者是嚴瀚欽,摘自《碎與拍打之間》。
但這不要緊,脫根處你停下筆
以悲觀者的幽默
串那一些不太相關(guān)的詞語,例如放逐
與流浪、書寫與玩笑
此鄉(xiāng)與彼鄉(xiāng)
如果有機會,我會買這一本詩集。
錢穆圖書館往邊上走,是半圓形的新亞廣場。時不時有學生樂隊在這里表演。應該都是香港學生,唱些粵語歌、日語歌或英語歌。
YIA,全名康本國際學術(shù)園。商科的課多在那兒,我也幾乎天天在那。YIA二樓有個小書店。九月我還沒有考試安排,在那個書店里幾乎讀完了一套日本作家中短篇小說集。二樓還有個咖啡店。我從前沒有喝咖啡的習慣,但下午的課太困人,加之課間無處可去,我竟也常常惠顧彼家店。
還有一些視角很獨特的地方,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時間去拍一拍風光:通往五高的天橋,伍何曼原樓五樓外的平臺角落,李卓敏基本醫(yī)學大樓通往LT的反復樓梯路外接的某個平臺……
中大很大。乘著校巴繞著山轉(zhuǎn),能轉(zhuǎn)個半小時。在中大待了兩個多月,我想我也沒轉(zhuǎn)完過這個校園,總還有一些地方?jīng)]有去過。
不過香港是小的,這份小賦予了中大方便。其實中大的地理位置算不上太方便,幾乎在東鐵線盡頭,是地圖的角落。但中大靠著大學站。幾乎所有校巴的終點都是大學站,大學站人來人往,不是校門勝似校門。而到了大學站坐上地鐵,就進入了港鐵的交通網(wǎng)絡,花半個小時能到中環(huán)。
從大學站往金鐘方向搭兩站是沙田站,直接連著新城市廣場。買衣服、日用、零食都能去新城市廣場,平均下來我與新城市廣場三五天一會。來港兩月我在新城市廣場吃過十來頓飯,其中五六次在四樓的燒肉like,一家非常不負其名的烤肉店,我在學校吃某些食堂的次數(shù)都沒有這家多。新城市廣場不好的點在于太繞,一個商場分三期,找一家店要轉(zhuǎn)大半圈,對于我這種路癡而言實在不太友好。且新城市廣場背后還連了個連城廣場,往前走轉(zhuǎn)個天橋還能到沙田中心,實在是現(xiàn)代建筑交互性流暢性的寫照。
往羅湖/落馬洲方向坐一站,就是大埔墟。出門又是一個商場,叫作新地商場。香港和深圳都盛產(chǎn)商場,而我在商場和商場夾縫中的學校里讀書,難能。我和舍友常去這間商場里的百佳買菜。其實大埔墟有街市,但出站要走一段距離,出一趟門太累,舍友不太愿意走,我也就沒走過。我說我們下次去吧,她說可以呀,但要等考完試后。
上學期間并沒什么很輕松的日子,但還是忙里偷閑,去了不少地方。
九月開頭,和一波國際生去了淺水灣,到了海灘,六七個人齊刷刷地換上泳衣鋪了條浴巾開始日光浴,我和朋友目瞪口呆,這是我見過的最具象的文化沖擊;和舍友去了M+,開啟了我們后續(xù)的一系列博物館探索之旅;中旬又跟著i-centre去了太平山和赤柱,不幸那天霧蒙蒙,看不到什么好風光;到九月底,找不到人同我去海洋公園,本都做好打算賺不到二人同行的票價差,不想不熱衷戶外活動的舍友最終答應了我;然后終于決心備戰(zhàn)托福,結(jié)果還是被中大mcamp的朋友拉去坐了個游船,人果然禁不住玩的誘惑。
九月曬夠了太陽,十月初則在托福和期中考的時間夾縫里去博物館吹吹冷氣,去了趟藝術(shù)館又去了趟文化館。兩個館的布展都很有意思。藝術(shù)館的幾個展都很不錯,放展品的玻璃干凈透明,仿佛沒有痕跡,伸手可觸展品;最出名的巴洛克展對得起名聲。文化館做得也很好,一些古代展品做了數(shù)字化展示,與內(nèi)地博物館常見的厚重氛圍有所不同,是有趣的體驗。十月底,在兩個期中考之間,坐了大半個小時車去了趟電影院,算作越獄。看了《海賊王》大電影,歌很好聽,但劇情叫作為情懷買單。
現(xiàn)在是十一月,天氣依然很熱。中午又去了燒肉like吃飯,接著去大埔墟買菜。三個小時后回到宿舍,一窗子的陽光落在地上,亮堂堂。有太陽的午后容易生長倦意,我和舍友同時嘆氣。我說香港的天氣和深圳一樣可怕,她說去年不是這樣的,可能是全球變暖。
(寫于2022年秋,于香港中文大學交流交換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