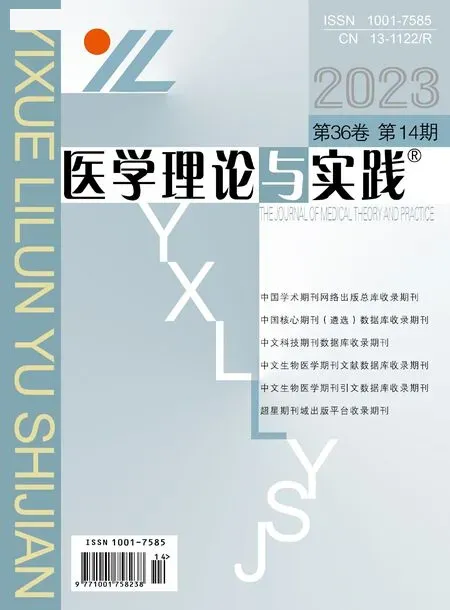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對社會疏離的影響分析
付寧寧 孫 垚 天津市人民醫(yī)院神經(jīng)內(nèi)科 300121
根據(jù)我國相關流行性調(diào)查顯示,我國腦卒中患者現(xiàn)存約1 100萬例,每年新增患者240萬例,其中約75%的腦卒中患者由于軀體障礙、語言障礙等并發(fā)癥,導致其在康復期出現(xiàn)社會回避行為、消極心態(tài)[1]。社會疏離感是指在多種因素影響下,個體對社會群體活動、交流的自動疏遠、隔離的心理狀態(tài)及行為表現(xiàn)[2]。對于腦卒中康復期患者而言,較高水平的社會疏離感不利于患者個體情緒及行為體驗與外界的社會環(huán)境相交融,對其身心健康及生活質(zhì)量的提高產(chǎn)生阻礙作用,導致疾病康復進展的延緩。創(chuàng)傷后成長是指個體在經(jīng)歷震撼性的創(chuàng)傷事件后,其原有目標、信念受到巨大沖擊后動搖、破碎,個體為有效應對而重新構建的有益于自身的認知圖式,是一種與具有創(chuàng)傷性質(zhì)的事件或情景進行抗爭后所體驗到的正性心理變化[3]。但目前,相關文獻發(fā)現(xiàn),關于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社會疏離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通過調(diào)查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社會疏離感的現(xiàn)狀,并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旨在為后續(xù)開展相關心理康復干預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1月—2022年5月我院收治的120例腦卒中康復期患者作為觀察對象,其中男72例,女48例,平均年齡(54.87±6.88)歲,小學/初中學歷49例,高中/中專學歷51例,大專、本科及以上學歷20例,47例患者合并有慢性疾病,73例患者未合并慢性疾病。本次研究經(jīng)過我院醫(y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且所有觀察對象均以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1)符合2016年美國腦卒中協(xié)會關于腦卒中的診斷標準;(2)均為首次發(fā)病,且經(jīng)治療后病情好轉、生命體征穩(wěn)定;(3)意識清晰,閱讀理解能力正常,能夠配合調(diào)查研究;(4)患者知情并簽署同意書。排除標準:(1)心、肺、腎等嚴重病變或合并惡性腫瘤患者;(2)臨床資料缺失患者;(3)研究期間失訪或死亡患者。
1.3 調(diào)查工具 (1)一般資料調(diào)查表:該調(diào)查表分為一般人口學資料及疾病相關資料兩部分,其中一般人口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水平、婚姻狀態(tài)、居住地、家庭收入情況、醫(yī)療付費方式;疾病相關資料包括腦卒中類型、是否合并慢性病、肢體功能情況。(2)創(chuàng)傷后成長量表(PTGI):采用中文版創(chuàng)傷后成長量表[4]對患者進行調(diào)查,該量表分為人際關系(7條)、欣賞生活(3條)、自我認可(7條)3個維度共計17項條目,采用Likert 6級評分法進行計分,其中從“完全沒有”~“非常多”分別記0~5分,滿分85分,分值越高,代表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水平越高。(3)一般疏離感量表(GAS):采用一般疏離感量表[5]對患者進行調(diào)查。該量表包括自我疏離感(3條)、他人疏離感(5條)、懷疑感(4條)、無意義感(3條)4個維度共計15項條目,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進行計分,其中從“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分別記1~4分,滿分60分。分值越高,代表患者社會疏離感水平越高。
1.4 調(diào)查方法 在問卷調(diào)查前,研究人員就研究目的、意義、問卷填寫方式等內(nèi)容向患者進行解釋,以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及配合。在本次研究中,采用現(xiàn)場發(fā)放問卷方式對患者進行調(diào)查,在問卷調(diào)查過程中,研究人員需采用一致性的指導用語對患者進行問卷填寫指導,在患者問卷填寫完畢后,及時檢查問卷的完整性。排除規(guī)律性作答問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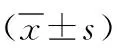
2 結果
2.1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社會疏離感現(xiàn)狀 本次研究共計發(fā)放120份調(diào)查問卷,有效回收120份,有效回收率為100%。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水平為(60.24±11.94)分,社會疏離感水平為(42.15±9.67)分,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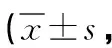
表1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社會疏離感現(xiàn)狀分)
2.2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社會疏離感相關性分析 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與其社會疏離感呈負相關(r=-0.299,P<0.05),見表2。

表2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社會疏離感相關性分析
2.3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社會疏離感水平對比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其社會疏離感水平在年齡、學歷水平、家庭收入情況、是否合并慢性疾病、肢體功能情況等方面存在差異(P<0.05),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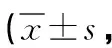
表3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社會疏離感水平對比分)
2.4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社會疏離感影響因素分析 以患者社會疏離感水平作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及Pearson分析中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的量作為自變量納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賦值情況見表4)。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患者年齡、學歷水平、是否合并慢性疾病、肢體功能情況、創(chuàng)傷后成長水平是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社會疏離感的影響因素(R2=0.589,調(diào)整R2=0.577,F=49.240,P=0.000),見表5。

表4 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賦值情況

表5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3.1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社會疏離感現(xiàn)狀 本文結果顯示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水平為(60.24±11.94)分,處于中等水平,與胡存杰等[6]的研究結果(59.82±6.90)分相接近,高于張秀娟等[7]研究中的腦卒中手術期患者(34. 37±5.76)分。分析其原因在于:相較于腦卒中手術期患者,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在經(jīng)過系統(tǒng)化的臨床干預后,對于自身疾病狀況及治療有了正確的認知,且在治療過程中患者身體各項機體得到改善,部分患者心理狀態(tài)也逐漸平穩(wěn)。此外,本文結果顯示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社會疏離感水平為(42.15±9.67)分,處于較高水平,高于趙翠翠等[8]的研究結果(39.18±7.26),對患者疾病康復產(chǎn)生不利影響。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120例腦卒中康復期患者中近1/3的患者由于疾病因素存在肢體功能障礙,導致其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乃至喪失,更容易導致其社會疏離感水平的上升。
3.2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與其社會疏離感的相關性 本文結果顯示,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與其社會疏離感水平呈負相關。減少暴露、回避社交等一系列社會疏離行為是個體受到特異性損傷后為避免歧視所采取的一種自我保護行為,其中個體的消極心態(tài)及不良應對方式是社會疏離感產(chǎn)生的核心要素。創(chuàng)傷后成長是患者經(jīng)歷創(chuàng)傷后為降低自身痛苦而產(chǎn)生的正性心理改變及行為活動,根據(jù)Tedeschi等[9]的理論,創(chuàng)傷后成長具體可表現(xiàn)為個人信念及力量的增強、積極尋求外界的幫助、對生命的感激及重視等方面,對于降低患者消極情緒的影響、增強患者社會適應能力、改善疾病應對方式具有意義,由此可以解釋腦卒中康復期患者創(chuàng)傷后成長與其社會疏離感水平呈負相關。
3.3 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社會疏離感影響因素 本文結果顯示,患者年齡、學歷水平、是否合并慢性疾病、肢體功能情況、創(chuàng)傷后成長水平是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社會疏離感的影響因素。其中在年齡方面,患者年齡越大,其社會疏離感程度越高。分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老年群體由于身體機體的不斷退化,其認知、交流、行動等方面的能力均顯著下降,增加了社會疏離感;另一方面,老年患者相較于中青年患者,其在罹患腦卒中后,其自我照護能力急劇下降,對于家人的關心陪伴的依賴性更高,但由于社會節(jié)奏的不斷加快及家庭經(jīng)濟方面的壓力,導致患者家屬難以抽出更多的時間陪伴、照顧患者,使得患者內(nèi)心孤獨感不斷上升[10]。在學歷水平方面,小學/初中水平的患者社會疏離感最高,高中/中專次之,大專、大學及以上最低,與李永平等[11]的研究結果相似。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患者文化水平越低,其認知水平相對局限,導致其獲取疾病相關知識的渠道也相對更為封閉、也更少,使得其對于疾病發(fā)生的心理準備度更低,在疾病治療過程中,更容易出現(xiàn)焦慮、恐懼等負性情緒,從而采取回避、消極等疾病應對方式[12]。在是否合并慢性疾病、肢體功能情況等方面,合并慢性疾病以及肢體功能障礙的患者其社會疏離感水平更高。其中合并慢性疾病、肢體功能障礙可導致患者治療周期的延長,其生活自理能力受到更為嚴重的限制,因而其社會疏離感水平更高。
綜上所述,腦卒中康復期患者社會疏離感處于較高水平,其創(chuàng)傷后成長水平與其社會疏離感密切相關,在臨床中對于高齡、低學歷、合并慢性疾病、存在肢體功能障礙的患者,護理人員需要格外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