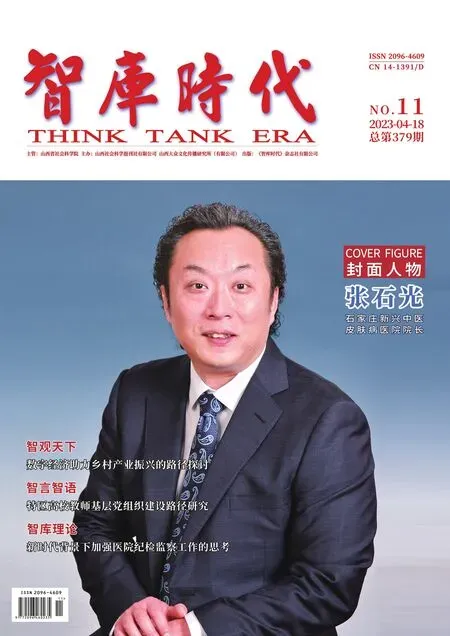從大型民族歌劇《沂蒙山》看中國民族歌劇的創作
劉琳 呂俊禹
(煙臺工程職業技術學院)
中國歌劇自1921 年黎錦暉的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公演開始,已然走過了百年的發展歷程。期間,中國歌劇經歷了以《揚子江暴風雨》為代表的話劇加唱詞的“左翼”歌劇時期;經歷了以載歌載舞的廣場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為代表的延安秧歌劇時期;經歷了以《桃花源》《沙漠之歌》等作品為代表的借鑒探索西洋歌劇創作手法的創新時期,為中國歌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自被稱為中國歌劇里程碑之作《白毛女》的誕生,中國歌劇進入到了一個發展高潮,標志著新歌劇的開始。新中國成立后反應新中國建設題材的作品《小二黑結婚》《草原之歌》等;1956 年“百花齊放”藝術指導方針的提出后,誕生的與戲曲元素緊密結合的歌劇《紅珊瑚》《紅霞》等,以秧歌劇形式創編的歌劇《洪湖赤衛隊》《江姐》等,以及表現少數民族故事情節的歌劇《阿依古麗》等作品,膾炙人口的藝術作品,深入人心的表現形式,將中國歌劇不斷推向成熟。
在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中國歌劇也有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傷勢》《原野》《屈原》《張騫》等作品更是有了創作層次上明顯的提升,中國歌劇再次進入到發展的高潮期。
歌劇藝術發展到當下,不論是在藝術價值、舞臺表現、戲劇創作、等方面,還是在人物塑造、演員表現唱功等方面都呈現出了質的飛躍。融合了中國民族歌劇發展過程中一直傳承創新戲劇元素的特色;中國民族歌劇中“話劇加唱”,說唱結合的特色;繼承開創了中國歌劇一直以來借鑒吸收西方歌劇的優秀經驗方法等特點,在現代嚴謹創新的創作技法、現代舞美表現手法、舞臺表現得多樣性、創新性發展的探索嘗試中,誕生了眾多可圈可點的經典作品。
由王曉嶺、李文緒作詞,欒凱譜曲,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中共臨沂市委、臨沂市人民政府共同出品,山東省歌劇舞劇院排演的大型民族歌劇《沂蒙山》在全國各地陸續上演。劇作以大青山突圍、淵子崖戰役歷史事件和真實人物原型為創作素材,通過兩個家庭、四位主要人物的故事發展為重點,巧妙運用獨唱、重唱、合唱、對唱等多種歌唱表現形式,融合民族地域特色和現代舞美技術等創新手段,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沂蒙山革命根據地發展壯大的真實歷史事件;展現了沂蒙山軍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動人故事;揭示了“軍民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沂蒙精神”;體現了紅色歷史背景下民族歌劇的戲劇性與民族化,主題清晰,特色鮮明、藝術價值和欣賞價值都具有開創性。
一、戲劇性的故事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賦予了歌劇生命力
曲折生動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特色的人物形象是歌劇創作的內核。在有著420 余萬人口,120余萬擁軍群眾,20余萬參軍戰士,10 多萬英烈的沂蒙山地區,“遍地是英雄,處處有紅嫂”。歌劇《沂蒙山》中“塑造的每個人物都有原型,展現的每個事件都有記載”[1]。民族歌劇《沂蒙山》選取大青山突圍、淵子崖戰役為創作素材,生動講述了1938 年冬季八路軍115 師來到山東沂蒙山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在危難之際解救沂蒙山深處的村民,村民們心懷大義、心存感恩,軍民一心、英勇斗爭的故事。全劇分為“蒙崖解圍”“送夫參軍”“護軍就義”“夏荷托孤”“海棠舍子”“軍民重逢” 六幕,圍繞兩個家庭,四位主要人物展開。一條脈絡以海棠及其丈夫林生、舅舅孫九龍的故事發展為主線,代表了老百姓生活和心理狀態的變化成長。另一條脈絡是以夏荷與其丈夫趙團長等人物為代表的八路軍戰士,展現了大義凌然、英勇斗爭的革命精神和親近百姓、融入百姓、解救百姓的革命情懷。兩條故事主線圍繞軍愛民、民擁軍,舍小我為大家展開,相互襯托、互為表里。四位主人翁之間的戲劇故事和性格鮮明的形象塑造,將戰爭年代艱苦卓絕、大義凜然的革命精神展現的蕩氣回腸、悲壯崇高。
在劇目中每一位人物形象的塑造都生動鮮活、真實感人。海棠是一位農村姑娘,性格爽朗、剛強,從小父母雙亡,跟隨舅舅孫九龍長大,在與青梅竹馬的小伙子林生操辦婚禮時,遭遇了鬼子的襲擊,千鈞一發之際,八路軍一一五師及時出現,擊退了敵人,解救了全村百姓。在“軍愛民”深情的感召下,海棠支持丈夫林生參軍。林生是一位熱情善良的農村小伙子,新婚不久就踴躍參軍,與親人骨肉分離投身革命斗爭中,從一名熱血青年成長為革命軍人,最終英勇就義。海棠的舅舅孫九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村長,為了掩護受傷的八路軍戰士,毅然選擇犧牲自己保全大家,最終獻出自己的生命。一一五師趙團長與女戰士夏荷是一對軍旅夫婦。夏荷性格溫柔善良,因懷有身孕,在村中待產,與村里同樣有身孕的海棠成為好姐妹。在敵人攻擊村莊時,夏荷為掩護隊伍和老鄉撤退,不幸身負重傷,臨終前把剛剛出生的孩子小沂蒙托付給了海棠撫養。海棠不負所托,含辛茹苦將兩個孩子撫養長大。后來遭遇鬼子進村,海棠義無反顧地用自己的親生骨肉引開敵人,保護了夏荷的孩子,當趙團長從前線重新回到村子時,海棠將小沂蒙交給了生父。
在劇情的創作中海棠由一位農村姑娘,成長為人妻人母;由一位普通百姓成長為一名心懷大義、重情重義的人民戰士,人物形象、角色身份隨著劇情的發展不斷變換,鮮明生動,是全劇的亮點。夏荷的大義凌然、林生的血灑疆場、九龍叔的視死如歸,一個個生動真實的人物形象躍然舞臺。劇中的其他人物山妮子、福順、小八路、小山子、小沂蒙等,創作者也進行了生動的刻畫,有血有肉、入情入理,為劇情的發展做好了襯托和鋪墊,使感人的故事更加真實生動。
二、貼近劇情,各具特色的曲目創作為歌劇注入了靈魂
音樂的創作是歌劇的靈魂。民族歌劇《沂蒙山》中共有六幕,40個唱段,通過獨唱、重唱、合唱、對唱等形式,選取經典有代表性的民歌音樂旋律和戲曲元素,結合中西音樂創作技法,創作出旋律優美、形式多樣、符合人物角色和劇情發展的音樂,使劇目有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的帶入感。
選段《等著我,親愛的人》是全劇中最動聽、最有感染力的一首二重唱。全曲采用西方大旋律線條的音樂風格,通過民族化的演唱技法和歌劇表演形式進行歌曲的演唱和呈現,旋律風格抒情優美,細膩婉轉,準確的刻畫了海棠、林生兩位戀人內心的情感變化和依依惜別之情,使劇情得到了升華。
選段《沂蒙山,永遠的爹娘》將山東經典民歌《沂蒙山小調》的旋律揉碎了融入其中,既有經典民歌的影子,又有創作性的改編,推陳出新,旋律線條富有地域特色,生動優美,與歌劇的名稱遙相呼應,使人身臨其境,沁人心脾,聞聲便能感受到祖國河山的美麗和人民的淳樸可愛。
選段《世間哪有這樣的情》是海棠和夏荷演唱的一首女聲二重唱,在創作技法上結合了西方音樂旋律創作手法和地方音樂特色。如“一聲聲呼喚,一聲聲真情,沂蒙的男人,將生命留給子弟兵”這一部分,在樂曲的創作上運用了F 大調,使音樂展現出了大調式旋律寬廣大氣、磅礴有力的音響效果,展現了主人翁崇高寬闊的情懷。唱段中地方音樂曲調山東民歌《鳳陽歌》的半音音型的也在該唱段中進行了創作性的改變,自然流暢,具有民族特色[2]。在分曲之間,還有過渡的器樂曲及交代劇情的說白,使劇情和樂曲得到了巧妙的連接。
劇中除了有創作考究的獨唱曲目外,重唱與對唱也占據了很大的篇幅,非常有特色。全劇五首重唱曲中有表達夫妻間情感的旋律優美纏綿的核心唱段《等著我,親愛的人》;表達姐妹間情誼的唱段《花開花謝不分離》;表達軍愛民情感的《感謝親人子弟兵》;有表達民擁軍情感的《世間哪有這樣的情》等;表達內心矛盾沖突、復雜心情的海棠、夏荷、林生、孫九龍的四重唱《海棠,讓他去吧》。五首重唱都有獨立的藝術價值和欣賞價值,放在一個劇目中又為劇情的發展進行了敘述與烘托。
歌劇中的合唱唱段也非常有亮點,男聲合唱、女聲合唱、混聲合唱等形式多樣。合唱選段《東進!東進!》《以命搏命保家鄉》《怎么辦,怎么辦》《一雙鞋子針兒密》,對劇情整體的敘述和群眾情感意愿的表達發揮了重要作用,使音樂的展現形式體現出了多樣性,場面宏大有氣勢。
三、多元融合的創作手法為歌劇注入了創新亮點
歌劇《沂蒙山》在演唱技法上融合了民族唱法、美聲唱法、戲曲演唱方法等。主人翁海棠、林生等采用民族聲樂演唱技法,結合有美聲唱法的發聲方法,聲音明亮、細膩、委婉動聽。夏荷、九龍叔等人物采用美聲唱法,也結合有民族唱法的咬字吐字方式,聲音渾厚、堅定、有力。在海棠的唱段中還多處運用了傳統戲曲的演唱和表現方式,飾演者王麗達,融湖南花鼓戲、民族、美聲唱法于一身,結合山東民間音樂的演唱技巧,在演員的二度創作中歌曲的民族特色更加濃郁。
在歌劇中中國戲曲的創作手法隨處可見,傳統戲曲分場方式的使用;詠嘆調中板腔體的創作方式;“一字多音”的運用和體現;民歌《趕牛山》《鳳陽歌》《我的家鄉沂蒙山》等旋律元素的融入;大量民族器樂的使用都體現出了民族音樂的特色[3]。在樂器的選擇上采用管弦樂隊作為歌劇的主要配樂,體現了民族音樂的繼承和創新以及與西方音樂元素的碰撞融合。
四、現代化的舞美設計為劇作增加了的質感
創作團隊在舞臺布景、舞美燈光的設計上下足了功夫。以山體為背景的變化就達36次之多,舞臺燈光的使用更體現出詩意和質感。
巍峨雄偉的高山,茅草屋、手推車、秧歌隊、煎餅攤、碾谷子等舞美的設計,展示了山東民風、民俗、民間藝術的魅力和特色。巧妙的布景設計,形象地在舞臺上還原了當時的生活環境,讓作品真實自然,精致靈動,也與《沂蒙山》這部歌劇的主題和環境巧妙地呼應。
燈光的使用上冷暖色交融輝映,月色下送別新婚丈夫;陽光下女兵們給鄉親們表演秧歌;漫天大雪中老百姓給部隊送軍糧;冰天雪地里士兵們守衛故土;陽光照耀下滾滾的麥浪。舞臺燈光時而展現昏暗的灰色;時而展現夢幻的藍色;時而展現溫暖明亮的黃色,現代技法的燈光運用使劇情的展現活靈活現,更加真實,對劇情的發展起到了有益的烘托[4]。追光燈的運用使重要角色和重點場景更為突出,也給舞臺變化和場景布置贏得了時間。
大型民族歌劇《沂蒙山》在劇情設計、音樂創作、舞美呈現、演員表演等多個方面都體現出精益求精的創作精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扎根民族文化土壤,傳承開拓、融合創新,為中國原創民族歌劇的發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與創新。
五、中國當代歌劇的創作趨勢
歌劇《沂蒙山》是新時代優秀民族歌劇的代表,體現了現代歌劇與傳統歌劇的結合。近年來各屆為了促進優秀民族歌劇的創作采取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有效舉措,自2011 年開始的首屆中國歌劇節和開始實施的“中國民族歌劇傳承發展工程”等項目,都對優秀劇目和重點劇目進行創作、宣傳等方面的扶持。讓文化藝術屆對民族歌劇的創作重拾信心,為經典劇目的創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民族歌劇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不盡人意的發展趨勢。
首先,強烈的追求用西洋歌劇的創作手法、表現形式,甚至是演唱技巧和演唱方式作為歌劇創作和表演的主要方式,而相對弱化了民族歌劇的特色、民族音樂元素、民歌小調、傳統音樂旋律的特色,甚至是傳統民族音樂的演唱方式和表演形式,對民族歌劇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上還有待加強[5]。有的歌劇在創作過程中也注重了傳統元素的融入,但結合的方式還顯得過于生硬,浮于表面,使得有些歌劇和歌劇唱段有中不中,洋不洋的感覺,沒有發揮出傳統歌劇的民族特色,創新還不夠有新意。
中國戲曲是中國歌劇發展的基礎,中國傳統歌劇曲目中的板腔體就來源于中國戲曲[6]。將戲曲素材提煉、加工運用于民族歌劇的唱腔和旋律中,是當代歌曲創作的一個繼承發揚的重要特色。傳統戲曲聲腔來源于地方劇種的聲腔基礎,和當地的地方語言特色還結合緊密。
除了戲曲外,傳統的民歌、說唱、彈詞、鼓詞等形式也是當代歌劇創作吸收傳承重要的傳統元素。如歌劇《江姐》中不單運用了故事發生地四川的地方民歌、清音、川劇,還吸收了蘇州評彈、江浙婺劇等說唱音樂的音調與元素,豐富了歌曲的表現。
其次,現代歌劇創作在創作題材上,有厚古薄今的態勢。近年來,由重大歷史事件、歷史故事、歷史人物改編的歷史劇目,內容以描寫大場面、大事件的居多,而體現現代生活,描寫生活中的小人物、身邊故事的生活化情節很少。例如大型歌劇《木蘭詩篇》《長征》《張騫》等等,《沂蒙山》本身也是基于革命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來改編創作的。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了當代歌劇在創作中創作素材的單一化,創作的局限性。
再次,在歌劇的創作上追求氣勢磅礴,場面宏大,舞美表現越來越奢華高端。在歌劇的整體呈現上體現出了與西洋歌劇接軌,與國際化音樂接軌的趨勢,但有些脫離本土、脫離生活、脫離大眾群體的欣賞水平。在歌劇曲目的創作上,有類似像西方歌劇中的大而華麗的詠嘆調,充滿戲劇色彩的宣敘調等表現形式。也有追求大而華麗,創作的作品有曲高和寡,難以攀附和欣賞,脫離群眾的云端高雅藝術的感覺。
在未來歌劇的發展過程中堅持藝術服務人民的出發點,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忘傳統,吸收外來,面向國內舞臺與國際舞臺,運用傳統創作技法和音樂特點,吸收借鑒西方歌劇的先進經驗和優秀做法,即保留中國歌劇的根和魂,又不斷的注入發展與創新。推動中國歌劇向著特色鮮明、博采眾長的創新與包容的方向邁出堅定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