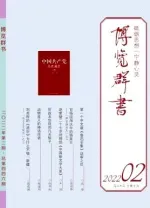《人罪》對打工者精神困境的反思
錢天瀾 章濤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城市化進程,農民進城務工逐漸成為近幾十年普遍的社會現象。“打工”一詞本是粵語方言,隨后流傳至全國,同時也衍生出更多含義。除了受雇于人之外,打工一詞通常意味著背井離鄉到外地、外省工作,且多指從事比較勞累、每天工作時間比較長、收入不高、可替代性強、重復性高的體力和低級腦力工作,這種工作一般來說不屬于“鐵飯碗”的工作。傳統社會主義時期,勞動具有塑造社會主義新人主體以及創造新生活的神圣性和意義感,相形之下,“打工”可以說重新定義了近些年國內最大范圍的勞動形式,表征著時代的深刻變化。21世紀以來,文學批評界圍繞著題材和作者等問題對“打工文學”的定義展開了集中的討論,以何西來、洪治綱、李敬澤為首的一派認為打工文學應該從題材的角度進行定義,既包括打工者寫打工生活的文學也包括專業作家寫打工生活的文學。
從中國“打工文學”的發展與現狀出發,關注到打工群體的文學寫作已然成為當代文壇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而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參與工人群體的文學教育,媒體關注和支持,涌現出“皮村文學小組”,發行紀錄片《我們的詩篇》,出版《勞動者星辰》等文化事件。近年來,不乏學者提出用“新工人”取代“農民工”這一稱謂,其主要關切是超越實用主義消極描述意味的命名,而將這一數量龐大的群體重新放置在“工人”這一社會主義主體的序列中,探尋新的時代狀況中新的工人主體塑造的可能性及其現實出路。
當下語境中,關注新工人群體的文學寫作行為本身與評析其作品同等重要。因此,本輯所評均為新工人所創作。本輯評論作者皆為高校中文系學生,他們以敏銳的思考、細致的筆觸呈現了新工人筆下的世界,剖析了新工人主體的困境和對未來的展望。
——陜慶(寧波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周春英(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
作為龐大打工者隊伍中的一員,王十月的復雜經歷為其“打工文學”的創作賦予了鮮明的個人色彩。自2000年第一篇小說《我是一只小小鳥》發表以來,他的作品迅速受到批評界的關注。特別是小說集《人罪》的出版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認可。
和大部分打工文學作家一樣,王十月的創作始終關注打工者的命運和生存困境。但前者更傾向于在城市—打工者的二元結構下來描述打工者的邊緣處境,而王十月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這個固定化的敘事結構,將敘述的重點轉向了對打工者本身的精神困境的考察。
如果說這個特點在之前零星發表的作品中并未構成一種“顯性”的文本現象,那么當小說集《人罪》出版后,我們便能更直觀地將他筆下的形象排列為某種“譜系”加以研究。王十月對打工者精神困境的揭示,首先體現在一系列“蒙昧”的打工者形象上。如《人罪》中,小販陳責我為了供孩子讀書,從農村來到城市。但就在兒子即將高考之際,他的三輪車被城管沒收。陳責我心生怨恨,干出了驚天血案,且毫無懺悔之心。在他那些既“天真”又“殘忍”的言語背后,呈現了一個深陷精神困境中的“囚徒”形象。
其次,王十月還注意到了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中遭遇的精神“異化”。如在《不斷說話》中,忘川大橋的守橋人職位是為了防止有人爬橋而設立的,而當爬橋的人都被阻止了之后,這個工作崗位就面臨著撤銷,守橋人于是陷入了失業的恐慌中,甚至開始希望有人來爬橋,每天在痛苦和焦慮中度日。
最后,王十月還觀察到同樣出身貧苦,打工者之間非但不能互相幫助,反而彼此戕害。如在《出租屋里的磨刀聲》中,生活和工作中的種種壓力使得天右和鄰居互相仇視,最終暴力相向。又如《白斑馬》中的英子,一心努力工作,換來的卻是同伴的敵意,小說中寫道:
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利益沖突時,是可以相互溫暖的,當有了丁點大的利益沖突,一切馬上就會變得冰冷無情。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何關注于打工者的精神困境,這反映出他對“打工者”群體怎樣的新思考?
第一,和王十月本人的打工經歷有關。他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因為自己的懦弱,未能及時向一位打工妹伸出援手,導致對方被治安隊抓走。這次經歷帶給王十月以強烈的“創傷”體驗,以至于“許多年來”還會想起“她那凄涼求助的聲音,和我們躲在黑暗中瑟瑟發抖而不敢伸出援手時的冷漠與無力”,并最終發展成了某種“罪感”意識:“因為她,讓我知道我是一個有罪的人,我所有的寫作,都是在贖我的罪。”
正是在這種“罪感”意識的引導下,王十月于自我內部發現了“人性”的弱點,進而意識到打工者的苦難遭遇不僅來自外部物質世界的壓抑,還有精神層面的孱弱。也因此,他總是在小說中追問人物的主體性動機,并力圖將之提升到思想、精神層面加以考量。如小說《人罪》對農村娃趙城和陳責我進城后的戲劇性命運的刻畫,寫出了人在面臨絕境時強烈的內心交戰與靈魂原罪;又如《九連環》中吳一冰和林小玉面對破產與勒索,意外殺死勒索者后的驚慌與自責。這些顯然都離不開作者對“罪感”意識的把握。
第二,這也和王十月對底層文學的接受與反思有關。同樣以底層勞動者為書寫對象,王十月在學習創作的過程中,很自然地注意到了“底層文學”。但同時他也發現,在知識分子筆下,打工者形象在極大程度上被本質化和符號化了:
我讀他們的作品,反觀自己,發現這是一種通病,我的經歷告訴我,不是這樣的,不能簡單地看問題。我們要撇開道德審判,撇開善惡判斷,把這一切歸結到人,歸結到時代,把這一切放到一個大的時代下去考量。
作為打工者,王十月感受到了當代中國社會政治與文化轉型的力量,也充分體驗到這一轉型過程中,打工者群體的心理和情感變化遠遠超過了知識分子的底層敘事。基于這種反思,王十月于是格外注意避免用外在于打工者的社會身份來規定主要人物的言行舉止。在他筆下,打工者未必永遠正面,但始終有血有肉。如《出租屋里的磨刀聲》中的天右:他受鄰居磨刀聲的影響,無法得到身心的休息,失去了女友和工作,情緒崩潰。最終,他在迷茫與憤怒中意外殺死了磨刀人,自己的良心也永無安寧之時。
如此一來,打工者內在的精神問題便“浮出水面”,得以被細心的作者所捕獲。換言之,正因為王十月不再將打工者簡單視作麻木無知的“無產者”或“城市邊緣人”,而是充斥著精神矛盾的立體的“人”,他才能夠突破一般“打工文學”和“底層文學”的藩籬,觸及打工者灼熱的靈魂。
羅吉·福勒曾說過:“作品的敘述者可能是作者自己,……也可以是作品中的某個人物或某些人物,作者把他(他們)放在作品中充當講故事的角色。”對于一般的打工文學作者來說,為了盡可能充分地實現其“自我傾訴”的最初目的,他們往往有意識地將自己的聲音與作品中的敘事者/主角統一起來,由此形成某種一體化的敘事視角。因此,哪怕小說采用了第三人稱敘述,也總是帶有明顯的“我”的痕跡。
對打工者精神困境的關注,意味著王十月不能再單純地“我手寫我心”,因為“我”無法反思自身的存在,更難以深入靈魂去審視自我的精神殘缺。于是我們看到,在《人罪》集的許多作品中,在主要形象之外,還有一個隱含著的敘事者視角,對前者形成“審判”。比如《白斑馬》中不斷出現的“你”,又如《九連環》中穿插出現,以反思打工者悲慘命運為主要功能的柒小兵和小伍。
正是這種敘事視角的分離,使得作者能從不同立場,相對自如地探究筆下人物所面臨的精神困境,進而分析悲劇的成因。但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眾所周知,打工文學的生命力在于對打工者思想情感的正面呈現,而這恰恰與其高度統一的敘事視角有關。反觀王十月,敘事視角的分離打破了打工文學原本穩定的情感結構,客觀上在敘事對象和敘事者之間制造了“距離”。換言之,在從“外部”更為細致地對敘事對象加以反思的同時,作者與打工者原本親密的關系卻變得曖昧不明,前者必須謹慎地使敘述保持“豐富的張力”,才不至于令作品脫離打工文學所必需的情感邏輯。
然而,要維持這種張力關系卻十分困難。它一方面要求作者對打工者所身處的時代語境變化、相關政策的調整都有敏感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求作者始終與在時代大潮中沉浮的打工者群體維持“血肉聯系”,與他們的情感同頻共鳴。而對于王十月來說,危險之處在于,從作品看,他不僅沒有為這個分離出來的新視角找到一個穩定的“位置”,毋寧說隨著他的成名和身份轉變,這個游移不定的“視角”正越來越被納入當代文藝體制建設的過程當中,進而“知識分子化”。事實上,《人罪》出版后,王十月就沒有再發表打工文學作品,而是轉向了更具“知識分子性”的科幻文學創作。綜上所述,在《人罪》中,王十月轉向“人”的視角,關注于打工群體的精神困境,深化了打工文學的思想內涵。但敘事視角的分離,又悖論性地為其寫作帶來了新的危機。站在更為宏觀的層面,這種危機實際也指向了當下語境中,打工文學整體性的發展困境:作家們如何跳出日趨僵化的二元敘事模式,在時代變遷中發掘打工者所遭遇的新問題,還需要我們不斷地思考。
(作者簡介:錢天瀾,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研一學生;章濤,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講師。)
在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迅速崛起和90年代的“更新換代”之后,打工文學已經形成了特定的問題意識和寫作方法,甚至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模式化的窠臼。如何超越既定的身份限制,回到本雅明所謂“此時”“此地”的層面來思考打工者的生存處境和情感結構,似乎變得尤為重要。在這個意義上,王十月于《人罪》集中對打工者精神困境的討論不僅是寫作視角上的轉換,更意味著作者對打工者群體的思考進入了一個更為深入的空間,因而有著不可忽視的價值。本文從人物形象分析入手,討論王十月如何在審視打工者精神困境的過程中,將這批一度被符號化的無產者還原為生動立體的“人”,同時也注意到這種轉變背后潛藏著的敘事危機,以期為學界反思打工文學的未來發展提供參考。
——章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