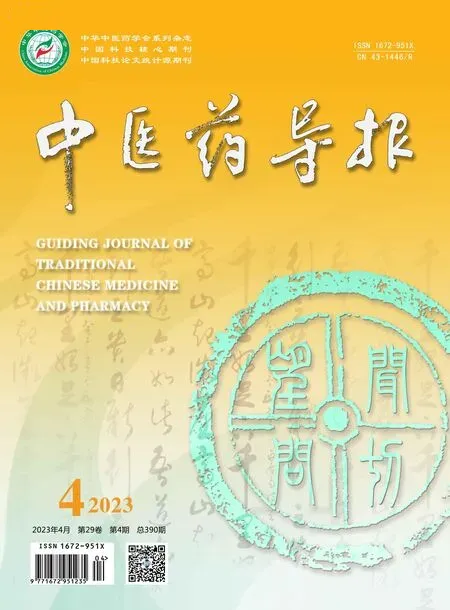陸瑾運用舌針結合體針治療失眠伴焦慮狀態經驗*
吳若瑩,陸 瑾,魏心昶,王雪瑋,侯瑞涵,韓小玉,葛皓裕
(1.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01;2.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南京中醫院,江蘇 南京 210001)
失眠是以頻繁而持續的入睡和(或)睡眠維持困難并導致睡眠感不滿意為特征的睡眠障礙,多伴有日間困倦疲勞、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等問題[1]。失眠伴焦慮除上述癥狀以外,還伴有煩躁、驚恐、緊張易激、坐立不安等焦慮情緒,或口干、面紅、易出汗等自主神經紊亂癥狀,是一種典型的生理-心理疾病[2]。流行病學研究顯示,中國的失眠人群高達42.5%,且原發性失眠伴焦慮狀態發生率為51%~54%[3]。社會競爭激烈、生活節奏加快、環境壓力增大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致使我國過去8年間失眠患病率由不足20%升至38%。其中80%慢性失眠患者伴有焦慮狀態,以女性居多,且大部分患者因為過度關注自身的睡眠狀態產生焦慮感,而焦慮感在一定程度上又會加劇失眠,由此形成惡性循環[4-5]。研究表明,失眠與焦慮和抑郁呈現出雙向相關的關系,睡眠-覺醒調節與焦慮狀態受去甲腎上腺素、γ-氨基丁酸、乙酰膽堿、多巴胺、血清素等多種神經遞質共同作用。失眠與情緒調節過程有關,而情緒調節對焦慮狀態的改善非常重要[6]。目前西醫治療失眠主要應用苯二氮艸卓受體激動劑、褪黑素受體激動劑、食欲素類藥物、具有鎮靜作用的抗抑郁劑,但長期服用具有依賴性和耐藥性等不良反應。研究表明,針灸在治療失眠方面有獨特優勢,具有療效佳、安全等特點。
陸瑾教授,南京市名中醫,南京針灸學會副理事長,潛心臨床三十余年,在針灸診療及科研教學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尤其對失眠的診治有獨到見解。陸瑾教授認為該病主要責之營衛失和、心神失養,治療以調和營衛、頤養心神為整體思路。筆者有幸師承陸瑾教授,受益匪淺,現將其運用舌針結合體針治療失眠伴焦慮狀態經驗總結如下,以資共享。
1 病因病機辨析
中國古代醫學典籍中沒有關于失眠伴焦慮這一病名的直接記載。陸瑾教授認為,可根據失眠伴焦慮狀態的相關臨床癥狀,將本病歸于中醫學中的“不寐”“臟燥”的范疇。病位在心,病因與營衛、肝、脾、肺、腎密切相關,病理因素責之“火”與“痰”。治療當以調和營衛、頤養心神為主,同時平衡其他臟腑陰陽。
1.1 營衛失和 失眠屬于中醫“不寐”范疇,最早見于《難經·四十六難》,又稱為“目不瞑”“不得眠”或“不得臥”。營氣和衛氣都是以水谷精氣為其主要的生成來源,但是“營在脈中”“衛在脈外”[7-8]。陽主晝,陰主夜,陽主升,陰主降。人之寤寐取決于衛氣,衛氣晝行于陽,動而為寤,夜行于陰,靜而為寐[9]。衛氣白日時循行于體表,夜間則走行于內臟,與營氣相合,共助五臟之精,以濡養五臟之神,神安則能寐。衛氣這種有規律的行陽入陰,與自然界陽氣的晝夜變化相一致,保證了人體正常的作息機制[10]。營衛氣血充盈,肌肉滑利,氣道通暢是擁有正常睡眠的必要條件。衛陽與營陰交感互藏,相接而和,營衛不調和,衛氣浮越,夜間衛氣不能入于陰分,則出現“夜不瞑”。因此,陸瑾教授認為導致失眠的根本病機是營衛失和。
營衛失和也會影響情志調暢。《素問·舉痛論篇》言:“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11]悲致心肺郁結、上焦不通、營衛不利而氣消,然心肺位于上焦,心主血而藏神,在志為喜,肺主氣而藏魄,在志為憂,營衛失和,可直接引起情志障礙[12]。由此可見氣血調和、營衛通調才得以濡養五臟,使神志平和,心身正常。
1.2 心神失養 《素問·六節藏象論篇》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11]。《靈樞·大惑論》言:“心者,神之舍也”[13]。任何心理活動皆因“神氣舍心”而發于心,應于其他臟[14]。張介賓《類經·疾病類》就如此說:“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而總統魂魄,并賅意志。故憂動于心則肺應,思動于心則脾應,怒動于心則肝應,恐動于心則腎應,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15]心能夠支配人的意識、思維、精神、情感活動。心為君主之官,心主血脈、主藏神,是人體生命活動的之本,因此心能支配人的整個生命活動。故治療失眠伴焦慮狀態始終離不開心,責之營衛、肝、脾、肺、腎。若心之氣血陰陽虧損,或心火亢盛,或水飲、痰濁、瘀血等阻滯血脈,使得氣血陰陽失和,則可影響心主神明的功能。心神失去濡養亦或心神被擾、心神難安,則心不藏神的各種臨床表現會相繼出現,如失眠多夢、心煩健忘、思維遲鈍、精神不振等[16]。
綜上所述,陸瑾教授認為:飲食失節、勞作失宜、情志所傷等原因造成營衛不充,營衛通路阻滯,衛氣浮越于外,陽不入陰,夜不得寐;心神失于濡養,心神被擾、心神難安,情緒失去調控而導致失眠伴焦慮狀態。
2 針灸臨證特色
2.1 舌針針刺 舌體刺血或針刺治病的歷史源于《黃帝內經》,歷代也有發展。真正創立并最先提出舌針療法的是著名中醫管正齋先生。舌針療法較傳統針法具有操作簡便、安全、不留針等特點[17],目前舌針較多應用于舌歪、舌強、舌麻,以及腦卒中所致的中風言謇、語言不利、吞咽困難等。陸瑾教授在長期的臨床觀察中發現失眠伴焦慮狀態的患者存在口干、口苦、舌體麻木或不適的情況,故選取點刺舌體穴位,取得了良好的療效并逐漸形成個人特色。
舌與機體是一個整體。舌不僅是心之苗竅,脾之外候,還是五臟六腑之外候,與臟腑經絡也關系密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記載:“心主舌……在竅為舌。”[11]“脾經之脈……連舌本,散舌下;足少陰腎經……循喉嚨,挾舌本;手少陰之別……循經入于心中,系舌本;足太陰……上結于咽,貫舌中;足太陽之筋……其支者,別入結于舌本;手少陽之筋……其支者,當曲頰入系舌本。”[18]可見,五臟六腑直接或間接地通過經絡、經筋與舌相聯系,臟腑的氣血上營于舌;舌位處于陰陽之交,上達督陽,下抵陰任,交通陰陽;舌質、舌形、舌色及舌苔反映了人體氣血陰陽虛實、津液盈虧和病癥進退。心氣通于舌。失眠伴焦慮狀態病位在心,與其他臟腑亦有密切聯系,因此通過對舌體相應區域的刺激能夠對心神及全身臟腑陰陽氣血的調整平衡起到一定作用[19]。舌針可引起腦葡萄糖代謝增加,舌針治療后顳上回前部、兩邊枕葉的楔前葉和距狀回的代謝明顯提高[20]。研究發現舌針治療機制可能與生物全息學說、神經學說、近腦學說、腦的代償功能學說等有關。實驗室研究則證實了舌針可提高心功能,抗疲勞,降低血液黏稠度,從而防止血栓形成,改善血流動力學,還可以改善微循環,增加腦供血,從而促進腦代謝,有益于腦組織的修復[21]。其中“近腦學說”認為舌位于頭的正中,是一個隨時可外露其貌的肌性器官,具有豐富的體液及酶;舌體十分敏感,且腦神經分布至舌體的徑路最短,使得針刺后的感覺沖動很快傳至腦干的網絡結構,因而調節全身各個系統,尤其是對腦源性疾病有快速與良好的調節作用[22]。目前較為公認的失眠及焦慮共同的發病機制與中樞神經遞質和免疫細胞因子有關,而舌針針刺的作用機理也與中樞神經遞質密切相關,故舌針能夠有效調節失眠相關癥狀和患者緊張、焦慮、煩躁等情緒。
選穴及操作:辨證選取心穴、脾穴、腎穴、肝穴、金津、玉液等,每次根據患者舌象選取1~3個穴位點刺,不留針。患者取仰臥位,將舌自然伸出口外,暴露舌穴位置即可(有畏懼者可用牙齒輕輕咬住舌尖)。醫者左手固定患者頭部,右手持針,快速點刺,不留針,不以出血為度;操作的同時要注意觀察患者的面部表情,一旦表露痛苦、不適之感,立即停止針刺;首次操作時應充分考慮患者的耐受性。
筆者在舌針治療的過程中觀察到,失眠伴焦慮者對舌針療法有很高的接受度。在治療早期,舌面及舌下絡脈較易出血,尤其是舌邊、尖紅或口干口苦明顯的患者;隨著治療的持續與深入,舌象也隨之改善,舌色趨于淡紅,黃苔或少苔也逐漸好轉,裂紋減少。經舌針治療后,患者自覺舌強、舌麻、口干、口苦等癥狀明顯改善,口中津液增多,同時失眠及焦慮狀態均有明顯緩解。舌針能疏通氣血,調整陰陽,扶正祛邪,與其能夠調節體液和神經系統的作用密切相關。舌針的作用機制是一個復雜的機體調節過程。舌針可通過經絡系統、神經體液、血液循環等多系統、多途徑的調節作用達到綜合治療效果[23]。
2.2 體針針刺 主穴選取百會、四神聰、太陽、安眠、內關、神門、印堂、大橫、中脘、下脘、氣海、關元、三陰交等。百會、印堂屬督脈,督脈上巔,為陽脈之總綱,并于脊里,主神志病。百會在手、足三陽與督脈及足厥陰交會之處,位于巔頂,內絡于腦,而腦為髓海、元神之府、精明之府,主宰著五臟六腑的功能協調及其與外界的聯系。《道藏》云:“天腦者,一身之宗,百神之會也。”[24]取百會通督調神,安神益氣。內關為手厥陰心包經絡穴,八脈交會穴,通于陰維脈。陰維有維系聯絡諸陰經之作用,因“陰維為病苦心痛”,病位在里,有寧心安神、疏通經絡、理氣和胃之效。神門為手少陰心經原穴。《道藏》曰:“玉房之中神門戶。”[24]“玉房”,心也。取本穴以開心氣之郁結,使神志得舒。神門與內關原絡相配,治療效果尤佳。三陰交為足三陰經交近處,能夠宣通氣血。百會、印堂、神門、內關、三陰交五穴相搭配,能夠溝通上下,疏通經絡,通調陰陽,安神益氣。中脘、下脘、氣海、關元為腹針引氣歸元之義,同時營衛之氣出于中、下焦。中脘為胃經募穴,中脘配下脘可理中焦、調升降。胃氣升則心氣降,脾氣升則腎氣降。氣海協關元發揮培本固腎之用,調補五臟氣血,如此以達交通心腎,水火既濟之效。大橫穴屬足太陰脾經,能夠溫經通絡,健運脾胃。研究表明大橫穴能夠緩解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21]。
安眠穴和四神聰為經外奇穴,取其調和氣血陰陽、鎮靜安神之用[25]。兩穴與百會、安眠為伍,共奏寧心安神之功。太陽為經驗用穴。陸瑾教授認為因手陽明、手太陽和手足少陽之經筋結于太陽部,針刺太陽或太陽穴周圍區域能夠起到改善睡眠與放松緊張、焦慮情緒的作用。該穴深部有顏淺動、靜脈,布有三叉神經第二、三分支和面神經顆支,刺激該穴位具有調節神經和血管等多種功能[26]。
肝火擾心者,加人中、太沖、行間以清瀉肝熱;營陰不足或陰虛火旺者,加復溜、太溪、大椎、心俞、腎俞以溝通心腎;脾胃不和、痰熱熾盛者,加豐隆、梁門以清化痰熱;心脾兩虛、氣血虧虛者,加足三里、脾俞、心俞健脾以調補氣血;衛陽亢奮者,加取水溝、合谷、鳩尾、中庭、內庭、大椎;心虛膽怯者,加日月、丘墟、膽俞、心俞。
3 驗案舉隅
3.1 病案1 患者,女,38歲,2021年12月13日初診。主訴:入睡困難伴焦慮1個月余。現病史:患者1個月余前因精神緊張出現入睡困難,服用艾司唑侖片(1 mg/片,1片/晚),每周3~4次,睡眠時長4~5 h,多夢易醒,肌肉酸痛,情緒焦慮,煩躁易怒,為求針灸治療,遂來診。刻下癥見:入睡困難,自訴入睡時間需1~2 h,甚至徹夜難眠,精神緊張難以放松,急躁心煩,面色黃欠潤澤,時有頭痛、頭暈,有輕微耳鳴,目干,口干,納差,食后腹脹,腰酸明顯,倦怠乏力,小便調,大便質稀,不成形,月經周期規律,量少,色正常,無血塊,無痛經。舌色淡苔白膩,舌尖偏紅,脈細。既往史無特殊。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SQI)評分20分,提示睡眠質量很差;貝克焦慮量表評分51分,提示存在焦慮狀態。西醫診斷:失眠伴焦慮狀態。中醫診斷:不寐;辨證:脾胃虛弱兼心火上炎。予針刺治療。取穴:舌針取心穴、脾穴,取0.25 mm×40 mm毫針,快速點刺,每穴2~3次,點刺深度2.5~5.0 mm,以不出血為度,不留針;體針取百會,四神聰,印堂,雙側太陽、安眠、內關、神門、大陵、大橫,中脘,下脘,氣海,關元,雙側三陰交、足三里等,均為常規針刺操作,留針30min。囑患者治療每周2~3次,持續治療4周。
2診:2021年12月27日,治療1周后,患者訴整體均有改善,心情較前舒暢,每周服用艾司唑侖次數減少,目干、口干改善明顯。舌色淡苔稍膩,舌尖紅不顯,脈細。陸瑾教授考慮患者標實之證已去大半,予兼顧扶正,遂調整取穴:去大陵,加雙側梁門、太白、心俞、脾俞。
3診:2022年1月4日,治療2周后,患者訴睡眠已有改善,艾司唑侖片改服用0.5片/晚,1~2次/周,入睡時間約45 min左右,睡眠時長5~6 h,煩躁、焦慮、緊張等情緒較前明顯好轉。目干、口干不顯,胃口佳,食納較前明顯增加,食后腹脹不顯,日間疲乏感、腰酸、肌肉疼痛改善,頭暈、頭痛發作次數減少,耳鳴未作。舌淡潤滑,苔薄白。
4診:2022年1月14日,4周治療結束后,患者訴能夠正常入睡,已停用艾司唑侖,睡眠時長可達7 h,易醒多夢明顯好轉,自覺近期心煩緊張癥狀少見,大便基本成形。PSQI量表評分5分,提示睡眠質量很好;貝克焦慮量表評分32分,提示不存在焦慮情緒。患者逐漸恢復正常的工作生活。后電話隨訪,患者訴大部分時間睡眠正常,情志舒暢。
按語:本案患者為青年女性,體型消瘦,面色黃欠潤澤,納差,倦怠乏力,舌色淡苔膩,脈細,可知脾胃虛弱,運化無權,水谷精微無以承化,生化乏源,營血不足,營陰虧虛,運行無力,致營衛阻滯不交,營衛失和,發為不寐;情緒緊張,焦躁不安,舌尖偏紅,可知心火上炎,陰不斂陽,心腎難交,加重失眠與焦慮情緒。陸瑾教授認為該患者為本虛標實之證,治法當以清心安神,益氣健脾。故初診時重在清心火,寧心通絡。2診時患者標實之癥均有改善,治療重心轉向脾胃,增加太白、梁門等穴位健脾益氣,理氣和胃。治療過程中患者表示睡眠狀況出現反復,陸瑾教授認為此現象是睡眠功能自身調節的過程所致。3、4診時患者諸癥得緩,故守前方以鞏固療效。
3.2 病案2 患者,女,58歲,2021年11月3日初診。主訴:夜寐欠安3年余,加重5個月。現病史:患者3年前因精神壓力大出現夜寐欠安,入睡尚可,睡眠時長4~5 h,多夢易醒,醒后難以入睡,情緒急躁,心煩易怒,為求針灸治療,遂來診。刻下癥見:面色無華,痛苦面容,五心煩熱,入睡時間30~60 min,睡前服用灑萬酸唑吡坦片(10 mg/片,1片/晚),3~4次/周,睡眠時長4~5 h,眠淺易醒,醒后難以入眠,伴心悸、頭昏脹悶,口干口苦,潮熱汗出,食納可,小便調,大便偏干,已絕經。舌質紅、舌苔少薄黃、舌面細裂紋,脈弦細。既往有原發性高血壓病史16年、糖尿病病史2年。PSQI量表評分18分,提示睡眠質量很差;貝克焦慮量表評分53分,提示存在焦慮狀態。西醫診斷:失眠伴焦慮狀態。中醫診斷:不寐,臟躁;辨證:陰虛火旺兼肝郁化火。予針刺治療。取穴:舌針取心穴、腎穴,取0.25 mm×40 mm毫針,快速點刺,每穴2~3次,點刺深度2.5~5.0 mm,不留針,以不出血為度;體針取百會,印堂,雙側太陽、安眠、風池、內關、神門、大橫,中脘,下脘,氣海,關元,雙側三陰交、復溜、太溪、人中、太沖、行間等,均為常規針刺操作,留針30 min。囑患者治療2~3次/周,至少治療4周。
2診:2021年11月12日,治療2周后,患者敘述病情時面露喜色,自覺心煩急躁情緒有改善,面色較前稍有光澤,睡眠時間較前延長30 min以上,夜間易醒次數減少,口干口苦改善顯著。
3診:2021年12月25日,治療4周后,患者訴睡眠已有改善,停用思諾思,入睡時間少于30 min左右,睡眠時長5~6 h,心情較前舒暢,心悸、頭昏悶脹不顯,1周有兩晚不出現多夢易醒,舌色稍紅、舌苔薄白。原治療方法取穴中去行間、太沖,加心俞、腎俞、陰陵泉等。
4診:2022年1月28日,8周治療結束后,患者訴睡眠時長可達7~8 h,多夢易醒基本消失,醒后可復睡。PSQI量表評分3分,提示睡眠質量很好;貝克焦慮量表評分27分,提示不存在焦慮情緒。患者逐漸恢復正常的工作生活。后電話隨訪,患者表示睡眠正常,情志暢。
按語:本案患者年近六旬,腎水腎精虧虛,精虧血少,不能上濟于心,陰虛陽亢,心火熾盛,不能下交于腎,則虛熱虛火內生,心腎不交,水火難濟,因而出現心悸失眠、心煩頭昏、口干口苦、潮熱汗出,舌紅苔少等癥。加之患者病情遷延日久,心神難寧,肝郁火化,久病多瘀,故出現急躁易怒,大便干等癥狀。陸瑾教授認為,治療上應予以滋陰降火,交通心腎,疏肝清熱。初診時患者腎經虛熱及肝火熾盛之象突出,故治療側重在清瀉肝經郁熱和心腎虛火,同時不離滋陰,瀉實補虛。2診時患者諸熱象之癥漸有改善,沿用原方鞏固療效。3診時患者火熱之邪已不顯,故去行間、太沖,增加心俞、腎俞、陰陵泉等著重滋陰補腎,培元固本。
4 結 語
陸瑾教授治療失眠伴焦慮狀態辨證求因,審因論治,基于調和營衛、養心安神這一整體思路,因人制宜調整臟腑陰陽,以舌針結合體針療法為手段,取穴精巧,用意深遠,針法輕盈,治神守氣;同時重視患者情緒疏導,普及睡眠健康教育,多管齊下,標本兼治,療效顯著,為治療失眠伴焦慮狀態拓寬了思路與方法。